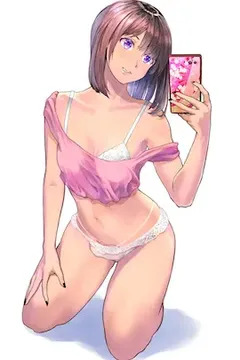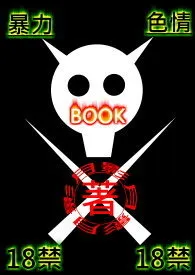春天的时候,我醒了。
雪花早已融化,太阳真大,像张大饼。
我吃掉手中的大饼,喝光桌子上的鲜牛奶,开始整理我的东西了。
报纸和杂志我收拾了足足一百斤,我决定把它们卖给收破烂的。
这些报纸和杂志被我买回小屋,用去了大概一千块钱,那个大爷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数了二十多块钱给我。
书是一本也不能卖的,我买了两个大号的密码箱子,全部放进箱子里,整整两箱子,估计有二百斤,加上我另一个箱子里的衣服和零碎,估计有二百五十斤。
被子和褥子就不带了,可以打个包寄回家让老妈拆洗。
屋子里干净起来,东西聚集在看不见的箱子里。
看见的只有三个箱子。
我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一夜过后,我就能站在北京的黎明里。
我是多么的开心。
我就要离开了,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了。
这个不快乐的城市,我不快乐的生活啊。
花儿在开放,和我没关系。
你踩着我的脚了,你比我还凶,你正要抱怨我弄脏了你的鞋底,我对你宽容地一笑说,没关系。
你拉着煤球上坡,眼看就要上不去了,我随手推了一把你就上去了,你上去的时候,你的煤球掉一只污染了我的白鞋子,你回过头,不知道先说谢谢还是先说对不起,你终于决定先说对不起,你刚一张嘴,我对着你说,没关系。
你理坏了我的发型,把我搞得跟个少妇一样,我皱着眉头看着你,你正要张嘴道歉,我对你说,没关系。
你挡着我的道了,你装做没看见,我等了半天才能过去,我回头对你说,没关系。
你死之前说过我坏话,我对着你的尸体说,没关系。
你是男是女,你是挤公交车的,你是拉煤球的,你是理发师,你是无赖,你死了,这一切都没关系。
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Z大学校园也和我没有关系了,我想在里面再走一走,看一看,我一点都没有留恋。
天都黑了,我也无法看见你的脸,你说你挡着我干什么,难道我连在这所校园里走走看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你是校长他女儿吗?
你就算是校长他女儿又怎么了,你管不了我,我来旅游,我给钱还不行吗?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真让我恐惧,你说什么?
你想对着我抽完手中的烟,**,你凭什么呀?
你不怕得肺炎我还怕呢,鲁迅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鲁迅是抽烟太多最后得肺炎死的,他死的时候他的肺都成了乌黑的鱼网了,你知道他要是不死能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继续付出多么大的贡献吗?
你不知道!
不抽烟的人和抽烟的人在一起,危害性比抽烟的人还大,什么,你不这样认为?
这可是科学,你连科学都不相信吗?
你刚才叫我什么,爬小房?
**,你怎么把我的名字倒着叫,我叫房小爬,不叫爬小房,你这样叫我不是姓房而是姓爬了,我不是叫小爬而是叫小房了,**,你别再胡搅蛮缠了好吗?
什么?
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倒背如流?
**,就三个字,听一遍就能倒背如流,你要是伟大,你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倒背一遍试试,什么?
你认识我都快两年了?
你问我的病好了没有?
我什么时候的病?
两年前的病?
**,两年前的病得到现在就是发烧也上升到七八万度了吧,那我不是早就化成了空气,还能在这见到你吗?
恐怕你连我的屁味儿都闻不见了。
你的烟抽完了吧,什么?
你还想再对着我抽一根,大姐,你行行好,放我过去吧,我还要去找张朵告别呢,我马上就要去首都北京了,我马上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春天都来了,你还挡着我干什么,你去园子里看花吧,那些花儿和你一样美丽,去吧,我也不认识你,我认识苗苗,她一个人去看大海了,什么?
我认识你?
我在哪里认识你?
你一说名字我就能想起来?
你倒是说说看,让我搜索一下我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和你同名的,什么?
你叫张朵,你刚才就听见我说我要去找一个朋友叫张朵吧,你真丢人,张朵可是一个男人,你能叫一个男人的名字吗?
你在瞪我吗?
那我想对你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反正我也看不见,你的头发为什么要遮盖眼睛遮盖脸,你以为这春天校园是拍国产恐怖片的地方啊!
什么什么,你说你的名字不叫张朵?
我正仰着头走路,突然看见对面有一个女孩站住了,她穿着一双拖鞋,右脚上的拖鞋有一只塑料狗,左边的拖鞋没有,好象不是成对的拖鞋,但颜色好象是一样的,我惊讶那拖鞋有一种不对称的美。
女孩的裤子又肥又大,穿着一件小巧的花外套,好象没有扣子,就那样敞开着,乳房把看不见颜色的毛衣顶得脱离了肚皮,在空中悬着。
她的头发好象是刚刚洗过,不听话地都围到了前面,我无法看见女孩的眼睛和脸,只看见有一截香烟从她的嘴里突出来,她把烟抽得雾气腾腾。
我正要从她旁边走过去,她却挡住了我,我往左拐,她也往左拐,我往右拐,她也往右拐,我站住,她也站住,吓得我后退了两步,我就站在路灯下看着她。
我知道她的眼睛绝对可以透过头发的缝隙看见我,完全的看见我,这是我的经验,因为在公交车上我总是让头发遮盖住眼睛去偷看女人的屁股和乳房。
难道这个女孩认识我吗?
她认识我应该是正常的,我常常被别人关注嘛,但我要是认识她,我就不正常了,因为我不爱关注别人。
她猛吸了几口烟,她的双手插在小巧外套的口袋里,两腿都开始晃上了。
她在听音乐吗?
我们的周围不断有学生穿来跳去,有些学生还停一下看看我们。
我有些不耐烦了,我对着两腿越晃越陶醉的长头发女孩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真让我恐惧。
女孩像个杀手一样,半天才抽出左手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她对我说,我想对着你抽完手中的烟。
我有些愤怒了,我问她,你凭什么呀?
女孩又抽了一口烟说,凭我知道你叫爬小房。
我扑哧笑了,**,你怎么把我的名字倒着叫,我叫房小爬,不叫爬小房,你这样叫我不是姓房而是姓爬了,我不是叫小爬而是叫小房了,**,你别再胡搅蛮缠了好吗?
女孩严肃地对我说,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倒背如流。
我扑哧又笑了,**,就三个字,听一遍就能倒背如流,你要是伟大,你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倒背一遍试试?
女孩故意用很沧桑的腔调对我说,我认识你都快两年了,你的病好了没有?
我有些纳闷,我什么时候的病?
女孩吐出一口烟说,两年前的病。
我不是扑哧又笑了,而是哈哈大笑了,**,两年前的病得到现在就是发烧也上升到七八万度了吧,那我不是早就化成了空气,还能在这见到你吗?
恐怕你连我的屁味儿都闻不见了。
女孩没有笑,她的烟越抽越短。
我问她,你的烟抽完了吧?
女孩的右手抽出来,抓着一包“桂花”牌香烟,她把左手的烟头熟练地用指头弹到路边的墙上,那烟头火花四溅,然后消失。
她用腾空的左手抽出一根新的插在嘴上,她说话的时候嘴上的烟就上下晃动起来,她说,我还想再对着你抽一根。
女孩说完,把左手插进口袋,抓出一只打火机,打着后就点上了。
她点烟的时候,我看见火光中她苍白的鼻子。
我开始求饶了,大姐,你行行好,放我过去吧,我还要去找张朵告别呢,我马上就要去首都北京了,我马上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女孩拼命地抽着烟,吐起了烟圈儿,那些烟圈儿在她的嘴里吐出,在空气里上升,越升越大,大得不能看见就消散了。
我看她不说话,就又对她说,春天都来了,你还挡着我干什么,你去园子里看花吧,那些花儿和你一样美丽,去吧,我也不认识你,我认识苗苗,她一个人去看大海了。
女孩幽幽地说,你认识我。
我问她,我在哪里认识你?
女孩说,我一说名字你就能想起来。
我笑着说,你倒是说说看,让我搜索一下我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和你同名的。
女孩的双手又插进了口袋里,一副挑衅的模样,她说,我叫张朵。
我嘿嘿笑着说,你刚才就听见我说我要去找一个朋友叫张朵吧,你真丢人,张朵可是一个男人,你能叫一个男人的名字吗?
我等着女孩回答,可是女孩没有说话。
我又对她说,你在瞪我吗?
那我想对你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反正我也看不见。
女孩兴致勃勃地听着,她更陶醉了,几乎跳起了摇头舞,她的腿和身子动着,双脚却没有动,她的头发也开始动了。
我大声地对她说,你的头发为什么要遮盖眼睛遮盖脸,你以为这春天校园是拍国产恐怖片的地方啊!
女孩跳着回答我说,我的名字不叫张朵,我叫吴敬雅,反过来叫是雅敬吴。
两年之后,我在夜晚的校园里,碰见了吴敬雅。
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离开Z大学,离开那里的一切,奔赴北京。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站在那里,木偶一样看着吴敬雅,她已经不跳了,把烟从嘴上拿到了手里。
我拢了一把头发,对着她嘿嘿地笑起来,我听见她也在嘿嘿地笑。
我们的样子彻底迷惑了一个男学生,我眼角的余光看见他站在路边的树底下,等着看我和吴敬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并不讨厌这样的男生,我小时候也经常干这样的事情,看见谁吵架或者两个人面对着瞪眼,我就会躲在一边观看,我祈祷他们能够打起来,那样就更好看了。
但我长大之后是非常讨厌这样的事情的,这个男生的心态和我小时候的心态很符合。
我对吴敬雅说,把你的烟扔了吧。
吴敬雅就听话地把烟弹向路边的墙壁,那截烟头在空中倾斜着朝看热闹的男学生飞去,眼看就要上他的脑袋了,男学生的脖子往下一缩就躲过了烟头,那烟头在墙壁上火花四溅,然后消失。
男学生遭此一劫后,就兔子一样跳着逃走了。
我看见吴敬雅笑得肩膀都在抖动,我走过去,伸手把她的头发拢到了耳朵后面。
我再一次惊呆了。
我知道我会眩晕,我知道我会心跳,但还是比我想象的更强烈。
那张脸在路灯下,在小诊所的灯里,两次将我打倒。
那张无可挑剔的脸,完美而魅惑的脸。
整整两年,我都在寻找,都在默默地张望,到最后,我甚至就要遗忘了,她却突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知道我将注定迷失在她晶莹的眼睛里。
我的手颤抖着从她的脸上拿开,凝视着她。
我看着她问,我怎么会在这里碰见你。
她拿下耳机回答我,我也很奇怪。
我说,你从那以后没有再找过我。
她说,是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我看出你喜欢我。
我问,你很讨厌我吗?
她说,不是的。
我说,我找过你,但我没有刻意地去找你,我只是在校园里走的时候左右看看,没有看到你。
她说,你不经常在校园里走。
我说,是的。
她说,我老远就看出是你,你的头发更长了,好象比以前高了。
我说,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个时候病着,可能是弯着腰的。
她笑了笑说,你很向往北京吗?
我说,是的。
她说,我会请你去我家吃饭。
我惊喜地问她,你家北京的?
她点点头说,怎么,不像吗?
我说,不是,我第一次听你说话,就怀疑你是北京的。
她说,我家在团结湖住。
我高兴地说,那你以后可得照顾我。
她说,没问题,不过我今天晚上还没吃饭,你得请我吃饭。
我拉着吴敬雅的手走在校园里,我几乎忘记了一切的忧愁,甚至决定不那么着急去北京了,留下来等她回家的时候和她一起去。
我带她去了“三百”饭店,饭店的老板娘看见我,开心地吩咐服务员带我们上楼。
我们在玻璃雅间里坐下,她坐在我的对面,眼睛里流露出温暖的色彩。
服务员把菜单拿上来,我对她说,你随便点,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
吴敬雅看着我说,我觉得你这两年变化很大嘛。
我说,说说看。
她说,你是不是发财啦?
我说,没有。
她开心地笑着说,你不像是那个生病的男孩了,那时候他连医药费都付不起。
我嘿嘿笑了一下说,这两年写散文,在电台开了专栏,小赚了一笔,还有些存款。
吴敬雅把菜单推给我说,还是你点吧,我请你。
我说,你把我当吹牛大王了。
她说,点你的吧。
我当然不会忘记点烤鸭,我还点了两道名字很长,而且价格很贵的特色菜。
我对吴敬雅说,我们喝白酒?
她说,成,什么酒都成。
我为她满上酒后问她,北京的高等学府多如牛毛,北大清华什么的,你怎么不弄一个上上,跑这古老破败的城市瞎逛荡什么?
吴敬雅喝着酒说,说来话长,还是不说了。
我说,那就不说了,喝酒喝酒。
我过了一会儿又问她,你也不讨厌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找我,你怕我强暴你不成?
吴敬雅说,什么话,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觉得你太喜欢我,不敢呐!
她说完这句话开始拿眼睛瞥我,一脸坏笑。
我说,那今天晚上看见我还不躲着走,还拦住我干什么?
她说,冤家路窄,既然碰见了,就打一架好了。
我说,怎么打?
她说,你想怎么打?
我嘿嘿笑着说,说出来别生气。
她说,说吧。
我说,床上打。
吴敬雅乐坏了,她喝了口水笑着说,大色狼,我觉得那没什么劲。
我说,你不会性冷淡吧?
她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着我说,我命令你,马上给我闭嘴,小心我揍你。
我端起酒杯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北京女孩。
吴敬雅说,我可是人中豪杰,你别拿我和普通北京女孩比。
我说,那是那是,怎么会呢。
我问她,两年来都是有什么变化?
她说,分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手,考了几次试,面临毕业的危险,我真不想离开校园,我害怕到社会上去。
我开心地说,你现在单身呀?
她看着我说,对啊,怎么着?
我说,那我就有希望了。
她笑着说,你能有什么希望。
我说,这种希望只能到手之后才有意义。
吴敬雅说,到手,意义?
我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女朋友了。
吴敬雅笑了起来,我们喝着酒,她渐渐有些醉意。
我说,今天就喝到这里,改天接着喝,去北京我看就算了吧,我想留下来陪你。
吴敬雅说,你走你的,我随后就到,北京人话多,但心眼都不错,你不要认为他们是骗子。
我说,哪里话,你不就是一个出色的北京人吗?
最后我们走下楼,那顿饭还是吴敬雅请的,她把钱扔进去,老板娘找回了一把零钱,她是认定要请的。
我和吴敬雅走出“三百”一起往东慢慢走去,在一座桥上,我们站住,看着下面的河水。
我和她站在一起,她几乎和我一般高,头发被风吹起。
我对她说,你很漂亮。
她说,我知道。
我说,你就不能谦虚一下吗?
她说,本来嘛。
我问,你多高?
她说,不穿鞋1米74。
实在没什么话,我就问她,你喜欢我吗?
她说,不讨厌。
我说,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很兴奋。
她捡起一个石子儿扔下去,我没有看见任何动静,也许是马路对面的灯光照不到下面。
她趴在桥的栏杆上说,我看出来了,我比你大5岁,我今年25,你20,我不可能和你谈什么恋爱,我老得快,你最后也不会要我,我看算了,既然老天让我们又见面了,那就做个好朋友吧。
我说,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你了。
她有些烦躁,左右看看说,你别他妈那么煽情好吗?
搞得我想哭。
我说,那就不说了。
吴敬雅跑到桥那边去了,我跟着她过去,她蹲在一间房子的门口等着什么,我问她,你干什么呢?
她说,我看见一只老鼠跳进去了,等它出来我去捉。
我说,你肯定没有猫有耐性。
她摸出烟扔给我一根说,闲着没事,抽吧。
她走到我跟前把打火机给我。
我和她就蹲在那里抽烟。
我问她,你和你男朋友什么时候分手的?
她说,半年前。
我说,他现在在哪里?
她说,跑德国留学了。
我问她,也是在Z大学毕业的吗?
她说,是,要不是为了来找他,我到这破地方干什么。
我说,半年来你寂寞吗?
她说,寂寞不寂寞无所谓了,只要我愿意,有的是男孩子,可是我讨厌一切,我也不上课了,也不学习了,整天瞎混。
我不想提起她的伤心事,就没有再打听她和她男朋友从前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把吴敬雅送到南门外的一个路口,我们互相记了手机号码。
她对我说,看见这个路口了吗?
拐进去,一直走,到头看见湖,右拐第一个胡同儿进去,一直走到头,看见一家院门,门是木头的,我就在那家院子里住。
我笑着说,你不怕引狼入室吗?
吴敬雅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哥们儿,你就别再浮想联翩了,成就做我弟弟,不成就别去找我。
我说,那我不去找你了。
她说,那是你的事,我只是把话说到前面。
她不让我往前送了,她说,你一推门,准有一帮小狗围着你叫唤,我就在二楼中间的那间房子里住,你叫一声我的名字我就能听见,我一般不出门。
我说,我知道了。
吴敬雅重新把耳机塞进耳朵里,掏出CD机打开对我说,我走了,记得找我啊。
我看着吴敬雅走进了胡同,很多灯照着她,也照着别的行人,她的身材好得让人看一眼就能牢记终生。
她穿着肥大的裤子,趿拉着拖鞋,穿着小巧的花外套,她穿什么衣服也遮挡不住那身体的美丽线条,令人揪心的美丽。
我在想,我为什么还能碰见吴敬雅,我就要走了呀,她家还是北京的,我就要去她的家了呀,我能爱上她吗?
我已经爱上她了呀,她愿意接受我吗?
在她的面前我没有一点把握,她很狂妄,显得很自我,我能忍受她吗?
两个性格相似的人能彼此容忍吗?
我能娶她吗?
我的这一辈子就和吴敬雅过了吗?
我会后悔吗?
她会后悔吗?
这一切显得遥远吗?
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无用的事情,可是我失眠了呀,我很久没有失眠过了,失眠的滋味真好,我打开录音机,在如水流淌的音乐中想她。
我竟然又看见你了,吴敬雅,我竟然又看见你了。
你是蝴蝶吗?
是飞在春天的蝴蝶吗?
你不需要在你忧愁的时候有个扮演猴子逗你开心的房小爬吗?
你很勇猛,不会受到外部的侵袭吗?
你不需要一个甘心为你付出一切的房小爬吗?
为你去死?
我不会多考虑一分钟,但我死的时候会担心你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得到幸福,要是我能得到确定的回答,要是我知道你会幸福,我就去为你死好了。
我可以为你死一万次,如果我有一万条命。
实在无法入睡,天马上就要亮了,我爬起来写日记,把她昨天晚上说过的话全部记成文字,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起来她曾对我说,让我为她写歌词的事情,我没有尝试过写歌词,那就胡乱写两句吧,反正我也睡不着了。
天亮了,亮了很久也没有阳光,是阴天。
我没有写出歌词。
我撕了很多稿纸,我发现自己内心的歌词不能统一到纸上,我变得无比忧伤。
我一直在努力,再见到吴敬雅之后我必须交给她一首歌词,不论她以后会不会把这首歌词唱出来,我一定要写。
我很快就写成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找太阳》我把这首歌词抄录在下面。
第一段:疾病是天堂,你使我向往。
如果你小巧的花衣裳,可以将我的悲伤阻挡,我就算没有翅膀没有腿也会爬到你身旁。
第二段:碗中的白开水,你眼中含着糖。
要是春秋冬夏没有太阳,可以将我们的生命照亮,我就算不能行走也要驮你去缓慢地飞翔。
末尾:找太阳,找太阳,找太阳,找太阳。
那些五彩的光芒,那些可以让你活得长久的光芒啊,你是我此生的梦想,梦想。
我在等着吴敬雅给我打来电话,我甚至不敢轻易给她打电话,我怕她会被任何声音惊扰。
三天后我去找她了,我按照她指引的路线,很快就找到了她住的那所院子,我刚一推门,一群白色的小狗就朝我大叫着扑来,但它们都没有咬我,它们的主人从客厅里出来,那是夜晚,我看不见主人的脸,是个中年男人,他问我,你找谁?
我说,吴敬雅。
他说,你找唱歌的那个漂亮女孩。
吴敬雅打开门,站在楼上的栏杆前高兴地叫我的名字,房小爬。
我就走上了铁楼梯,那铁楼梯颤巍巍的。
吴敬雅把我带进她的屋子里,关上门回头问我,你怎么才来找我。
我说,你希望我什么时候来找你。
她说,我以为你第二天就会来,结果我等了你一天你也没来。
她的屋子挺乱,床铺上堆着衣服和零碎,桌子上堆着书。
她有些慌张,她说,我没来得及收拾屋子。
我对她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
我就坐到书桌前看她的书,她竟然喜欢哲学,尼采,黑格尔,亚里斯多德什么的搞了一片。
我把歌词从口袋里掏出来给她,她看过后对我说,我很喜欢,写给我的吗?
我说,我以后还会再写,我写得不多,所以可能写得不好。
她说,我认为很好。
我又看见她脚上穿的那双拖鞋,只有右边那只才有一个塑料狗的拖鞋。
我问她,你左脚上穿的拖鞋也应该有一个塑料狗。
她说,是的,我把它拽掉了。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我觉得两只狗会打架的,我喜欢安静。
她说,我给你唱首歌吧。
我说,唱吧。
她就为我唱了许多伤感的民谣。
我一直看着她,我想去抱她,她唱完歌以后对我说,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问,为什么?
她说,你让我不安。
我问,你喜欢我吗?
她说,喜欢。
我说,那为什么不让我看你?
她说,你想看就看好了。
我说,你怎么突然害羞起来了。
她说,我没有。
她再也不敢正面看我了,她去摸口琴,摸小提琴。
她说,我都要老了。
我大声说,你永远不老,你多漂亮啊,你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
她笑着说,你哄十七岁小女孩呀,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真的。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心中憋闷的气息开始消散,这个叫吴敬雅的北京女孩,她刚才亲口对我说,她喜欢我。
我这时去抱她,去扒光她的衣服,她不会拒绝的,她在期待我。
她那天晚上在胡同口说的全是废话,她也许已经忘记了。
我想守着她。
她一定想不到我很快就会离开她的小屋,我将回到铁牛街22号我的小屋去。
我站起来,她开始紧张地用手去拿桌子上随便一本什么书,她以为我会去拉她站起来,以为我会去抱她。
我觉得我可以用一生时间去爱她,叫吴敬雅的女孩,我爱你。
我不会稀罕这一刻,我要掠夺她的一生。
我想让她永远地属于我。
我已经无比地疲惫,不想再往前走了,她就是我一生停留的地方。
我停在她那里,就要掌握她,给她幸福和限制。
吴敬雅抬起头看我,用她瞬间柔软下来的眼神看我,她微笑着,不说话。
我对这个女孩说,吴敬雅,我走了。
她分明不相信这句话,她说,你不是刚来吗?
你再坐会儿好吗?
我说,我还是走吧,你早点休息,多看书。
这个漂亮的女孩也懂得爱情,懂得那个两年前一个病恹恹的男孩对她的眷恋。
她只好站起来准备送我,她抢在前面开门,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开门,她回头看着我说,对了,你小时候遭难的故事只给我讲完了一个,另一个你也给我讲讲吧。
我说,你让我现在讲吗?
她说,对,现在讲。
我说,我现在不想讲,我要走了。
吴敬雅干脆倚着门看着我说,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我说,是。
她说,那好,我要你留下来陪我一会儿。
我说,我给你时间,你好好想想,我不愿意陪你一会儿。
她说,你想陪多久?
我说,是一辈子。
她看着我,再看着别的地方,她说,你还小,你最后不会要我的,我不想再受任何伤害。
我说,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吴敬雅打开门,我走到她的跟前,她身上那种好象牛奶的气味我再次闻到了,我有些发疯,我真的不想走,真的想立即抱着她,让她软在我的怀里。
我对她说,改天见。
吴敬雅想下楼送我,我说,太黑了,楼梯不好走,你回屋吧。
我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走到院子里,那群小狗又围住了我。
我抬头看吴敬雅,她还在那里看着我,屋子里的灯照着她的后背,她整个身体好象背对着晨光。
她周围一片金黄。
我大声说,再见。
她说,给我打电话。
我踢开了狗,走出了那条胡同儿,走上大街,走回铁牛街22号我的小屋子,我的大屋子。
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开心,我在我的屋子里听着音乐跳舞。
我不会跳舞,我胡乱扭动。
我关上窗户,我打开窗户。
我发现自己原来什么都可以干。
我真的很开心。
20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开心。
我边跳舞边脱衣服,我跳着人们所陶醉的“脱衣舞”我脱得非常迅速,一会儿就脱了个精光。
我晃荡着肥大的阴茎,夜色深沉,我光彩照人。
我终于等到了吴敬雅,我几乎遗忘的姑娘。
我担心自己熬不到天亮,她是那样的令我着迷。
为什么,这个讨厌的世界。
为什么,我。
我关掉录音机,关掉灯,我躺倒在黑暗里,我听着寂静的声音。
我能够听见寂静的声音。
当我就要离开这片田野的时候,却发现我渴望的种子已经发芽,我想住下来,去浇灌那些嫩芽。
我想大把地收获粮食。
爱情的粮食--吴敬雅。
风从窗口闯进屋子,吹动我的脸。
风带来了吴敬雅想我的消息。
我又失眠了。
我想听到她的声音,想看到她的那张使我迷失的脸庞。
我可以无限漫长地去热爱她,可以为她付出我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