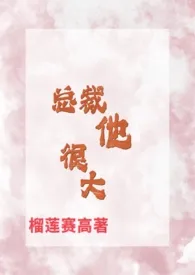骨节撞击人体,发出一声闷响,徐意丛的头皮蓦地一麻,猛地推开挡路的人走过去,张嘴没发出声音,攥紧了拳头才逼自己出了声,“别打了,徐桓司。”
她试图拉架,但那两个人谁也没停手,徐桓司还推了她一把,他这一推弄得她一个踉跄,自己也露了空门,又被许蔚程一脚踹在腰上。
徐意丛的腿还是麻的,咬牙转身去一瘸一拐地拿来老查理手里的酒杯,又一瘸一拐地走回来,许蔚程正把徐桓司扑倒在地挥拳,她抬高杯子兜头淋下,香槟酒全数洒在徐桓司脸上。
两人扭打的动作一顿,徐意丛已经劈头盖脸地把香槟杯扔到了地上,细长的杯子碰到了徐桓司的额头,又从他额角滚下去,清脆地碎成了片,“徐桓司,你没听见我跟你说话?”
徐意丛脸色煞白,牙关都在抖,许蔚程没再动,定定望着她。
她飞快地弯腰把徐桓司拖起来,香槟酒混着血丝沿着他的下颌线滴在她手上,她揪着他的领口,仰头盯着他的眼睛,“走。回家。”
徐桓司眼里的戾气没散,跟她对视的时候下颌线紧紧绷着。她确认他听见了,就松开手,“走。”
徐桓司的眼神又扫到许蔚程身上。
他们的脸上都全是伤口,身高也相仿,但徐桓司的目光渐渐一冷,随即带出惯有的居高临下的审视,许蔚程擦了一下脸上的血,无所谓似的看回来。
侍者周到极了,送来包和外套,徐意丛一一接过,“徐桓司,你不走就再也别回来。”
她没再等他,自己下楼。
徐桓司接过侍者递过来的餐巾,擦掉唇角的血,向查理抱歉地一颔首,转身快步跟下去,边走边脱掉破了的外套,扯开松了的领带,然后追上去替她提裙子。
徐意丛高跟鞋穿得腿疼,就脱下来拎在手里,光着脚上车,靠车窗坐着,一路都没说话。
徐意丛是真的生气了,她真的生气的时候就不说话。
陈昂被他们进门的动静吵醒了,溜达过来,“嚯,怎么了这是?遇上歹徒了?哎,丛丛你今天挺好看的呀。”
徐桓司只不过是愿意跟她走,自己火气也还没消,面色不善地点点头。徐意丛没搭话,头也不回地提着裙子上楼去了。
徐意丛换了衣服洗了澡,黑着脸擦头发。陈昂早习惯了他们吵架,不怕死地敲开门探进头来,“医药箱在哪啊?我找不着。”
她把毛巾一丢,蹬蹬蹬下楼去找出医药箱,提着上楼,径直推开徐桓司的门。
徐桓司皱着眉头叼着烟,正大手大脚地开着水龙头手上的伤口,打算把血冲干净就算完。
听到动静,他飞快地把衔在嘴里的烟头摘下来在水里一冲,丢进垃圾桶,眉毛都没抖一下。
徐意丛目睹全程,面无表情地等他解释。徐桓司很镇定,真诚地说:“就一根。”
徐意丛上前关上水龙头,打开医药箱拿出消毒棉球。徐桓司接过去,把手上脸上的血口擦了一遍,就当收拾完了。徐意丛说:“脱掉。”
徐桓司像是消气了,甚至心情不错,跟她东拉西扯,“最近没练,别看了。”
徐意丛瞪了他几秒,没消气,也没发火。
他只好把衬衫脱掉,转身过去,让徐意丛替他处理背上的划伤和淤青。
徐意丛下手重,在结实的背肌上重重一按,徐桓司对着镜子控制表情,龇牙咧嘴地对她笑笑,“……专业。”
徐意丛泄完了私愤,把他丢在卫生间里,去沙发上拿起他的手机,给医院打电话预约明天的检查。
大圣撅着毛毛屁股跳上沙发,在她旁边挤暖和,被徐桓司踢下去,他在沙发另一段坐下,握住她的小腿,找到那一小片淤青,轻轻揉一揉。
小腿被揉得舒坦,逆来顺受的徐桓司也的确清热降火,加上这个姿势极其适合行凶,徐意丛挂掉电话就踢他一脚,终于骂出口:“他踢到你的胃怎么办?徐桓司,你就作死吧,你等着看,你死了我就去找男人练手,十六个脱衣舞男,十六个硅谷总裁,十六个衣冠禽兽,各种类型走一圈,把你忘到九霄云外。”
徐桓司闷闷笑起来,“好,我等着看。到时候你再好好跟姓许的聊一聊,再考虑一下。”
提起许蔚程,徐意丛面色不善地试图把脚抽回去,被他环住脚踝扣在怀里,她挣扎了一下,“你说什么呢?”
卧室里灯光如昼,徐桓司握着她脚腕的五指微凉,“他说圣诞节前是他让人划你脖子的?那要是句真话,”他的神情是平和的,甚至有些冷,“你早就看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