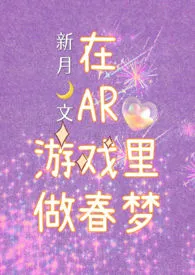俩人从山上的石阶走下来,到一座重檐神殿下面躲雪。
徐妙锦伸手拍打着身上的落雪,又把玉手伸到朱唇前面,呼出一口白汽,轻轻搓了一下手,叹道:“这世上真冷……”
不仅冷,而且这个地方很孤寂,雪落几乎无声,周围不见人影。笼罩在大雪纷飞之中,他们仿佛已被世人遗忘。
朱高煦听得徐妙锦的轻叹,侧目看到她的侧脸。
白净的脸看起来很清纯,眼睛却生得妩媚,眼神里带着幽深的苦楚,这一切矛盾的东西都在那张秀美的脸上融为一体。
……不止是她这么感觉,朱高煦也感同身受,偶尔能得到几分好意的慰藉,也往往转瞬即逝。
但朱高煦觉得自己的内心要比徐妙锦强大……他才不信什么道德礼教,经过了后世崩坏而多样的价值洗礼,他完全不受一般道德所制约,除非违反规则时、会受到实际的严惩。
他终于忍不住说道:“小姨娘可知,咱们遵从的这些礼法,只适用于庶民?”
“甚么?”徐妙锦困惑不解地转过头来。
朱高煦想了想,便道:“小姨娘先前说死后要下地狱,真的多虑了,完全不该成为你的心结。”
徐妙锦默默地听着。
朱高煦想了想又道:“你注意过燕子窝么?燕子孵育小燕,并非为了反哺,却是天性。小燕长大之后,母燕会把它卖了?”
“鹁鸽呼雏,乌鸦反哺,仁也。”徐妙锦轻轻念道,“乌鸦就会反哺。”
朱高煦竟然被噎住了。
徐妙锦看了他一眼,无奈道:“我不是想故意反驳你。便是用禽类比拟,可人非禽兽,岂能相比?”
朱高煦道:“人比禽兽狠多了。猛虎虽猛,不会奴役牛马、甚至别的老虎罢?”
徐妙锦抬起头打量着朱高煦,“你很不一样……我总觉得高阳王身上有种别样的东西。”
朱高煦便不吭声了。
……沉默稍许,徐妙锦忍不住又问:“去年除夕,我记得好像没说漏什么要紧的话,高阳王是如何察觉的?”
朱高煦便坦然道:“那晚小姨娘要自尽,在我看来非常之蹊跷。你的处境应该有很多路走,不至于到那一步;而且小姨娘聪慧,并不是那种见识狭隘、一点事想不通就要寻死觅活的人……那么,你肯定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
但是没几天,我再见到你,你又变了个人似的,全然不像走入绝境的样子。
后来也没听说你出了什么事。
此时我又接连得知了续空被逮、章炎刺杀续空之事。
于是我先假定你是和他们一伙,这一切蹊跷,不是都说得通了?
先是续空及其家眷被查出来,极可能供出你,所以你很担心恐惧,才会想一死了之;后来续空被杀,燕王府追查的线索一断,你就不必再担心了。”
朱高煦顿了顿,又道,“但假定不能说明什么,必须要验证。所以我先后在燕王府北门、池月观设点,暗中亲自察探。
直到今天,发现你在帮助章炎的儿子,于是便得到了验证……章炎杀续空灭口,就是要保护你或别的奸谍;你从中受了益,所以才会帮助章炎的后人,以为报答其恩。是这样?”
徐妙锦听罢,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整个燕王府的人都没想到,高阳王心思却如此缜密,我无话可说,只能服气。”
朱高煦强笑道:“那是因为燕王府其他人,没能撞见小姨娘跳井。”
徐妙锦轻声道:“高阳王也不是撞见,你是跟来的。若非一直在意我,又怎能发现我那天有异?”
朱高煦点头赞同,他忽然想起去年除夕晚上她说过一句话:没人在意她。
这时他发现,落在自己肩上的雪花,感受到体温的暖意,已经融化了,肩膀上的布料变得湿漉漉的。
徐妙锦仰头观赏着空中的飘雪,问道:“你既然只是猜测,为何能追查我几个月?若只是担心我危及燕王府,又为何不索性告诉别人?”
朱高煦心里感觉似乎能回答,却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解释。
于是他便反问:“还有一处我不明白,既然续空家眷被逮,你留下来已十分危险,为何不干脆逃走?”
徐妙锦转头看了他一眼,那张原本应该纯真的年轻的脸上,却露出了心酸无奈:“有些内情,你不明白。”
“什么内情?”朱高煦脱口问道。
徐妙锦只是摇头,又苦笑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朱高煦见她原本朱红的嘴唇都乌了,情知外面严寒,人站定下来更冷。他便道:“走罢,咱们回去了,在外面呆得太久怕染上风寒。”
徐妙锦点头,“咱们还是分开走,你先走。”
朱高煦伸手做了个动作,“我怎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徐妙锦便道“告辞”,先往屋檐的一边走去。刚走了一段路,她忽然又回过头来,“高阳王,你真的要为我保密?”
朱高煦点了点头。
望着徐妙锦的背影消失在墙角处,他也缓缓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心道:我为燕王府做得贡献不少了,利益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啥要为整个燕王府的利益,牺牲小姨娘?
朱高煦从寺庙偏门走下山,在路口找到了王贵。
他挑开布帘,见王贵缩成一团在车厢里簌簌发抖。
王贵见着朱高煦,便抬起头来:“王爷总算回来了,若再不来,王爷就只能瞧见奴婢冻僵的尸身啦!”
“去前面赶车。”朱高煦爬了上去。
王贵缩着脖子先下车,再到前面拿起鞭子,“啪”地甩了一鞭,回头道,“王爷见着那穿青色斗篷的人了么?”
“见着了。”朱高煦道,“此前那件事已弄清楚,你不必再查。”
“是,王爷。”王贵应答一声,便闭了嘴。
朱高煦渐渐发现,虽然王贵以前十分普通,但这个宦官有不少优点。比如嘴巴算严实,而且主人不说的事儿,他不会问,便省去了解释的麻烦。
马车“叽里咕噜”在路上行驶,刚下的雪还未堆积,便被碾进了泥土,让道路变得有些泥泞。
王贵的声音又随口道:“那事儿王爷办了几个月哩。”
连朱高煦自己也说不清楚为啥那么执着。
记得前世有一次被人坑了,输了很多钱,他一肚子愤恨,便想报复。
他先在暗地里跟踪观察那人,以寻找机会。
但只坚持了三天,就气馁放弃了。
愤恨的情绪虽然一时很强烈,却往往难以持久,毕竟得不到任何好处,缺乏动力。
王贵赶着马车返回北平城,然后径直回郡王府。早上出城时很早,现在还不到中午。
外面的天气很冷,雪一直在下,完全没有消停的迹象。朱高煦遂躲进了自己的房中,叫奴婢烧了木炭取暖。
红红的炭火,温暖的房间。但此时前线的将士,恐怕就没那么好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