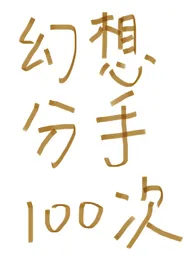晚膳过后,杜竹宜在闺房中来回踱步,寻思是否该去找父亲,问问他可知母亲为何要让她去见那弗居大师。
不料她心念着的人,倒先一步自行来了。
“父亲,您怎的来啦?”
杜如晦嘴角噙着笑,朝她摆摆手,转而对一旁侍立的翠儿说道:“我有事情要与小姐说,你先下去。”
翠儿昨日才见老爷将小姐送回来,今日又见着老爷亲自来找小姐,心道这两日老爷来得倒是比这两年还多。
她瞧一眼自家小姐,见她没注意自己,便躬身应诺,接着退到门外去了。
及至翠儿退出厢房,将门带拢,杜竹宜仍眼波柔柔地瞧着杜如晦,没回过神来。
父亲温和儒雅又不容拒绝的大家长做派,从前她既敬佩又孺慕,如今再看来,却引得她心脏怦怦乱跳,既是着迷又是折服。
“怎的,心肝儿不欢迎为父?”杜如晦趋近女儿身前,笑着轻声问道。
父亲突然贴近,温热的气息拍打在脸侧,让杜竹宜脸一下羞红,磕磕巴巴地回道:“怎么会,女儿方才正想着父亲,父亲就……”
话说出口,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杜竹宜羞窘万分,抬头偷眼望父亲一眼,又羞怯怯垂下头,双手迭在身前绞着手指。
杜如晦被女儿娇羞的模样逗得开怀,朗声一笑,捧起她纠结着的一双柔荑,爱怜地柔声说道:“心肝儿能想着为父,为父心中才觉安慰些,为父可是想了心肝儿一天。方才用膳时,看着心肝儿还想着心肝儿…”
他这一连串的心肝儿,叫得杜竹宜面如火烧、眼含春水。
若不是她亲身体会,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端方稳重的父亲,说起情话来,会让人如坠蜜罐。
半个时辰前,一家人用晚膳时,那冰火两重天的感受,仍清楚分明。
一边是父亲脉脉温存的目光,三不五时地将她牵缠,让她既喜且羞、如获至宝;一边是母亲微带忧愁的视线,若有似无地纠结于她,令她暗暗心惊、殊感愧疚。
但此刻,她仿佛明白了诗人笔下,“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的涵义。
哪怕一生都要背负着愧疚,她也只期盼能与父亲,倾心相爱、结爱至深。
杜竹宜咬了咬唇,甜糯糯说了句,“宜儿亦是如此”,身体软如一团棉花般靠倒进父亲怀中。
“不请为父坐坐,就站在这里说话吗?”
发觉此刻与父亲仍站在闺房门口,杜竹宜“啊——”的一声,羞红着脸小声说:“女儿不是有意怠慢,父亲随孩儿来。”
说罢,便拉着杜如晦往内室而去,引着他坐在对着她绣床、靠着窗的罗汉塌上。
杜如晦坐下后,她又走到外间盆架处,拧条湿帕子来,细致入微地为父亲擦脸,擦完脸又擦手,跟着又为父亲上了茶。
待到她再要去张罗果盘时,杜如晦忍俊不禁,叫住了女儿。
“这些便够了,心肝儿,坐到为父这儿来。”
无论是作为他娇养在深闺的女儿,抑或是他牵肠挂肚的心仪之人,他都并舍不得她服侍自己,只是看她做得认真,他便也看得有趣。
恍惚间,更有一种,她是迎他归家、为他操持的小妻子的美妙联想。
这种关起门来父女做夫妻的日子,在他决定彻底占有她的昨日,他便已打算为自己谋得了。
杜如晦如是想着,摊开双手,对女儿敞开怀抱。
“心肝儿,到为父怀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