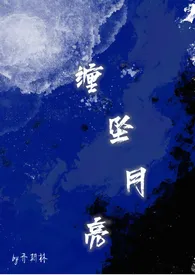杜竹宜原以为,父亲将那百般折磨她的毛笔拿走,她便能浑身清爽,可当真抽出,却发觉那古怪滋味,对她内里有致命诱惑——
那豁豁辣、酥酥麻的接触失去后,花心里头,是漫无边际的空虚!
被那笔毫下过辣手的肉瓣、宫颈纷纷抗议,命她将它们的新玩伴速速挽回!
眼角呛出一滴饥渴的泪花儿,杜竹宜带着哭腔求道:“父亲,不能,不能,宜儿不能没有……”
她焦急哭求,一面双手死命扯着大小阴唇,穴口洞开,微微蠕动,一点嫣红媚肉外翻,沾着滴滴淫液,似一朵杏花微雨,清丽又靡艳。
杜如晦凑近,一动不动地盯着女儿娇艳面庞:“心肝儿,不能没有甚么?”
杜竹宜心颤了颤,眼神聚焦,看着父亲近在咫尺、放大的脸上沉肃的眼,直觉不能说毛笔,呜呜咽咽道:“不能没有父亲……父亲,插插宜儿,宜儿为父亲入墨……父亲奖励宜儿,快来…插插宜儿,可好?”
“心肝儿做得很好,的确当奖,父亲便为心肝儿,换个大的?”
“大的?”杜竹宜稍愣了楞神,是这个大的,抑或是那个大的呢?
好过甚么都没,便不多想,“要的……父亲……求求,求求父亲,快给了宜儿罢!”
杜如晦双眸微眯,喉结上下滚动,平静面容下是欲壑难填——
他不再言语,回到女儿腿间,复又俯身倒腾起来。
杜竹宜斯哈斯哈细细声抽着气,太刺激了!
直径有她两指宽的大号紫毫,钻进她花心之中,肉瓣每一道细微沟壑无不被照顾到。
热辣辣的微针般刺痛,在她嫩滑的穴道中炸开,她的颅内,也像炸开无数火星子,劈里啪啦,此起彼伏……
但她对这疼痛并不畏惧,因对其并非一无所知,她知道,当它的尖毛舔到她花心最最深处时,会有多么令人无法自拔的快感!
另一支紫毫被父亲握在手里,刷在她的阴沟上、阴道里,时不时扫过她扒开穴口的手指,令她不能忽视,她是多么饥渴淫荡地、渴求着父亲的亵玩……
“嗯嗯……啊啊……”她婉转呻吟,凝成一些纤细的音调,时起时落,不绝如缕,骤然拔高,“啊——”的一声,如冲出悬崖,瞬间掉落,而后意外平缓着陆,归于安稳,脱力地一句“到了……”
杜如晦松开那管大号紫毫,只剩一小截暴露在女儿穴口,嘴里也不知是叱了句“妖精”、还是“要命”,右手握住自己那根阳具——女儿高潮妖娆美丽的样子,刺激得它硬邦邦地高高翘起,顶端还流出前液。
他快速撸动两下,却不顶事,他那根狰狞无b的物什,叫嚣着要进入女儿温润紧致的穴中,顶撞她、冲击她、射爆她!
他干脆丢开手,右手拿过那管中号紫毫,汲满女儿方才高潮时又喷射出的许多淫液,而后左手把着女儿腿根,将女儿腰肢折弯,娇体轻轻抬起,对着那朵早被淋得靡艳又娇羞小雏菊,细细描绘起它的花痕。
小雏菊敏感异常,立时像含着东西在吃的小嘴儿一般,包口包嘴地颤动、蜷曲、痉挛……
似是经受不起玩弄,又似是扭捏着闹别扭——怎的才想起玩儿它——
淫荡,太淫荡了!
“啊!啊啊啊!”杜竹宜原还沉浸在泄身的绵绵余韵中,红彤彤的荔枝眼儿睁得又大又圆,不可置信般地弹坐起身,那笔毫舔她小穴也就罢了,如灵活湿滑的蛇信子般舔她菊门?
痒,痒,痒!
痒到极点!
她才知道,原来痒b痛,更令人难耐!






![《男主男配们都黑化啦[快穿]》小说大结局 豆小腐最新力作](/style/img/thumb.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