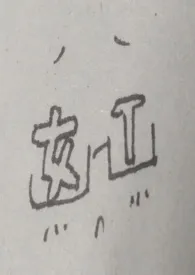金陵,客栈二楼
顾若清这会儿已经听到下方的动静声音,来到楼梯上,静静伫立,凝望那少年。
先前她其实是要约这位严以柳晚一些来的,也就是带晌午的时候过来,不想竟是提前到了,分明是想要等候着自己。
贾珩也没有多说其他,打量了一眼蒙得严实的魏王妃严以柳,温声道:“魏王妃,在下有事先告辞了。”
毕竟男女有别,他也不可能一直与魏王妃走的太近。
否则,容易引人疑惑。
难不成,真就王妃收集者?
也不能总是得住老陈家欺负。
“子钰慢走。”魏王妃严以柳声音清冷中带着几许温和,称呼不自觉由卫国公转变成子钰,目送着那少年转身离去,斗笠下的清眸闪了闪,若有所思。
听说北静王妃先前就有不孕,还是贾子钰寻了游方郎中才诊治好的,她或许可以借机问问他。
想了想,忽而唤住贾珩,说道:“子钰,我有一事请教,未知子钰可否有空?”
贾珩转过脸来,怔了片刻,行至近前,说道:“魏王妃可还有事儿?”
严以柳声音清冷中带着几许浑金璞玉的金石质感,轻声说道:“我先去见一位朋友,子钰可否午后的未时在城中的东篱居茶楼等我,我有事相询。”
反正正如他所言,她从咸宁那边儿论起,与他也是一家人的吧。
贾珩心头有些古怪,正如与这魏王妃保持距离,点了点头道:“那午后再说,魏王妃先走。”
严以柳闻言,心头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暖流,说道:“多谢子钰了。”
眼前之人虽然与父王不睦,在政见上也屡有争执,但其实并未主动加害过父王,反而父王太过贪嗔痴怒,平常多有愤恨、加害之举。
然后,在贾珩走后,严以柳在侍女的陪伴下,登上酒楼二楼。
这位丽人沿着木质楼梯拾阶上了二楼,来到约定好的厢房,当然是另外一座包厢,而顾若清显然是有些懒得换地方。
这位身形苗秀、矫健的魏王妃,进入包厢之中,就将头上戴着的斗笠摘了下来,放在一旁的小几上,眺望着外间的金陵烟雨。
此刻,春雨繁密,微风和煦,斜风细雨中,远处的屋檐房舍影影绰绰,如笼薄雾。
严以柳轻轻叹了一口气。
顾若清想了想,等了一会儿,也转而去了约好的包厢。
严以柳在侍女小梅的侍奉下,品着茶盅,只觉阵阵清香袅袅而起,流溢于鼻端,沁人心脾。
伴随着脚步声响起,只见顾若清缓步而来,面容清冷如霜,柔声说道:“魏王妃今天来这般早?”
严以柳放下手里的茶盅,连忙起得身来,抬眸看向那少女,清冷声音中带着亲近:“可是顾先生当面?”
顾若清点了点螓首,打量了一眼严以柳,在其两道英眉下的目光停留了下,温声道:“魏王妃,请坐。”
这魏王妃不愧是将门虎女,眸光明亮,全无病弱之气,从面相来看,倒不像是难孕子嗣的样子。
说着,顾若清落座下来。
这会儿,严以柳打量着那容颜绮丽,宛如昆仑雪山绝巅雪莲清冷的丽人,低声道:“姐姐说顾先生您擅长岐黄之术,精于此道,还请顾先生帮着我诊治一番。”
其实,心头有些怀疑这位容颜明丽的女子,能否诊治她的病症。
顾若清柔声说道:“王妃客气了,我也只是略通此术,不过可以帮着王妃看看。”
严以柳点了点头,道:“有劳顾先生了。”
双方初次见面,大抵还很是客气。
顾若清开口问道:“未知王妃先前可寻了其他人诊治?”
严以柳想了想,说道:“寻了其他人诊治,最近也在煎服汤药,那位郎中说我年少习武,气血旺盛,乃至影响孕育子嗣,倒是与京中一些名医之言大差不差,倒也是个有本事的。”
顾若清点了点头,声音清冷说道:“他这般诊断倒也没有出错,不过,气血旺盛,也未必不能降服、平抑。”
“他也是这般说的,故而给我开了一个方子,用以平伏气血,蕴养生机。”严以柳清眸平静,似说着别人的事儿一样,语气缥缈。
但愈是那样,眉眼间的哀婉气韵却无声散发,让人心神一动。
顾若清柳眉挑起,眸光盈盈如水,轻声道:“其实,生孩子,也未必是女人之故,可能是男人的问题,魏王妃可曾让魏王寻太医诊治过?”
严以柳摇了摇头,面色微顿,清声说道:“天潢贵胄身份不凡,也不可能动辄去延请太医诊治,况且传至外人耳中,也难以道明缘故。”
事实上,魏王根本不可能怀疑自个儿的身子出问题,更不可能去请太医诊治,这要查出自己是不育,什么东宫之位,想都别想了。
所以,第一时间就觉得是魏王妃严以柳的问题。
而,这个时代的女子,纵然婚后无子,也多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顾若清点了点头,目光有些同情地看向那丽人,柔声道:“王妃,我先给你号号脉吧。”
严以柳应了一声,然后伸出胳膊递给顾若清,藕臂如雪,白腻惹目。
顾若清探出一只纤纤素手,将手指搭在严以柳的手腕上,清冷明艳的玉颜之上渐渐现出思量。
顾若清还真通岐黄之术。
顾若清转而又凝眸看向严以柳,询问了一些比如第一次天癸来时是什么时候,还有最近的月信又是什么情况。
顾若清默然片刻,目光笃定地看向严以柳,幽幽说道:“王妃身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严以柳:“……”
所以,这不是她的问题,而是……王爷?
顾若清柔声道:“起码从目前来看是这样,先前那位诊治的先生,想来也知道原委,但碍于情面,不敢直言相告,王妃心头还当有数。”
不管是为尊者讳,还是不敢去联想,总之,一些郎中的确没有将不孕的原因推到严以柳身上。
严以柳闻言,心湖中恍若落下一颗大石,波澜掀起,两道细秀柳眉凝起,心神已是震惊莫名。
所以,这一年多来所有的委屈,一年多来的误解,一年多来的冷眼,所以都与她无关吗?
念及此处,少女心头既是心酸难过,又是解脱和欢喜,但过了一会儿,就有些茫然。
其实,严以柳早就怀疑了,但也只是在心头泛起嘀咕,不敢直言相询魏王,更不敢说让魏王看看郎中。
除非,再纳侧妃,仍然无所出,那时魏王才会反思到自己身上。
顾若清朗声说道:“王妃,还是让魏王请郎中诊治一下,更为确证一些。”
严以柳这时反应过来,眸中似有泪光点点而闪,说道:“多谢顾先生。”
顾若清轻声道:“不过王妃的确是气血旺盛,需要稍稍平伏气血,那位郎中给王妃所下之方,倒也没有出错,只是子嗣艰难,也并非一人之因,王妃也不要太过自责、忧虑了。”
所谓气血旺盛,自然是后世某音评论,从气色而看,总有一种姨妈量大的健康之美。
而顾若清也从其他方面佐证,终于断定,眼前这位魏王妃身上并没有什么疾患。
“多谢顾先生。”严以柳说着,看向一旁的小梅,说道:“小梅。”
这时,小梅从袖笼中取出银票,从面值上都是大额。
顾若清却摆了摆手,晶莹如雪的玉容上满是坚定之色,清声道:“王妃无需如此,只是帮王妃探明病因而已,王妃如想顺利诞子,还是从魏王那边儿入手才是。”
她也有些奇怪,这天家怎么如此子嗣艰难?想来宫中怨气太重,阴气汇聚,是故子嗣艰难?
严以柳点了点头,美眸凝露,目中却若有所思。
王爷现在正在京城纳着侧妃,只怕还在想着绵延子嗣的事儿,到时候就真相大白了。
念及此处,严以柳眸光怔怔失神,面容忧色浮起,芳心深处却不由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当初王爷娶她过门,更多还是看在父王能够在嗣子之位上有所助力,如今父王因罪夺爵,只怕王爷更为不将她放在眼里了。
念及此处,严以柳心头不由生出一股怨怼来。
顾若清秀眉弯弯,玉容微顿,明眸莹润如水,宽慰说道:“王妃也无需忧虑,王妃还算年轻,等魏王诊治过,痊愈以后,两人尚有转圜之机。”
大抵是圆你妈妈梦之类的安慰话语。
而后两人叙了一会儿话,而后严以柳这才起身告辞。
……
……
金陵,晋阳长公主府
贾珩在几个锦衣府探事的陪同下,回返晋阳长公主府上。
而贾珩返回金陵的消息,却因为郝继儒的孙子被带进锦衣府,再次不胫而走,让金陵官员心头一震,惊疑不定。
这不是刚刚才走?又杀了个回马枪?又要搞什么阴谋?
这是金陵不少官员心头的第一想法。
而对郝家而言,自从郝继儒之孙郝希先,因为当初的倒卖米粮之事被抓以后,郝家其实低调了许多,这次还是在确信卫国公贾珩已经离了金陵城,这才将子弟放出来。
谁知道,不过眨眼的工夫,这就出了事儿。
此刻,晋阳长公主府中——
贾珩缓步回到府中,行不多远,在抄手游廊之中,抬眸正好见到手里正拿着一份账簿的元春,轻声唤道:“大姐姐。”
元春目中现出欢喜,讶异问道:“珩弟不是去外间办事了吗?”
“忙完了,回来吃午饭。”贾珩面色微顿,轻声说道:“时间还早儿,我给大姐姐说点儿事儿。”
探春喜欢他的事儿,他考虑要不要和元春说说。
人常言,长姐如母,如果他真的与探春有了风情月思,元春真的以为他是一个都不剩下,这实在影响他的风评。
元春柳叶细眉之下,明眸眸光盈盈如水,低声问道:“珩弟,你寻我有事儿?”
两人其实也算是老夫老妻了。
贾珩道:“到大姐姐屋里说。”
元春说话间,引着贾珩来到自己所居厢房,屋内窗明几净,桌椅以及书画装扮的简约大方,身形丰腴,曲线曼妙的丽人,缓步来到书案之畔。
元春提起一个茶壶,给贾珩斟了一杯茶,道:“珩弟,喝茶。”
说着,将茶盅递给贾珩。
贾珩接过茶盅,抿了一口,看向那隔着一方小几落座的丽人,说道:“大姐姐,最近比较忙,有些冷落大姐姐了。”
其实,在正月的时候还是与元春温存过的。
随着年龄渐长,元春也到了花信之龄,原就如满月的秀丽容颜丰润如霞,眉眼细长,倒也渐渐有几分贤德妃的气象。
元春柔声说道:“我们都在一块儿好几年了呀,珩弟倒也不用整天陪着我的。”
其实,她还是想要个孩子,在珩弟不在她身边儿童的时候,能够有个慰藉。
她也不奢求男孩儿,女孩儿就行。
贾珩轻笑了下,看向那容颜丰媚的丽人,说道:“是啊,在一块儿好几年了,都快成老夫老妻了。”
说着,徐徐拉过元春的素手,道:“大姐姐,让我看看瘦了没有。”
元春白腻如雪的脸蛋儿线条丰润,白里透红,眉眼蒙起一股羞意,低声说道:“珩弟,我还胖了呢,唔~”
那少年却已凑近过来,丽人呼吸一滞,莹莹美眸缓缓阖上,宛如中秋满月的脸蛋儿爬上绮丽红晕。
与此同时大姐姐云鬓微束的螓首向侧后方扭转过去用火热的红唇贴住了贾珩的嘴巴。
贾珩自然也毫不客气地将整条舌头伸长到大姐姐娇艳欲滴的双唇中,舔过元春樱桃小嘴里每一寸贝齿与粘膜。
而与弟弟媾和许久,如胶似漆的少女也满面春情地撅起一双润泽丰唇,十分配合地主动将情郎的舌头牢牢吸附柱不愿松口,将那有力的舌头当作冰棍一般在自己柔软唇瓣间来回吞吐,在久别重逢的激荡中,元春潮红的丰腻双颊都微微地凹陷了进去。
同时贾珩灵巧的舌头伸长出来如同藤蔓一般纠缠环绕住元春的舌头,海量浓稠唾液在两人唇舌抵死缠绵之下,混合在一起由高至低倒灌进丰腻大姐姐的秀口中,被情动盎然的美熟丽人甘之如饴地大口吞咽下肚,如同情郎的唾液是什么美味珍馐一般。
少顷,元春玉颜染绯,微微喘着细气,明眸盈盈如水,凝睇而望,说道:“珩弟,刚才不是说有事儿要和我说吗?”
说着说着,又亲昵了起来,都老夫老妻了,还亲昵不够呢。
贾珩拉过元春绵软的素手,向里厢而去,坐在床榻上叙话。
正是二月时节,乍暖还寒,贾珩在暖手宝里轻轻暖着,拧了拧眉,轻声说道:“是三妹妹的事儿。”
贾珩抱着少女,手越过元春的腋下伸到两只硕乳之上覆盖住了整片乳晕以及大半松软雪峰,两手的中指与无名指各自夹住一颗娇艳欲滴的鲜嫩奶头,十根强而有力的手指深深陷进大姐姐弹性十足的乳肉里肆意揉动。
而那狰狞硕大的悍然巨棍此时也轻车熟路的正被元春夹在一双丰圆玉腿之间。
随着元春因为滚烫和酥麻轻轻扭动圆臀的动作,使得那肉茎陷在大腿软肉中前后抽插起来,青筋虬结的狰狞肉棒一进一出之际轻轻研磨着大姐姐的柔嫩阴户,两片薄薄的鲜红小阴唇被霸道的肉棍硬生生挤得向两侧绽开,
川流不息的春水自蜜穴里不断涌出,贾珩的粗长肉筋早已被正不断往下滴落来自少女花穴里的透明粘液,完全淋湿。
毕竟是老夫老妻,元春也没有抗拒着那少年的亲昵,反而高抬起两只藕臂绕到脑后轻轻环住贾珩的脖颈,丰润脸颊酡红如霞,稳着微颤的声线,柔声道:“珩弟,三妹妹她怎么了?”
贾珩轻轻解着衣带,说道:“三妹妹年岁大了,也到了嫁人的时候,我前个儿问她的意思,她倒是不怎么急着嫁人的。”
元春柔声道:“三妹妹年岁还小一些,论年龄也该是二妹妹先定亲才是的。”
贾珩温声道:“我就是问问。”
说着,轻轻拥着元春,瘫软在贾珩身上被不断玩弄调戏的少女,此刻一身雪白美肉上的每一寸肌肤都透出淡淡的粉红,恰似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无边的媚态直叫贾珩都神色一顿。
元春恍若翠羽的秀眉之下,那双水润莹莹的美眸眨了眨,轻声说道:“珩弟你说,然后怎么了?”
贾珩默然片刻,斟酌着言辞道:“我瞧她的意思,倒是对我有些……有些情愫。”
说到最后,声音也有一些异样,只是手上的动作却是不停,一只大手搂着少女的腰肢,一只大手伸入肉腿之间,按住两片红艳花唇,向外侧用力掰开露出隐约可见的鲜嫩阴肉,
同时让她的娇躯微微下沉,还滴着丝丝淫液的两瓣红艳花唇一左一右夹住了那一柱擎天的硕大龟头,汁水四溢的肉穴与不断溢出先走液的狰狞马眼深情亲吻在了一起。
元春:“……”
似是被那下身的炙热烫得失神了片刻,旋即,芳心羞恼不胜,丰丽脸颊羞红如霞,眉眼绮韵流淌,似有些恼怒道:“哪个少女不怀春,谁让珩弟这么招人喜欢?”
她现在还记得,当初她就是给鬼迷心窍了一样,宁愿出家也要和他长相厮守,这二年倒是乐在其中,感慨当初坚定。
谁曾想三妹妹也…
贾珩轻轻扶住元春的丰腴腰肢,故地重游,倦鸟归林,挺翘的肉茎如同一根滋滋冒油的滚烫烙铁捅入了柔软多汁的丽人花穴中,只觉得温润不胜。
少年稳着心神轻声说道:“我也不知怎么办,这不是问你这个当姐的。”
元春还真是探春的亲姐姐。
接着,贾珩向后抽出了肉棒,挺腰,反复对着元春的花穴,抽挺了起来。
一次,又一次,肉棒打着颤,勉勉强强的从层层环绕缠绵的肉折抽离出来,捣出一摊淫水,再一鼓作气的刺入深处,搅得肉穴一阵收缩。
贾珩用着这样的态势来回撞击着肉穴,每一下都撞得元春丰圆的美臀跳着肉花,却仍是嫌不够的从肉穴试图榨取更多乐子。
元春娇躯颤栗了下,丰美、明艳的玉容两侧泛起绮丽红晕,低声说道:“珩弟,我…我也管不了她的,三妹妹她向来有主见的。”
贾珩轻轻拉过元春的手,低声道:“那我怎么办?”
元春白腻玉容滚烫如火,愈见丰艳雍美,额前垂下的一缕青丝随风扬起,樱颗贝齿咬着粉唇,声音已经飘忽不定,七上八下,道:“船到桥头自然直,珩弟…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她自己现在都这样了,还能有什么立场去管三妹妹?
到时三妹妹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她也无可辩驳。
贾珩温声道:“那好吧。”
只是少女却再没有回应情郎的话语,思量间,每当肉棒狠狠的挺向深处,在里头恣意的拐搅,黏腻勾人的呻吟就会从元春融化掉的嘴唇里喘出,
这声音比起任何的一切都来得悦耳,惹得少年像是颈脖被套了缰绳般,为了听到更多的娇声而向前挺动。
坚挺的腰臀使劲的往深处挺动,两人的股间撞击而发出淫猥的肉声,淫水在相互撞击下飞洒到四处,元春张开的双腿更是舒服得反复瘫软绷直,丰盈的腿肉一次次勒出诱人的肉痕,更是时不时的放下升起,挤压着浸透肌肤的汗水,发出“噗呲噗呲”的淫靡声响。
为了享受更多的快感,元春的圆臀不知何时已经悄悄挺了起来,一双藕臂环到了少年身后,而贾珩作为响应也抱住了她的美背,胸前的一对饱满乳肉受到挤压而成了肉饼,两人更加紧密的合为了一体,就只为了更多的快意而把荷尔蒙飘散到空气中。
两人相拥在一起,耳鬓厮磨着,此刻正是二月时节,庭院中春雨飞扬,柳丝轻舞,枝叶婆娑。
……
春雨稍住,屋檐上雨水哗啦啦流淌,落在青砖上,漉漉而浸,天穹明净如洗,只是屋内的情欲气息却越发浓厚。
“唔嗯!!!”
伴着绵延不断的勾人轻吟,女人热情而粗重的鼻息喷薄在精致华美的被褥,她雪白肌肤如脂如玉,迷乱脸庞染有雌性发情的晕红,倩丽眼眸因身上激烈地冲撞和不停开拓体内接受程度的炙热肉茎而浑浊分不得一丝残留的理性。
她纤细的藕臂被一双修长白皙的有力大手拉直,近乎是要把双臂从人体分离出去一般整个人呈弓形跪在床上私密的下体因身后那只好似发情雄狮般的少年的肉棒,撞击喷溅出汩汩淫水,
透亮温热的液体既喷洒在柔软的床榻上也溅射在男人粗暴蛮横的肉茎上,那足足有小儿手胫粗长的昂首肉棍不留余地地开凿着元春娇美的花洞,
掀起狂风暴雨般足矣令人大脑昏厥的快感同时也一步步支配着他身下已经被肏到神志不清的少女的肉体与思考。
响亮的肉体撞击于旖旎醺然的室内不绝于耳,满溢涨潮的雌性甜腥水儿味侵犯鼻腔,叫他身心愉悦也涨大着他身为雄性的支配冲动:
那双犹如铁钳般的大手用力拉着这个与他如胶似漆的丽人的藕臂向后拽去,在她体内如鱼得水的性器也力度一次胜过一次地侵犯着她紧窄湿润而腻滑的穴肉,他此刻正深陷在欣然的喜悦和征服丽人的愉悦中。
这个近来越发温宁雍容的丽人此刻已经成为自己的泄欲肉具而跪倒身下嗷嗷噗噗的媚声着,紧致狭窄的腔肉仿佛是找到永久的归宿般紧紧咬住少年暗红粗长的性器促动他一次又一次的摆腰,
坚实的臂膀不留缝隙地笼罩住元春少女娇嫩与人妻熟媚交织的诱人身体,身量颀长、挺拔宽厚的身躯使得元春那不过普通女性身量的丰腻娇躯显得娇小柔弱,宛如白腻丰软的白羊被凶猛霸道的猛虎擒住一般任其肆意摆弄。
少年的肉茎在元春媚软的膣腔里抽插着,硕大的龟头一次次亲吻娇弱的宫颈与之重合,黏腻的蜜液和晶莹的泪珠自女人上下两头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
‘咕湫咕湫’的水音与清脆的肉体碰撞混合一体,亦如粉嫩与暗褐的性器忘我交合一般侵满了整个厢房。
帷幔透入的天光衬映着丽人淫靡放浪的表情,早已沉溺在与情郎的交欢快意下的她在一次次激烈的做爱中下体早在不知多久以前已经变成了他的形状,甚至好似整个人的存在都是为了这一刻似的,不用思考的享受与肉茎交合的过程,体验子宫被浓精满溢灼烧送上高潮的快感。
“呜,噢,噢…珩弟,慢点……你这样抓的大姐姐好麻。”
温宁的嗓音因难以压抑的媚身而支离破碎,那纤细却不失温柔的语气是教导他的得力方针。
身后少年听闻她艰涩的呻吟仿佛心生怜悯之意般,放松了拽住娇妻的力道转而抚上她光洁的美背一点一滴地吮嗅起来,淡淡的奶香和着骚淫的气息飘入鼻腔,
上半身不着片缕,加之甩荡不止的丰硕雪峰,都显得透明虚幻迷人,可在这令人心魂荡漾的坦荡之下元春的小腹以下部分,套着的是那早已湿濡不堪的秀雅宫裳,这仿佛抹上水润的鹅黄衣裙,春光乍泄的朦胧遮掩,衬托着她熟媚丰腴的美姿与潜藏在温宁雍容后的骚浪,
飞舞摇曳的发丝落下,滚落下淌的汗液融化,早已泛滥成灾的淫水无不说明这个在别人看来十恶不赦的星核猎手也脱离不了被强大雄性征服的命运。
“唔嗯,大姐姐。”
他说着,双手握住娇娘的丰软腰肢缓慢抽送肉茎的进出。
而早已筋疲力竭的元春在双手得到解放的霎时整个人似昏过去般螓首倒到了宽广的床被里,那对无力的手臂也陷进柔软的被褥中随男人肉棒的深入拔出微微颤抖。
少年强大的身躯左右着元春的情绪与残存的思考,那双白皙修长的大手足矣握住丽人整个腹部使她动弹不得,
迷蒙而闷热的呼吸随着肉茎在淫屄里横冲直撞愈发高昂,汹涌如潮的快意和着突然变得粗暴激烈地撞击,一波波洗刷着丽人的认知与心理,
她昔日独身入宫数年养成的处变不惊在这个弟弟面前毫不管用,她丰腴饱满且娇嫩诱人的身躯不仅没能加速少年的败北,反倒被他化险为变作快感的帮凶。
在明净天光下油亮的白皙肌肤更加衬显了暗红肉茎对花穴实施的侵犯,少年那紫红色犹如鹅卵石大的龟头大力凿开媚肉的阻挠直直顶上柔弱的子宫,
酥麻蚀骨的快感直接逼上骨髓,炙热而庞大的力道与不讲道理的行为裹挟着元春的一举一动,她丰圆饱满的双腿因为需要抵抗快感的侵袭而弯成九十度,柔然的足掌抵到了雄性后臀上,那对本应疯狂摇晃成炫目奶浪的双乳却因为无力支撑身体而瘫陷在一望无尽的白色中央。
已如春笋拔尖的樱粉硕乳埋进洁白的大床,弥漫着淡淡幽香的玉肌喷薄着女人的热量,不断吮吸龟头肉冠与肉杵的软肉被一遍遍撑开,而情不自禁地叫出神魂颠倒的呻吟,
秀丽飘逸的发丝在空中曳起,温热透明的汗珠滚滚而落,同样滚烫热量近乎是烧却元春的大脑般令她痛苦又沉溺其中,炽热触感从穴口流遍全身,她已不知多少次领略这跟肉龙的威力与魅力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哈啊啊啊~珩哥哥……坏,都顶上元春肚子了~。”
风情万种的吐息彰显着怒目肉棒的威力,而这犹如火上浇油般的发自内心的感叹成了贾珩好不容易压住本能的助燃剂。
那湿濡又绵软却意外骚浪的娇喘解放了他的理智,于是那双有力的大手压住元春光润的肩头,力道强劲的胯骨不留余力地使劲冲撞少女弹软的臀肉。
久旷的花穴被肉棒肏干,敏锐的大脑只思考滚烫的快感,全身上下的感官都沦为只为更加深刻的感觉肉茎的感觉接收器。
这种认识或者说体验一步步蚕食元春的认知,待她再次被他压在身下时,这种认知便已如种子般生根发芽。
此时此刻,磅礴的混合到一起的男女体味与淫液的腥臊味汗液的黏腻味与肉棒浓郁的腥臭结合至一起溢满了整个房间,
因两人大力交合而发出狰狞尖叫的四根床脚剧烈抖动着宛如元春不停颤抖的娇躯,胯骨撞击臀肉的声音愈发响亮,咕湫咕湫的水声愈发悦耳膨胀,肿大的快感填满全身侵犯思考,无与伦比的快感刺激衔着清淡浓郁的体香使两人不约而同咬紧了牙关。
贾珩一次次摆动着腰部一次次抨击着宫颈,潮水般滚滚而来的激昂爽感毫不留情地冲洗着元春的身体,
她红润的玉体抖动着,嗓音飘漏意义不明的浪叫,浑浊的眸子更是笼上一层深不见底的尘雾,性欲与情欲的体验早已通过男人肉棒的深入将她吃得死死,
要不是最后一点身为‘姐姐’的矜持支撑着她,她真像发自内心地喊出对此时宛如野兽般的情郎的臣服宣言。
“齁哦哦…哦~~”
电击般的酥麻感从大脑炸开变作浑厚不清的画面通过声线播放,源源不断的快感吞噬着这位温宁美人的理智,早已无力反抗的她身体只是一味随身后强烈的冲撞毫无规律地晃动,
丰淫的臀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本奶白的臀部在无数次的撞击和时而巴掌的拍打下早已通红满面,清晰的掌印和不断浮现的酸疼足矣说明这名青年用的力道究竟有多重。
“怎么了姐姐,是要泄身了吗?”
男人轻声地调笑着,再一次加大了对大姐姐肉穴的施压:膣腔有如痉挛般的收缩着,丰盈的淫液起到的润滑作用已经消失,龟头有如炮击般一回回轰上女人娇弱的宫颈将没有赘肉的小腹顶出一个隆起。
“呜噢~~~~!!!!!!”
一刹那,元春美眸翻白琼鼻拱起,伴着一阵无法自己的骚叫精致的俏脸沦为一副淫荡的阿黑颜,这位艳美的不过二十来岁的少女在这一刻彻底沦陷,她再也无法对他作出任何的抵抗。
响着,响着。
无数轰鸣与无数声叫不知疲倦地响着,填满大脑取代思考。
元春舒爽地颤抖着,螓首无力地埋在精致的床榻上,被里黏稠的涎水将厚厚的被褥打上一层显眼的深色,经过无数次龟头冲击的宫颈的感受被放大的无数次,可那犹如小嘴似的媚肉颗粒却咬的更紧,箍住肉冠包裹肉杵,甚至吸附住龟头刺激男人射精的欲望。
“哦~大姐姐的小穴夹得真紧,就这么想要子钰吗?”
不绝于耳的淫水倾洒和已经听得疲倦的肉体碰撞仍然一刻不停地响着,女人不能思考了,下体潮涌的快感和被人征服的喜悦与贾珩柔声叫喊自己为姐姐的欢欣混合于一起填满她的身心,此刻的她早已化作一头只为体验交欢的牝兽而存在,只想臣服在自己的弟弟淫威之下。
“呜嗯嗯嗯…~”
断断续续哼着,最后的本能只余发泄:“珩弟,呜,珩哥哥快点,元春要泄了,快点,啊……”
“大姐姐,我也快…唔!”
也就是这一时刻,绝无伦比的腔肉收缩的紧致感死死绞住贾珩狰狞雄壮的肉棍,对前列腺的刺激和刺激画面感的丽人浪叫不约而同袭来,遏止不能的射精冲动终于袭上感觉,
于是他伏下身子,有力的大手牢牢握住元春淫腻的乳球加快且加大下体的冲刺拼尽全力地对着淫水泛滥的淫屄抽插几十下后,终于在近乎要被肏云巅的元春的体内射精:“射、射了,大姐姐接好了~……”
话音未落,炙热浓稠的精浆便射进了少女娇弱的子宫中,滚烫的白精冲入宫壁激荡翻滚落入狭小的宫室并伴着元春悦耳骚淫的昂叫占满了诞生生命的宝宝房。
“噢噢噢噢!!!泄了泄了,身为姐姐的我被珩弟肏的高潮了咿呀~~~~~~”
泪水和汗珠糊满了元春的俏脸,下体的淫液好似喷泉般倾洒在颤抖不已的大床,打湿了贾珩的肉棒和大腿,也打湿了那条被撕得杂乱不堪的裙裳。
肌肤上油亮的色泽在隐约的光线下泛着淫腻的颜色,元春的身体剧烈痉挛着,却因为贾珩的肉茎仍在穴里堵着而无法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身后的罪魁祸首享受着温热阴精冲刷肉棒,浓稠精浆喷射进子宫的余音绕梁的快感,待到将肉棒缓缓拔出双手松开霎时,没有一丁点力气的元春立刻瘫倒在柔软的被褥中央,再一次抵达了高潮。
“齁哦哦……~…好舒服~”
话语间,淫液二次喷涌,伴着痉挛挥洒至帷幔内的每一处,如同涌泉一般打在湿漉漉的床榻上,直至蔓延至地板上。
见此情景的贾珩,他那冷峭英武的面容上满是欣然快意,仿佛是将元春拾起般跟她位置对调使她坐在自己的腹部上,然后将未彻底得到满足的昂扬肉茎插入,以猝不及防的快感瞬间打碎元春好不容易回温的理性。
“噢噢噢!!!呜,珩弟,珩哥哥、不要了,元春受不了了~~~”
“大姐姐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可不这样想对吧。”
他轻笑着,略显粗糙的指腹抚上大姐姐挺翘的蕊珠用力搓弄,同时抓揉着少女的丰臀,使其轻轻扭动着。
不消片刻,再度被挑动情欲的丰熟少女,便像是按耐不住般主动扭动腰臀,丰腴的肉腿反复进行蹲坐的动作,
花穴吞吐着那深入蜜处的肉棒,花穴形状被粗壮的肉棒撑得扭曲变形,潺潺流水从缝隙中流出,沿着肉棒上突起的肉筋,螺旋状的向下缭绕,浇灌到床榻上,再宛如瀑布般流到地面。
及至天光高悬,贾珩拥住绵软如一团泥的丽人,凝眸说道:“大姐姐,好了,都晌午了。”
此刻,元春脸蛋儿绮艳明丽,美眸睁开一线,额头汗津津的,声音多少有些酥软、娇媚,嗔怪道:“珩弟,成天就知道胡闹。”
贾珩道:“大姐姐,等会儿,咱们该吃饭了。”
“让抱琴准备点儿热水,洗个澡,身上黏糊糊的,不得劲。”元春容色明丽,柔声说道。
“嗯,那我掀起来。”贾珩轻轻应了一声,目光温煦几分,然后找来衣裳。
两天赶路的风尘仆仆,在元春的一江春水中柔波荡漾,渐渐得以恢复元气。
贾珩起得身来,出了厢房,站在廊檐下,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大一会儿,陈潇从抄手游廊过来,面色淡漠,说道:“刚刚去金陵锦衣府搜集而来的战报,北静王那边儿已经歼灭了逃亡之敌,击毙刘香,全军返回台湾。”
贾珩伸手接过军报,垂眸阅览片刻,道:“刘香既死,台湾大安,海师筹建以后,就可护航商船,至于台湾抚治事宜,只能等我回京以后了。”
回京之后,肯定要讨论设省开府诸事,以及移民等事。
这也是崇平帝急召他回京的缘由之一,他作为许多事务的具体经办人,无他在朝中,军机处和内阁还真的无法进行下一步推演策略。
而女真似乎又派出了使者求和。
陈潇好奇问道:“你今个儿去见师姐,师姐她给你说什么?”
贾珩轻声说道:“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给我说了一下山东的事儿,让我提防一下。”
至于一些莫名奇妙的事儿,就不好与潇潇说了。
陈潇目光带着几许审视地打量了贾珩一眼,轻声说道:“就这些?”
“还能有什么?这么短的时间。”贾珩说道。
陈潇道:“足够你几个来回了。”
贾珩:“……”
拉过少女的素手,拥入怀中,轻声说道:“潇潇,你说话得凭良心,哪次不是你先……”
陈潇挣脱了下那少年,说道:“别胡闹,一身的脂粉气。”
贾珩默然片刻,道:“其实你师姐,人其实还不错。”
顾若清应该算比较有气节的,只是性情清高,不愿谄媚于世俗。
倒也不是那种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因为看到了不属于自己本身阶层的生活,就不管自己配不配得上,认不清自己,成天许愿。
而且顾若清本身具备一定的生产性才艺,而非旅游、烘焙、摄影、插花四件套,全部是不能创造生产价值的消费性才艺,妥妥的有毒资产。
“又看上了?”陈潇秀眉挑了挑,清眸闪烁了下,没好气道。
贾珩:“……”
转眸看向那少女,伸手捏了捏少女的清冷的脸蛋儿,低声说道:“你成天说什么呢,我能看上她?”
陈潇轻轻打开贾珩的手,清丽、明媚的玉颜上现出几许清冷之色,明眸闪了闪,说道:“别看上看不上了,现在说这些话,不怕将来打脸。”
贾珩:“……”
陈潇岔开话题,问道:“咱们是明天走?”
贾珩点了点头,轻声道:“就明天走,晋阳和节儿先在这儿待着,我们骑快马,与婵月一同赶上船队。”
陈潇想了想,说道:“那也好,一直在这儿耽搁也不是事儿。”
这会儿,元春的丫鬟抱琴,近前唤道:“大爷,大姑娘唤你过去洗个澡。”
贾珩轻声道:“我过去也洗个澡。”
是得洗个澡,潇潇都嫌弃了,而后也不多言,前往元春屋里沐浴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