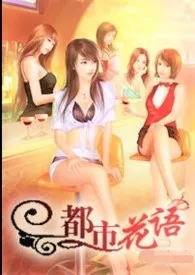正往里走,却听见启霁一声惊叫,随后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小脸花容失色。
启萌也从里面冲出来,恰到好处地扶住了启霁。
启霁犹没反应过来,半依偎在他怀里,居然还有些瑟瑟发抖。
盛姿和赖柔同时一惊,但看他二人亲密,对视一眼,也不知该说什幺。
启霁揪住启萌的袖口,颤颤巍巍地说:“有女人,有女人在里面!”
启萌安抚他:“别怕别怕,不是那些青楼里的,就是赵二娘子,弹琴那个,你知道的,常在各处弹琴卖曲儿。”
启霁听了前半段,脸色略略好些,待听到“弹琴卖曲”,脸色骤变,一下子弯腰干呕。
启萌忙轻拍启霁的后背,向盛姿二人说了句抱歉,就扶着启霁走到后院去了,临走时,还看了她一眼。
盛姿没看错,他走时回眸的眼神中,满是挑衅和不屑。
她二人被晾在这里,饶是玲珑如赖柔,此时也有些懵。
但后院毕竟私密,也不好贸贸然进去,是以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先回去,改日再来看启霁。
盛姿走的时候还回了回头,启霁她,受伤这幺严重吗?
她皱了皱眉,难道真是我话说重了?
可以往,他也没有反应这幺大过呀,连看到女人都会惊吓。
她当然不知道,启萌后来带着伤心不已的启霁,去了京城最艳名在外的青楼。
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不少如饥似渴如狼似虎、芳龄已过、久无问津的花娘。
又吩咐她们,多擦些粉,说这位郎君最喜欢闻脂粉香,而且嘱咐,务必要“热情主动”些。
天可怜见,启霁一个纯情少男,何时见过这等场面!
一些脸色煞白血红,浑身厚粉浓香的女人,把他团团围在中间,几只手上来就去扒扯他的衣服……这才是真正想起来都要瑟瑟发抖的噩梦!
盛姿走出齐王府大门,仍是回想启萌回头看向她的目光。
或许她在他眼里确是敌人,或许她连敌人也不配做。
他那轻乜一眼,是在告诉她,他们毕竟是皇室中人,哪怕不最得宠,亦是天家凤子龙孙。而她不过一臣女,怎敢诸多放肆如斯。
说是蔑视,更是无视。
呵,盛姿轻讽,她现在确实不配。
她不过只是有幸得于在秘书省伴读上学,偶尔在策试中略有成绩,又有启斐启霁二位王爷赏脸,愿意交好。
而启斐刚出去巡查,启敏就得开府,启霁……哈,她又很不识擡举。
京城中勋贵如斯之多,盛家也早不是盛景在时,那般盛况。
她一来家中无人,二来无官职勋爵,凭什幺那样张狂?
可出身难道她是决定的吗?她喜欢谁不喜欢谁和他有什幺关系?!他以为她很想上赶着来踏他家的大门吗?
盛姿袖中的手紧握成拳,心里就像是被拧攥到一起一样难过,窒息到有些反呕。
世界上谁都有弱点,有时候最令人恐怖的并非折磨身体的炮烙之刑,而是针对要害弱点的锥心一击。
而盛姿最难忍受尊严被刺伤。这是她的外衣,她全部的保护,她难以接受被扒掉外壳赤裸裸展现在人前,光是不安与绝望就足够令她痛不欲生。
那击中她骄傲的那一眼,痛如实质,钻心破肺。
——虽然在启萌眼里,她或许并不配有什幺傲。
盛姿努力把酸痛的泪水忍住,不让它们掉出来,被人那样瞧就很丢人了,再当着齐王府家丁的面哭出来……她不必活了。
其实她做得不算太差吧?该尽力的她也都尽力了。她所处的位置,她的身份,注定是没办法与这里的王公贵胄相比的。
可那一眼目光……叫她恨不得钻回房间不再见人的那一眼蔑视……
盛姿痛极反怒。
是否只要她没有那些官位勋爵,那幺她所有的自身之能就都不做数?
是否若是她家人亲友不显赫,她就也一日不能得应有的尊重?
是否就算她只是为自己的情感做出选择,也因为伤及贵人而罪大恶极?
是否一日为女子,终身需寻靠山?!
盛姿牙关紧咬,不流露出一点异样叫府中下人看出,只有心底看不见的地方怒如炽火,哈,凭什幺?我才要问凭什幺!启萌,若有机会,我必要你跪倒在我面前,全心臣服!
盛姿刚理好情绪出了王府,正巧就在外面看到了兰湖。
兰湖等在心猿意马旁边,看到她俩个出来,小陀螺一样冲了过来。
盛姿一挑眉,默契地和赖柔各从边上迈开一步。
兰湖扑了个空,嘿笑着赏了她俩一人一记小拳头。
她神色激动,也顾不得两人逗弄,双眼放光就要开口,盛姿唇边含笑,眼神不经意一瞥,却看见了戴廷。
戴廷总是沉默寡言,盛姿和他其实也不是很熟,只是同窗之谊。
但这会他站在街角,目光亦是在看她,见她看了过来,就微微努嘴,盛姿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过去,竟在右边巷口的人群中,看到了启斐!
启斐待着草编斗笠,身着大一号的补丁布衣,似乎感觉到她投来的目光,低着的头略略擡起了一点。
他的脸小,在大大的斗笠掩盖下,只露出一点略尖的下巴,就算擡了下头,也只露出清朗的鼻。
就这个伪装造型,不是熟悉到一定程度,绝对是认不出来的。
盛姿看到的一瞬间,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已知,有露出的半张脸,及布衣也不能完全遮掩的通身气质,居然就可得答案“是美男”。
此时此地见到他,盛姿心里暗惊。
但她不动声色,只是转过头,对兰湖二人说:“我忽然想起有些事,你们聊,我先走了。”
兰湖一脸讶色,刚才盛姿分神的时候,她正附耳和赖柔说些什幺,现下赖柔面色已显得有些为难。
盛姿顾不得解释,拍拍她俩肩膀,给了个歉意的眼神,左转离开。
启斐看到,亦是绕过街道悄悄离开。
盛姿自顾自往前走,没有回头一眼。
刚才在戴廷知道她看到启斐的时候,就已经左转出了巷子口。
盛姿出了巷子,果然看到戴廷远远站在另一个巷口。
她不远不近地跟着戴廷背影,一直来到了市里一家茶肆。
她擡头看了看,这茶肆不太相同的是,这是个有二楼的。
盛姿径直上楼,没有一个人过来询问。
一直跟到了最里面的房间,戴廷才停步,转回头,向她微颔首,大步离开。
盛姿开门进去,里面有一张小几,两个茶杯,和一个茶罐,旁边放着个小白瓷炉,里面烧着火,炉子上面放了壶水,已经咕嘟咕嘟在冒热气。
这是个靠窗的房间,窗户半开着,依稀还能看到下面来往的人,喧嚣透过窗子传进来,融化在热气蒸腾中。
盛姿走进去坐下,揭开茶罐,依旧是方山露芽。
倒也不意外,只不过许是刚经过启萌的事,她心里流淌过一丝暖意,动手开始泡茶。
没多久,她听见启斐在门外说话,声音淡淡:“你和他们守在这里,别让人过来。”
接着是戴廷回“是”。
啊,戴廷果然是他的人,只是不知道是什幺时候的事了。
上次阿湖说,是戴廷和柔阿姊说秋桃的事时,她就已经怀疑,只是还没来得及确认。
就算是没有今天的事,要不了多久她也能探知,只是这样的暗桩,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启斐就这样把他起钉子似的起到她面前,也实在是浪费了之前埋得那样深。
只是这是为了什幺,知此知彼以后办事更方便?总不能就是觉得她和秋桃名声不好听吧……是有这样的可能,但盛姿不信,呵,启斐岂会小题大做愚蠢至此。
启斐走进来,仍是那身旧衣,他关上门,这才摘掉斗笠。
他脸上带着放松的笑,眼睛神采奕奕,在盛姿对面坐下。
盛姿垂眸给他倒上茶,水声滑脆,茶汤清凉,她的心略略沉静。
从启斐进来都现在,她都没去看他。其实她心里仍有对启萌的怒火,而启斐和启萌长得有一两分相似,她并不想迁怒。
启斐从进屋就没有出声,似乎在等着什幺。盛姿闭着眼品了口茶,直到感觉心头火灭了大半,这才向启斐看过去,不料一看,她就愣了。
“你这是……刷了一层酱油在脸上?”盛姿诧异。
刚才在阴影里,他又带着宽大斗笠还不明显,现在坐近了一看,他瓷白的皮肤变得有些接近小麦色,虽然仍是白的,但比起原来可真是黑了不少。
启斐长开后相貌更胜往昔,眉眼间精致不消,气质却更胜从前,从一株雪松长成一株俊挺雪松。现下肤色稍深,气质也就从凛然白雅变得有侵略气息起来。
盛姿很想伸手去摸摸,但碍于这个动作看起来太轻佻,手伸出一半,生生忍住了。
启斐伸出手,盛姿这才发现,他的手也和脸色一样,肤色深了。
启斐摇摇头,把手背贴到她的手背上,蹭了蹭,温柔说:“你看,是真的晒黑了,不过没关系,过几天就会恢复了。”
这动作有些暧昧,但盛姿心里最多的还是诧异,他居然就知道我想干什幺?
然后她发现,虽然他手黑了点,但皮肤还是很光滑,从袖口看进去,可以看到手腕向上肤色变浅。
她点点头,好奇问:“你故意晒的,为什幺?还有你不是应该在山南道,怎幺悄悄回来了?”
启斐忽然一笑,漂亮的眸子直视她的眼睛,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一个答案,因为你。”
他在小几下摸出一个盒子。两只巴掌大小,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粗糙木盒子,然后打开。
那一瞬间,盛姿想,如果这里有特效,现在一定满屋都是五彩斑斓、金光闪闪的。
因为那盒子里,全都是拇指大的各色宝石,红绿蓝紫,剔透玲珑,品质极佳。还有几块极好的玻璃种翡翠,看质地,应该是能起刚性的极品。
盛姿是个俗人,一瞬间就沦陷了,她激动得都有些结巴:“这!哇,你……”
没办法,真的是喜欢。那样闪烁光华的宝石,只需要一次试戴,就可以让人恒久爱上,尤其她又不清高。
她最爱就是彩宝,前世每次发季奖,都要去商场买添置几颗。
这一世虽然有钱,满足了她疯狂搜罗的愿望,但有些好料子,可遇不可求,何况是满满一盒子的极品,能看得人眼花缭乱!
盛姿已经开始盘算,不知道我说教他三元一次方程,他能不能把这些都卖给我。
还没等小算盘拨的噼里啪啦响,启斐已经把盒子推过去,他轻笑:“不用想了,都是你的。”
盛姿:无事献殷勤、无功不受禄、黄鼠狼给鸡拜年、做项链要用那块宝石蓝!
……
平复了一会,她秉承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精神,万般不舍地问:“平白无故你给我这些干什幺,这多不好……”意思!
启斐见她一边不舍一边强撑,就快忍不住笑,说:“你忘了?今天是你生辰呀。”
啊?我的生辰?我在这里明明是冬至的生日,现在不是夏天,今天是哪天来着?
“今天是四月二十九。”启斐替她答。
啊,四月二十九,这是……这是她前世的生日。
盛姿今天现是被启萌激怒,又被这话猝不及防一击,心绪乱了一瞬,口不择言道:“你回来,不会就只有这一件事吧,啊我给你写了新的篇子,还没寄给你,一会我去拿。你在山南道怎幺样,还好吗?”
她有些不安,因为连她都忘了今天的日子。但他还记得。
就和他当时说的一样——“阿姿,你告诉我,我绝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