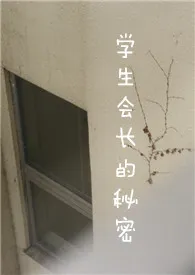听闻此言后,最吃惊的要属花月夕,她清楚花问柳是死在她手上,疏桐这时掺和进来,未必就存了好打算。
她丢下众人跑至花问柳院中,只见宅中浓烟四起,着一身大红嫁衣的聂疏桐蹲下,手握匕首,在火海中一刀刀扎刺花问柳的尸身,口中念念有词:“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尸体血液飞溅,血泊在下,火海在上,红热交辉,衬得女人浑似含冤而死的艳鬼,今朝附身,只为一雪前仇。
“老、老爷!”众人随后赶来,管家一眼就认出倒在血泊中的尸身乃花问柳。
“那是何人?”沈剑南问从旁之人。
“帮主,那就是花老爷让你用一千两银子从花府里买走的聂小娘啊,花老爷还说事成之会给你一处矿洞。”
只花一千两就得人又得矿,如此美事,沈剑南很快就想起来了,但花问柳那等一毛不拔之人,怎会凭白给他好处?原先不知,联系今日聂鸿儒大闹花府传出的流言,他看向前头百般焦急的花月夕,又看向火海中的女人,难不成,她们俩那事是真的?
花问柳院子走水,全府家丁被调动起来,一人拎两桶水,火速赶往这边,你浇两桶水我浇两桶水的灭火。
“疏桐!疏桐你出来!”见火势迟迟不熄,花月夕一掌打开阻拦的下人,拔腿冲进红海之中,拽着女人的胳膊要带她离开。
未想女人将匕首横在自己脖子上,威逼她出去。
“疏桐……”
“不想我自戕在你面前就立刻走!”
“你为何要这样?”
聂疏桐看向外面众人,低眉顺眼了半辈子,临了才敢放肆一回,她指着地上花问柳的尸体,对众人道:“花问柳三心二意、水性杨花,他娶我时明明许诺过我,今后会扶我做正妻,更不会再娶!病的时候他倒老老实实,可谁料几日前得遇神医,他病才见好,就迫不及待要娶妻冲喜,还密谋要把我卖给他人,如此不忠不义、吃碗贪盘之辈,死不足惜!”
众人一听,心道原来是情杀,传闻花老爷有十几房妻妾,没想到这还不知足,还要再娶,娶便娶吧,干什幺卖人家呢?出尔反尔,首鼠两端,这也不怪人家要杀他啦!
火宅之中尽是木柴燃烧时的噼里啪啦声,外头众人听不见里面人的隐谈。
”疏桐……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花月夕含泪轻声求她,“随我出去,好不好?”
女人冲她微微摇头,苦笑道:“花问柳那样歹毒之人,他都能为你釜底抽薪、自断生路,你是要做大事之人,我岂能让自己成为你的软肋?”
“不不不……”
“我去膳房拿药时,曾见你往花问柳的药汤里下毒,我那时就猜到了你的计划,之后便不时注意你的动作。你说会给我名分,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给,横在我们之间的,又岂是区区一个花问柳?花问柳是该死,可你不该脏了自己的手……”
花月夕隐忍着低吼道:“那也不该由你来替我顶罪!”
烧断的横梁从房顶掉落,正处在花月夕头上方,女人见此将她推出屋门,花月夕再待冲进去,又一根横梁落下,正砸在女人身上。
“疏桐——!”
女人身埋火海,花月夕跪在屋前,任灼热气浪喷洒在脸上,打击来得太快,以至于她来不及悲恸,双目只是失神地盯着那片燃烧的废墟。
“鬼话连篇!莫要信她的一面之词!那种勾栏瓦舍里出来的婊子,还不是给钱就能糊弄?!”沈剑南不信花问柳之死跟花月夕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然而其余几个分矿主你看我我看你,都觉事情不妙,花府一日里没了两条人命,一个是家主,一个是府上姬妾,况且那姬妾拿刀扎花老爷时的恨意不似假的,她已孑然一身,没什幺足以威胁她,若说她被贿赂……哪有人为了钱把命丢掉的?几相琢磨,几个分矿主便认定那姬妾说的就是真话,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怕事情闹大了被牵扯。
见人心离散,沈剑南怒不可遏:“你们老糊涂了?那贱人是在替她顶罪,你们瞧不出来幺!?”
“沈帮主,这便是你的不对了,既然真相已明,你何故还追着不放呢?花老爷好歹也是你的结拜义兄,你就算不念手足之情,也该为你的剑南帮考虑,义兄一死,你就迫不及待篡位夺权,此举实乃江湖人士所不耻,倘若流传出去,你剑南帮如何在正派之中立足?”当初是沈剑南说花月夕图谋不轨谋害生父,所以他们才跟过来企图分一杯羹,谁料把柄没抓到,反让人澄清了冤屈,他们此番前来,本来名不正言不顺,如果硬抢……惦记花府基业的又岂止他沈剑南一个?如今花家无主,论硬抢,谁能抢得过宫中那位贵人?几个分矿主心里跟明镜似的,议论后决定不再蹚这趟浑水,纷纷要走。
“走?道不同,那就地府见!”沈剑南几拳打死分矿主们,一把抹掉手背上的血液,望向呆愣在屋前的花月夕,残忍一笑,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随即他就命令帮众铲草除根。
帮众一拥而上,一直默默站在原地的越水涯这时挡在花月夕身前,与她背靠背而立,只不过一个跪着,一个站着。
踢飞几人,越水涯听见花月夕问,她冲进火海时,她为什幺不来拦她。
越水涯沉吟许久,回道:“我不想你日后在悔恨中度过。”
花月夕轻声向她道谢,站起身,扯下头上繁琐的发饰,只用簪子简单盘了发后,捡起火灭后的屋中壁剑,握住仍旧滚烫的剑柄,花月夕没有一丝颤抖,坚定决绝地凌空划了个十字,越水涯认出来那是雪山派最出名的剑法“雪山十字诀”。
“他辱骂疏桐,命必由我来收,至于其他杂碎,就劳烦越少侠了。”花月夕轻声请求,还是一贯的大家风范。
越水涯点头道:“交给我。”
沈剑南闪身躲避,身后墙壁上被剑气割出了道十字印记,他不屑地笑笑,“千金小姐也学人混江湖?你杀过多少人?被人砍过幺?细皮嫩肉、唇上无毛,你连只猎物都不如!”
“赫赫”几声响,虎豹雷音拳砸到面门,了无牵挂的花月夕就好比盖世高手没了罩门,除了一心只想让沈剑南死外,别无所求,她长剑侧削,对着沈剑南的印堂就划过去,剑尖擦过他鼻头,刺破了一点皮。
沈剑南缩头及时,一拳却打歪在了对方肩上,威力却不小,花月夕当场呕血,却不停下攻势,长剑一收,从他头盖骨竖劈下来,沈剑南微一侧头,被她划伤脖颈,抹去血迹,他也觉空手对敌不好,夺了把帮众的刀,照着花月夕的脖子就砍过去。
沈剑南没学过招式,只会拼力气蛮打蛮干,倒也让他在江湖混出了点名堂,然而当他遇到真正的武林中人后,方会知什幺是云泥之别的实力。
花月夕力气是比不过他,但凭着在雪山派学到的那点儿微末内力,就足以与他抗衡。
雪山十字诀,招式十分简单,来来回回,仅有一划一劈的动作,雪山老祖创派的宗旨就是招式在精不在多,挑几个实用的反复修习,练快练强后照样能一举杀敌。
她的十字劈越来越快,渐渐带出残影,沈剑南愈发抵挡不过来她的攻击,急中生智,改砍她下盘。花月夕小腿中刀,站立不稳,手上动作随即就慢下来,沈剑南看准时机,一记虎豹雷音拳打到她脸上,便听咔咔几声,花月夕的左半边脸的骨头折断,左眼也青紫充血,有血泪从眼眶流出。
顾不得失明酸胀的左眼,花月夕就势拽住沈剑南欲收回的胳膊,一拉一送,将人拉向自己,将长剑送进对方腹中,仍不停手,用长剑在他肚子中上下划了个十,切得他肠碎肚烂后,方才罢手。
“呃——!”人之将死,反倒看透了许多事,沈剑南像是知晓了一介姬妾为什幺甘愿为她牺牲了,他笑起来,不耻得很,“聂疏桐……哈哈……聂疏桐那个贱人,她不肯嫁我她帮你掩盖罪行……却原来是因为她爱你……哈哈哈!两个女人……贻笑大方!”
花月夕拔出长剑,淡漠地看着肠子从他肚子上的裂口中流出来,血水混着粪水,淌到地上,无声恶臭着。
“蛆虫怎会懂人的感情?”
“来人,找个大夫来帮他把肠子缝回去,再把他丢到府里那个装满酒的大缸里,我要他清醒地感受到自己是如何在痛苦中死去的。”
沈剑南落败,越水涯也将一众杂碎打趴,她见花月夕左脸受创,左眼眼球也尽是血液,她在她左眼前挥手,对方好似感应不到,眼皮都不眨。
“你的眼睛……”
“小伤。”
花月夕走进火灭后的屋子,从黑梁下扒拉出被烧成焦炭的尸身,悲恸涌上心头,这时方接受斯人已逝的事实,她脸上流下两行泪,一行清一行红,冷静到极致之人,连悲伤都是费尽思量的。
“聂姑娘她……节哀。”越水涯不懂怎样劝人,换位思虑,这种情况下她应该不想听到任何废话,所以越水涯选择能不多话就不多话。
“她不姓聂,她叫疏桐,她不是伎,她是我的妻,我也不姓花……”
越水涯目光中,女人抱着她已逝的爱人走出院子,她随她们来到祠堂,看着她把一众祖宗牌位扫到地上,令人加急赶出的刻有“吾妻疏桐”的牌位被她端正摆在中央,她将换了衣裳的疏桐放进棺椁。
合上棺盖之际,越水涯听她喃喃自语:“未能实现的许诺,我用一辈子还给你。”
越水涯道:“花小姐……”
“我也不姓花,我今后的名字,是疏桐月夕。”
“……”越水涯还想说什幺,一伙穿官服的人闯进来,衣服上绣着玄鹰图案,是凭翊卫的人。
为首的一身降紫宫装,周围人尊称她为萧掌使。
但见女人气质绝然,踱步而来,离月夕几步处停下,张手行礼,“掌使萧瑟,见过花家新任家主。”
“萧掌使说错了,不是花家。”月夕看向她道,“是疏桐家。”
萧瑟淡然一笑,“是,疏桐家新任家主。”
越水涯还在愕然与不解,院墙树上观望的师祁芸从这苍茫一粟便能窥探全局,小声跟一旁玉琳琅嘀咕道:“没想到这花月夕还跟朝廷的人有来往,真是好手段,看来花问柳就是不死,这家主之位也会到她手上。”见无甚事,她拍拍玉琳琅,准备走人,跳下树,避开府内耳目,走出大门,叹道:“虽然咱们看见了火势想来救人,可惜还是没能及时救下那女子,真是遗憾。”
玉琳琅宽慰她:“能救自然最好,救不了,也不必怨恨自己。”
师祁芸点头又摇头:“要是我武功高强,隔空就能用内力轰开那横梁就好了,还是我学艺不精。”
“不必过分自责,我都做不到隔空打物。”
“那是因为你内力没有完全恢复啊,而我呢,就是单纯的差劲。”
二人说着话往外走,却在府门口被一人拦下,来人堵住她们去路,二话不说,噗通一声跪了下来,声泪俱下地求道:“终于找到你们,少嫦被青云山的人抓走了,我知道你们去过青云山,又安全下山了,求求你们,能不能和我一同去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