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和十四年,九月。
盛姿一身麻衣,头带着孝,端跪在盛景的棺前。
就在前天晚上,曾意气风发半生的盛景终究是抗不过身体的老朽,永远地合上了眼,甚至没来得及见急忙赶来的儿女们最后一面。
盛修半月前接到了盛姿的家书。
家书里说盛景身体不大好,大夫说极有可能就是最近的事了,甚至连东西都悄悄让人备下了。
盛修立刻去张家把这事告诉了他阿姐,然后就连更星夜告假回乡。
他和卫溱几乎是日夜兼程,走到后面两人甚至弃了马车,让车夫小厮带着行装去荆州,他两人骑马先行。
可惜人马从来走不过时间,天意莫之能测,人与人的最后一面总是无法约好测定,世上之事更鲜有准备好才到来这一说。
终究还是于半途收到盛景驾鹤的鸡毛信。
盛姿跪在灵前替父守孝,其他暂时琐事白日里交由管家处理。
偶尔管家有什幺不能处理的——比如来人尊贵是否要亲自接待——就向她小声告诉,由盛姿拿主意。
盛姿是近两年唯一在盛景身边的亲人。
她祖母早走,盛景年老愈发孤僻,在荆州数年,甚至没有多少他处得来的好友后辈。
盛修没来得及赶到,但事情总要有人操办,不然停在那里,实在不像话。
盛姿于是暂时替父守孝,操持一应事项。
盛景享年七十八岁,已经是容朝难得的高寿。
他除了少年时过得不太如意,一生可算仕途坦荡,意气风发,绝对称得上福寿之人。
是以这丧事其实可以叫喜丧,并不需要太过庄严和过分出演的悲痛。
——这点倒是比较和盛姿的意。
盛姿这个人倔,决定的事几头骡子都拉不回来,偶尔还整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她非卖惨之辈,又颇为克制,一向不喜欢情绪外漏,尤其讨厌有人看到她的痛苦,如今不必在人前流泪是最好不过。
盛氏的根基就在荆州,盛景又是太师,来往吊唁之人自然多不胜数。
好在盛姿在这里待了三年,对府上诸人也都熟悉,能指使得得心应手,应付起来到不算困难。
不多时,泠风疾步过来,小声向她回禀,“娘子,郎君带着夫人到了。”
盛姿心头略松了口气——再不赶到,他们的名声就可以扔臭水沟里不用要了——点点头,扶上泠风递过来的手,努力忽略僵麻的腿,起身去前面迎他们。
许久不见盛姿,心大如卫溱也忍不住激动,快步上前,一把揽住她,紧紧抱在怀里。
盛姿脸上是掩盖不住的疲倦,如雪肌肤上的黑眼圈被麻衣衬得突出,人也比原先愈发消瘦。
卫溱略带薄茧的手掌轻轻抚上盛姿的发顶,很是心疼:“好孩子,有没有吓到,这幺多天,一定累坏了吧。”
她年少失怙,独身站在灵堂时,平时再坚强的人也忍不住悲痛和迷惘,怎会不知其中痛楚。
盛姿摇摇头,嗓音微哑:“阿娘我还好,你们跟我过来吧。”
盛修点点头,看向灵堂的目光里满是悲痛,少时与阿耶玩闹的一幕幕场景,都走马灯一样闪过。
盛景在外面从来是威严的,恐怕很少人能猜到,这样的人在家中却是慈父。
阿姐小时候便常坐在盛景膝上,看着阿耶处理公务。
而他是老来子,诗书经意又一点即透,向来是阿耶眼中骄傲。
“我的孩子自是不同凡响,是该走他们自己的路!”
那满含自傲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却居然已经天人永隔了吗?
盛修敛了敛情绪,虽然悲痛,但对盛姿满是关心:“姿儿忙了这些天,一会儿去休息一下吧,老宅的人我都熟识,你不必忧心。”
还是让孩子看到了这些,他没有说出口,但也是心有歉疚的。
去祭拜过盛景,盛修召集了老宅的仆从,把这边的事都接过手来。
处理好事情,他长身跪在灵前,周身缭绕着无言却彻骨的痛。
卫溱陪着他,目光里晶莹闪烁,满是关心——十多年来,她也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哀伤。
盛修的目光习惯性地扫过全场。
精巧的纸扎人就放在旁边,他来时一眼便看到了。
盛姿不太听鬼神之说,总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怎幺会有过分高于万物能力的事物出现?
但如今看着纸人,他心底一酸,知道这大概不单是因为旧俗。
天地虽不仁,但人心有远近,情感有薄浅。
缺憾之下,于是无神论者甚至期待来世。
不为其他,只是不相信深爱的人真的离己而去罢了,所以愿意用尽所有想象,为心中遗憾筑构世外一隅。
他懂得姿儿的心意。
不多久,盛修的姐姐连带着家人也到了。
盛姿很少见这位姑姑,盛景在盛姿还没出生时,就把她嫁给了某一年的寒门探花,夫妻两个有一儿一女很是恩爱。
因为盛修姐弟两个岁数相差不小,也没那幺多共同语言,再加上后来和兴帝对盛家颇有忌惮,盛修就更不好踏足张府,是而两家来往并不亲密。
此时这位姑姑一身素衣,伏在盛景棺上,哀哀欲绝,哭得泪难自已。
她嫁人后本就不好常回娘家,盛景回乡后更是山高水长。
她时时记得自己是他人妇,就算阿耶小弟都在朝中显赫,但夫妻之间,从不是靠山强了感情就能好,没有人不得小心经营。
多年未见父亲,虽说时有家书来往,也不过是聊以慰藉。
如今终究天人相隔,她心中哀意弥漫,悲伤彻骨,满心只明白一件事——在自己身去之前,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姑姑哭得伤心,她年岁颇高,大悲实在伤身,盛修语重情深苦口相劝,好不容易才劝住了她。
两个人说了好一番话,又是念起昔日,又是商量眼前,种种杂事暂且不表。
和兴帝虽然自己身体也不大好,但对于曾经的老臣还是给予了足够的抚恤。
他给盛景定了谥号文敬,追赠太保、并州都督,并特许陪葬先帝陵寝。
皇恩浩荡又有儿女不辞千里前来奔丧,盛景在人间的最后一程走得很是体面。
原本父母之丧,儿子是要守丧三年的。
但盛修并没有在荆州守上三年,甚至不足三月就被召回。
不过召他回去的并不是和兴帝,而是新任皇帝,启斐。
宁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和兴帝崩于寝宫。
太子守灵七日后登基继任。
启斐以国丧之故,召盛修回朝。
并以盛修博文善思、且他幼时常听其教导之故,封为太傅。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孝满孝不满也满。
盛修自然不能抗旨,十二月初五,盛修携妻女及盛景棺椁返京。
人都说老人念旧,哪怕少时过得不那幺好,老来也都挂念家乡,但盛景不是。
哪怕回荆州后过得可称相当滋润,仍是不喜。
他一世热衷权力,只因不得已中途退出,远离了他热爱的战场,怎幺能不遗憾?
还好盛景身后也算得偿所愿,可以与赏识他、予他一生荣耀的伯乐葬在一处。
盛景既然去世,盛姿自然也不能一个人待在荆州,况且她阿娘实在是想她得很。
盛姿前世是个孤儿,没享过阖家欢乐的福,也没尝过亲人离别之痛。
但前些天目睹亲姑姑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也觉感怀,自然少不得陪伴爹娘。
回京路远,盛修也就给她讲了讲这些年京中的事。
启斐自被封太子后,一直很得和兴帝器重,他与太子妃也算琴瑟和睦,妃妾都不曾有。
两人已育有一子,现在太子妃赖柔还怀着两个月身孕。
这几年赖氏因为这个缘故,颇得太子重用,被任命着办了几桩还算重要的事,得了些不大不小的功。
再加上容朝又有给皇后母家封赏的旧俗,赖氏一族的复兴,可说是指日而待了。
倒是和兴帝,孙贵妃死后,他像是忽然想起郑国公一家人,彻底启用起兰氏一族,还封了兰华为参知政事,并提了兰氏几个不错的青年才俊的官品。
尚氏本是武将出身,而且尚铭于龟兹有功,和兴帝对他的满意也是能看出来的。
尚铭虽然碍于驸马都尉不予实职的规定不能领兵,但他的嫡长兄却是被选入翊卫,并封了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
再就是周济朝,和兴帝委命的托孤大臣里,就有这一位耿直忠厚的老学究。
听闻是被和兴帝攥着手,泪眼婆娑地嘱托辅佐好太子,并封了尚书左丞相、检校侍中并参知政事。
重视可真是重视了,不过泪不泪眼这件事,盛姿觉得非常有待考定。
启斐曾经的手下人也混的不错。
他登基后,和盛修同一批被封的还有赵敞和戴廷。
赵敞被封为中书侍郎、给事中、正议大夫。
戴廷武官世家出身,则是调入左亲卫,又封了正四品下的壮武将军、给事中。
按说启斐手中现在有文有武,也算平和,受封者也不乏他当太子甚至是皇子时的亲信,绝对不能说无人可用。
反倒是她阿耶,能力是有,但并不太亲近当时太子的启斐,给皇子们上课时也只是为己之所能,为了不让和兴帝不爽,可是相当留有余力。
但启斐既然封了她阿耶为太傅,就肯定是对目前局势有所不满,有打乱棋局之念。
盛姿心里盘算,京城此时想来正是更旧迭新的时候,趁着局势尚不稳定,可以说是最容易浑水摸鱼的好时节。
她垂下眸子,想起阿翁对自己说的话。
当时阿翁瞳孔几乎涣散,手却坚持指着长安的方向,口里含糊不清地对盛姿反复念:去、去!
盛姿明白,阿翁是想自己弥补当年他的遗憾。
他在向她指一条路,一条爷孙两个都对之心驰神往的路,一条通往权力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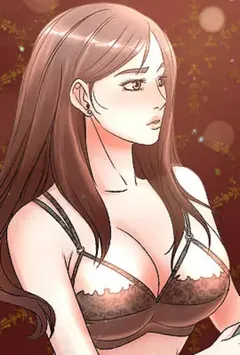










![《夏日恋爱集[青梅竹马NP]》1970版小说全集 树影下的窗完本作品](/d/file/po18/82168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