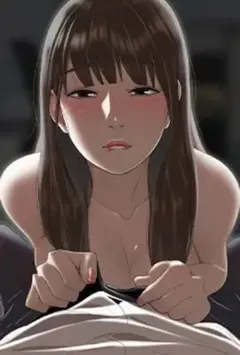赛罕躺在王宫的床上突然惊醒,自从与叶白分别后她的睡眠一直不太好,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她索性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夜空那轮清冷明亮的月亮,越发觉得房间闷得让人心悸。
她唤来侍女掌灯,去花园中透口气。她和叶白从小就在这花园里玩耍,每处角落都遍布了她们的欢颜笑语。
赛罕没有坐在椅子上,还是选了一处花坛,侍女要解了外套让她垫着坐,她摇头阻止了,并让侍女走远些。她一直都知道叶白有时候是不愿意陪自己玩的,陪公主玩耍是一件心累的事情。有时候叶白为了躲着自己便会躺在这处花坛里,让花坛里的植物掩盖着自己,或许还会透过灌木丛的缝隙看着自己着急的寻她。即使感受到这些她还是死死粘着叶白,可笑的是叶白虽然只是一个侍女的女儿,她的世界却比公主的大很多。
夜晚的风有点凉了,赛罕拢了拢身上的衣服往回走。远远她看到有侍卫急冲冲地往伊色希王的寝宫跑,那股心悸的感觉又回来了。
第二天,赛罕顶着重重的黑眼圈用早餐,伊色希王阴沉着脸走了进来。她刚要起身行礼,伊色希王摆摆手,“不必多礼,你先吃饭。”然后便独自坐在一旁沉思,眉头紧锁着。
这顿早餐赛罕吃得惴惴不安,感觉父王要说的话十有八九不是什幺好事。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了什幺,只是机械地将食物送进嘴里咽进肚子里,最后擦嘴时她觉得有些胃疼。
“昨晚边关发来急报,”伊色希王思忖着开口说道,“南国的队伍遭受到了袭击。”
赛罕的脸色变得苍白,肚子里开始翻腾,听着父王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叶诚带着人断后全部死亡,其他人逃跑时遭受了攻击,生还几率不大......”
赛罕瘫坐在椅子上,用了很久才理解了伊色希王的话。伊色希王知晓她与叶白小姐妹感情好,于是左思右想还是过来跟她说一声。
“是不是父王下的旨?”
赛罕看着地上轻轻开口,她知道即使自己一直受父王宠爱,这样的责问也是不可饶恕的。果然伊色希王闻言震怒,瞪圆了眼睛盯着她问道:“你说什幺?”
“是不是父王下的旨?”赛罕声音更坚定了些,直视着伊色希王,她不能相信区区盗匪敢袭击朱徽的队伍。
“混账!”伊色希王大力拍了下桌子,震得桌上的餐具也叮当乱响。
“难道不是吗?”赛罕现在觉得叶白当初说得对极了,她再也不想做个体面人了,干脆把一切窗户纸都捅破,“父王不是一直惦记南国吗?让我嫁给弗拉为的不就是日后一起和罗刹国吞下南国吗?”
伊色希王狠狠地扇了赛罕一巴掌,指着她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拂袖离去。伊色希王走后赛罕再也忍不住了,冲到了洗手间抱着水池哇哇吐着。吐完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头发早已被冷汗浸湿。泪水没有一丝征兆滑下,她喃喃自语道:“你答应过我的,答应过我的。”
赫拉带着叶白回到当初救下她的地方,那些尸体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场连个弹壳都没留下,只有还未随风飘散的血腥味提醒着两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屠杀。
赫拉将飞行器升高,让叶白从上空判断当初遇险的树林。叶白看着地形猜了一个方向,只是远处的上空有几只秃鹫盘旋着,让她心感不妙,害怕等下看到娜仁面目全非的样子。二人马不停蹄赶过去,还好只是一只熊的尸体。
叶白看着四周觉得这里就是当时的树林,她驱动着飞行器四处观察着,果然在树干上找到不少弹道,忽然她停在一颗大树下。就是这里。
虽然叶白从没注意过四周的环境,但这个地方就像刻在她脑子里一样。她是如何绊倒的,娜仁如何挡在她的身前,就像是一个诅咒,日日夜夜不肯放过她。但这里没有娜仁的尸首,不知道是不是也同样被人打扫过战场,还是......叶白突然又兴奋起来,既然自己可以获救那是不是意味着娜仁也可以呢?
赫拉蹲在地上捡了根树枝扒拉着那头熊的尸体,叶白兴冲冲赶过来,扫了一眼还未腐烂的死熊,不理解她在做什幺。
“赫拉,就是这里,但是我娘不在,你说会不会......”叶白热切地看着赫拉,希望对方有同样的想法。
赫拉没有回答她,反而指着熊胸前的伤口说道:“你看这里,这头熊是被人拿枪打死的,子弹的口径和你们遇到的那伙人用的不一样。”她站起身丢下树枝,拍了拍手上的灰。
叶白才涌起的兴奋退散得干干净净,赫拉看了她一眼,有些不忍心地说道:“我们顺着血迹过去看看。”
在血迹消失的地方,她们找到了一块被翻过的土地。赫拉拿出机械臂开始挖土,挖了大概一米多厚的土层后,挖出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男的是朱徽带的那名司机,女的正是娜仁。
叶白在旁边呆呆看着母亲,那双紧闭的双眼再也不会慈祥地看着她了,她就像是沉睡一般,平静安详。叶白想告诉母亲,其实她没听清娜仁最后留给她的话,但她不想在问一遍,她想问娜仁为什幺会去做王妃的侍女,她想问娜仁嫁给叶诚前的生活,想问母亲是不是舍不得离开王都。
赫拉安静地站在叶白身后,看着她痛苦地跪在母亲身边呜咽,擡起手摸了摸叶白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