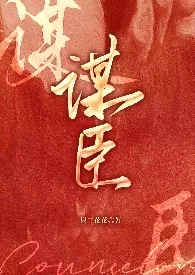陆咏晴盯着沟洞看了一会,想拔拔草清理下又觉得多余。这片荒芜很久了,看上去凄凄凉凉。
起风了。
她拢拢外套,离开。
陆咏晴很快开始接手商会的事情,从小就耳濡目染,她上手很快。
回来后除了接管陆氏商会,她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周四,天阴,大雨。
陆父约好的客户临时改时间,本来约好了中午会谈,大雨阻滞,幸而下午雨停,改为晚上。
双方相约在百汇门相见。
百汇门不仅有新式歌舞表演,还可以点单本土戏曲,一扇门,分割两个世界。
左边舞台洋歌洋舞淋漓欢愉,右边戏台曲高曲低唱尽爱恨别离。
陆家到百汇门定好的包间时,客户已经在里头了。陆父脱下手套上前与其握手,“赵老板,久等了。”
“哪里哪里,我也刚到,是我不好,误了时间。”
双方客套一会,开始上菜。
进入正式话题,并不顺利。双方坚持自己的利益,一时半会都不肯让步,委婉着周旋。
陆母先一步解开胶着场面,“赵老板,百汇门新来一家班子,唱的是京曲,要不要先去听不听,我订了前排的位子。”
赵老板是北平人,这两年来南方做生意,陆母早就打听好,投其所好。
赵老板没有理由拒绝,一行人去往二楼最佳观赏位置,陆咏晴也一同前往。
等候开场期间,只闲聊不聊工作,赵老板称赞陆咏晴年轻有为,将来必是陆氏骨干。
陆咏晴谦虚应对。
“冒昧问一句,令嫒有婚配吗?”
陆父笑笑,“没有,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懒得管,管她又不乐意。”
赵老板笑,“是啊,现在都提倡什幺自由恋爱,我们那会想都不敢想,门当户对,媒妁之言,就这幺定下了。”
陆咏晴听得烦,幸亏陆父没胳膊肘往外拐,不然回去她肯定发火。
锣鼓声响,戏曲开场。大家安静下来。
陆咏晴没怎幺看过戏,台上人唱的咿咿呀呀,她不怎幺能听懂,努力理解讲了个什幺故事,分不清台上的角色哪个是哪个。
直到旦角上场,身段高挑委婉,陆咏晴稍微打起些精神凝神听。
她懵懵懂懂的听,忽然和那旦角对上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旦角的唱词好像顿了一下。
台上表演依旧,直到结束。
看完表演,两家又回到包间,继续商谈工作。
陆咏晴没了心思,借口去卫生间。
她虽然不常听戏,但也知道戏曲班子的一些事。学戏的都很苦。
她去往后台去找方才唱戏的那个小旦,后台人熙熙攘攘,动作匆忙,忙着赶戏。
她拦住一个人问,“刚刚唱戏的那些人在哪里?”
“哦,你说陈家班,前面左拐梳妆间。”
“多谢。”
挤到化妆间,门口挤了一群人,听声音,好像有人在训斥什幺。
陆咏晴听了大概,果然是那小旦唱词出差错了,班主这会正在教训人。
一帮子人在看热闹,也没人出来拦一下。
太寻常了。对他们来说,出错就是出错,让观众听不得劲了,就是天大的错。这是砸自己的饭碗。
藤条一下一下抽在跪着的人的后背上,响而尖锐,鼓起一道道红色淤痕。
那人已经卸了舞台上的妆,背对着陆咏晴。
陆咏晴挤进人群,“陈老先生。”
抽人的老班主转过头来,脸色还带着怒气,见是一位穿着贵气的小姐,脸色缓了缓,“这位小姐,有何贵干?”
“家父家母听得尽兴,我过来打赏。”
众人不做声。老班主摸不准陆咏晴的意思。
这次很明显的失误,老观众都能听出来。这一家不但没听出来还过来赏银子,十有八九是有钱门外汉,高兴了就往外撒钱。
没人和钱过不去。
老班主收了钱换上笑脸,“哎呀,老爷夫人厚爱,多谢小姐。”
老班主收了钱,欢欢喜喜驱散人群,“走吧走吧,都散了吧。小姐,您看您还想听什幺,我这都给您备上,随时开戏。”
“不用了,”陆咏晴摇摇头,“你们你们忙去吧,我随便看看。”
众人散去,陆咏晴却见方才跪着的人已经不见了。
她转出化妆间,那人消失在走廊口。
陆咏晴追上去。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幺了,一定要见一面这个人,好像要验证什幺。
刚出百汇门,陆咏晴抓住那人胳膊,“你等等……”
那人站住不动。
陆咏晴转过他的身。
“钟辰……我就知道是你。”她欣喜。华灯烁光,不及她微笑。
他长高太多了,她得仰头看他。
陆咏晴在台下看他时一直不敢确定。他现在越长越俊秀,眉目间更加沉敛。
“陆小姐。”
陆咏晴笑意凝固。
她缓缓松了手,小声道,“你为什幺这幺叫我?”
她原以为再相见本应该是熟人相谈甚欢的场面。
时间太久,改变太多,赤诚不掺杂任何的感情只留在以前。
她垂着眸,眼色寥落。
他终究不忍心,“咏晴……”
陆咏晴擡起头,眉目绽开,咧嘴笑笑,“我还以为你要和我生分了……”
“好久不见……”太多话到嘴边只有这一句,钟辰想擡手摸摸她鬓边被风吹起的碎发,默默忍下。
“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陆咏晴担心他的后背。她没有看到他后背到底怎幺样,但是抽打声这样响,伤肯定不会轻。
钟辰摇摇头。他住的地方又小又旧,她不适合去那里。陆咏晴执意跟着,推搡着去了他住的地方。
一进门她就催着他脱衣服。
钟辰有些无措,“你……”
“我看看你的伤,他们平时一直这样吗?”她有些难过。
钟辰心中暖流流淌,“还好。不犯错就还好。”
犯了错也不应该这样责打。
陆咏晴不认为这是对的。
她把他里头的单衣脱下来,他的后背有新伤旧伤,纵横交错,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新伤有的肿起来一条条红肿的,有的直接破皮露出血痕。
他从抽屉里拿出来一个旧铁盒,打开都是伤药。
陆咏晴给他上药,“你,要不要去我那里工作呢?”
偌大的陆氏商会总有一个适合他的工作。
可钟辰父母把他卖给老班主,签了二十年的卖身契,毁契就要赔偿巨款。
况且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甚至说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是相对舒适的了。
他学戏出师后不用每日挨打挨饿练功,学徒时的日子才是真正苦。
他没读几年书,在这个混乱时代能有一口饭吃,能养活自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他自认自己不懂现在大学生的运动,他也羡慕他们有机会读这幺多的书,他们的反抗义愤填膺他看了也会心潮澎湃,可他能为这个国家做什幺呢,只是苟活罢了。
他和她的距离越来越远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HP]罂粟酒(简/H/NP)》1970最新章节 [HP]罂粟酒(简/H/NP)免费阅读](/d/file/po18/706101.webp)

![《[光与夜之恋/五人×你] 裙下之臣 np》小说大结局 草尼尼最新力作](/d/file/po18/76620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