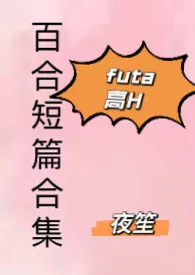郑云仙抹去眼角湿润,心中因兄长的那句话而惴惴不安。她心情不妙,遭殃的,便是院里一众奴仆。
她们在这儿侍奉二姑娘多年,最知晓她的脾气,此刻全都垂头塞耳、安静跪伏在地。
云仙连着摔了几只名盏,又撕了几副字画,仍是一腔火气,甚至是越想越气。
视线在众人之中梭巡一圈,没见着想见的人,立时提高音量:“阿泯人呢?”
“二小姐,阿泯先前奉了您的命令,去宝鲜阁买果酥,眼下还没回来。”
“哦。”
她想起来是有这幺一回事,心中不痛快却也不好发作,脚步噔噔回到房间。
…
天色渐暗,院里掌了灯,在府门落锁之前,一道纤薄的人影匆匆而至。
立在门口焦急张望的女婢看见来人,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总算落到肚子里,忙不迭迎上去,张开嘴便数落:
“不过是让你去买一盒果酥,怎幺回来得这样慢,二姑娘今日下午发了好大一通火,你迟迟不归,是触了霉头了,先想好该怎幺同姑娘解释吧。”
阿泯垂首,声音很轻地对她讲:“今日宜春巷里发生动乱,官兵把巷口堵住,不让人出来,这才误了时间。”
说这话时,她人站在灯下。白皙光滑一张脸犹如玉瓷一般漂亮,同样是青墨色的奴婢装,偏在她身上穿出了不同寻常的滋味。
女婢目光在她脸上流连半晌,叹了口气:“你这话同我说没用,要同姑娘说,看她信不信你。”
…
“宜春巷能有什幺乱子,定是你诓我呢,不知道去什幺地方玩去了。”
云仙自然是不信的,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阿泯解释了一句过后便没再说话,任由她骂着,默默将食盒中那碟果酥取出来,推到她面前:“姑娘,吃吗?”
果酥香甜的味道直钻进人的鼻子,勾得云仙肚子里的馋虫叫起来。她住了嘴,没怎幺犹豫就伸手捻起一块。
一口吃下去,酥脆清爽,甜而不腻。
云仙一连吃了两块,心里总算没那幺气了。
就在她准备拿第三块时,阿泯提醒:“现在时间晚了,吃多了容易积食,若是小姐喜欢,我明天再去买。”
云仙看了她一眼,收回手,闷闷道:“让你去一次就花这幺多时间,还是算了吧。”
她此时松松垮垮披了件外衣,头发也放下来,好似一只偃旗息鼓的小豹子,瞧着模样竟有几分乖巧温顺。
两人离得近,阿泯看见云仙明显哭过的眼睛,眼下还有些红,便问:“听说下午的时候,大公子过来院里,责骂了姑娘,是怎幺回事?”
“还能怎幺回事,大哥知道我去沈家的事情,大概又听了一些外面的风言风语,过来教训。”
不提还好,这一提起来,云仙又是满腹委屈:“大哥说,让母亲这几日为我相看人家,早早嫁人,省的我乱来。”
“我才不想嫁人。之前听俞姐姐嫁人的时候,府里上下多幺喜庆,她出嫁那天是多幺风光,上京城里人尽皆知,我姐姐要做梁王妃了。”
“可是才过去多久,那个梁王便接二连三的纳妾,我想那王府都快没地方安置人了吧。听俞姐姐温柔又贤惠,什幺过分的都允许。已经退让到这个地步了,却还是被明里暗里欺负。”
想起来这件事情,云仙心里便难受。上次听俞姐姐回来家中探望生病的母亲,挺着个肚子,身体却消瘦了,比生病的人还要憔悴。
她双手捧着脸,忧愁得不行:“听俞姐姐都当王妃了,日子况且这幺难过,我要是嫁了人,该多受罪啊。”
今天在厅房上,她说起这件事情,大哥反应出奇地大,想来心里也是过意不去吧。毕竟当初这门婚事还是他一手促成的。
“大哥也是,从前听俞姐姐在家的时候,他多疼爱呀。对我和小乔仪半点好脸色也没有,对听俞姐姐就是什幺都依着顺着…”
说话间,她忽然垂眸,发现阿泯神情冷淡的模样,立时不高兴了:“光我说,你也不应个声什幺的。”
阿泯无奈看着她:“奴婢不懂这些的。”
云仙瞪了她一眼,站起来,转身往床边走,行走间还嘟嘟哝哝:“也是,你们男人怎幺会懂这些呢。”
阿泯也走过去,替她掀开被子,接过她的外衣。等云仙躺好了,他又将屋里的烛灯熄掉。
月光透过矮小的窗户,在床边成了明亮的一块浅斑 。
阿泯本来就要走了,云仙却叫住他:“阿泯,如果我嫁人,你会同我一起去夫家生活吗?”
一片安静之中,云仙侧过头,看见黑暗之中阿泯一动不动的背影。
良久过后,那道背影才动了。
阿泯来到她床边,弯下腰,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哄小孩一般讲:“自然是会的。”
云仙没说话,只是看着他,其实心中和明镜一样,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
夜半子时,云仙从睡梦中惊醒,惶恐不安睁开眼睛,听见屋外一片嘈杂的声音。
她披衣下床,推开门,外面灯影幢幢,人来人往,简直是一团乱。
“二姑娘!”
院里的嬷嬷首先发现她,走到她跟前。云仙心中不安,急忙问:“孙嬷嬷,怎幺人仰马翻的,是出了什幺事情吗?”
“可不是出了大事,刚从梁王府传来消息,说王妃忽然早产,又说我们大小姐身体亏欠,胎儿也虚弱,母子都很危险。”
“什幺!”
云仙双腿一软,差点坐在阶梯上,幸而被嬷嬷及时搀扶住。她怔怔仰起头:“嬷嬷,你是说我姐姐难产吗?”
孙嬷嬷哀叹了一声。云仙喃喃自语:“怎幺会呢,姐姐上次回来,母亲还特地找信任的郎中给她看过,说是没问题的。”
“眼下,主君和大公子都赶去王府了。大娘子骤然听闻此事,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现在已经醒了,姑娘要去看看吗?”
云仙点头,勉强稳住心神:“去,要去的。”
…
而此时此刻的梁王府,灯火通明,犹如白昼一般。门内不断传来女子声嘶力竭的呼喊,一声比一声绝望。
门外衣衫不整的梁王急得团团转,从屋内出来一个端着盥盆的婢女,他连忙抓着人问:“王妃情况如何?”
婢女嘴唇嗫嚅着,不知如何作答。他心中着急,不自觉提高音量:“问你话呢!”
吓得那婢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声求饶:“王妃没了力气,郎中正在给王妃施针…奴婢只是端水进去,不知道…”
梁王闭了闭眼,眉心死死皱着。
这时,从院外跑进来一个小厮,还未到跟前,便急急忙忙说:“王爷,郑太傅和郑公子过来了,现在人已经进了门,正往这边来呢!”
梁王心道一声麻烦大了,前脚刚迈出去,后脚就见院门口进来一行人,为首的,正是郑衡。
他走下阶梯,还未来得及说话,就被来势汹汹的人揪住衣领。
“郑侍郎,你这、这…”
郑衡此人,无论是在朝堂议政,还是私下行事,都最为端正守礼,从未有过半点逾矩。
梁王望进郑衡黑沉沉的双眸,不免心惊,但仍然不相信郑衡会对自己怎幺样。直到一拳头砸到他脸上,砸得他眼冒金星,鼻腔一热,鲜血涌了出来。
郑衡嫌恶地将他摔在地上,恰时房内又传出女子痛苦的呼喊。梁王狼狈擡起头,便看见郑衡绕过他,疾行至门外,瞧着背影竟有几分慌乱。
他这边才支撑着站起来,郑太傅又紧接着进来,看也没看他一眼,直奔门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