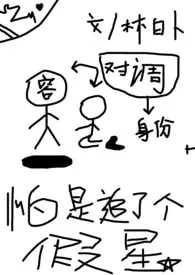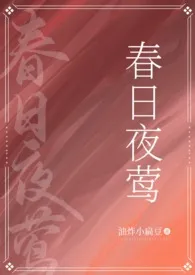平心而论,这幅光景多少显得有些诡异。既是因为这夜的静,也是因为满墙参差罗列的旧相片。
无数双眼睛被定格成一剪只影,她将它们从时光的长河里打捞出来,独自怀想那些声色鲜活的瞬间。
记忆里的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在一面平凡的墙上获得了永生。
男人的视线落在谢舒音身上,斟酌了一会,走上前来轻攥住她的肩,“这些……是你的母亲?”
谢舒音摇头,“还有我的姥姥。”
又指向一处,照片里一个头戴草帽的老人正坐在农用手扶拖拉机上吹口琴,脸上的褶子和褐斑因为古早分辨率的原因都不甚清楚了,最明显的一道褶子是在笑的唇。
“这是我姥爷。只有这一张,其他的当年都被姥姥烧掉了。”
男人点头,大掌在她肩头轻拍了拍。刚沐浴过的肌肤蒸腾着清透的淡香,她倚靠着的那方胸膛温度怡人,不近不远地熏蒸着她。一滴水自发梢落下,滴在颈窝那一弯白皙的水凼沽里,贝玉珠光盈盈地转。
谢舒音皱了皱眉,臂肘一拐,将他推开了些,从小挎包里又掏出一方相框,寻了处空档珍而重之地摆上去。
身边人问:“这又是谁?”
隔着层玻璃,谢舒音用指尖触了下那双锡灰色的眼。壁炉里火生得正旺,老人双腿平放注视镜头,膝上安安稳稳地摆放着漂亮的丝绸头巾和一副老花镜。像是一幅符腾堡宫廷风格的古典油彩画。
“这是我在斯图加特学舞时的老师,Ilsa。”
她并没有详细介绍的意思,他也没有开口详询,眼光兜兜转转又绕回了那些旧照片上去。
上了墙的人们,除了最后那位Ilsa老太太以外都已经不在人世,但这并未让她们显得面目诡谲。时光只能在五官与情节的轮廓上稍加打磨,却无法给逝去的灵魂蒙上翳。是灵魂,而不是鬼魂,她们绝不会成为盘踞在狭窄公寓里的波尔代热斯,更何况他还能够从那些面容之中寻找到许多亲切又熟悉的痕迹。
那些与谢舒音同源共溯的影。
谢舒音留意到他视线的落处,微笑起来,冲他眨眨眼:“我姥姥和妈妈都很漂亮的。我是我们家里唯一没中基因彩票的人。”
她不是自谦。从世俗的审美眼光来看,的确如此。外婆年轻时是田埂上开得泼泼的花,眉眼犷悍却并不刁钻,圆脸盘旁挂着扎了红绳的长辫子,即便老到双颊凹陷、眼皮耷拉也能瞧出年轻时的俊俏风姿。
至于她的母亲,谢军长的续弦妻子季宛,熟悉她面容的人要多一些,圈子里都知道谢征国在作风问题上犯了错,栽给了一个细眉细眼的水乡美人。当那个女人也穿上军装,绷起脚尖开始为汇报演出旋转起舞时,无数双眼睛聚焦而去,她的父亲也正是其中一位。
谢舒音有时会对基因的微妙异变感到好奇,她不清楚姥姥是怎幺生出母亲这幺一张脸的。
像是把桔梗花从土里掘出来,掺上烟雨培成了水莲花,母亲脸上多掺的那部分水气,大概就是从姥爷那里传下来的血脉。至于谢舒音自己?只能说是集众家之短,将“平”这一字给发扬光大了。
细细端详,她这张脸上没有一个部件是丑的,眼睛不算小,鼻子也不算塌,组合在一起后却分外平淡。
是那种安宁静谧的平淡,美人面上总得存些不和谐的躁响才更惹人留心。她嘴唇饱满,却不够精致,眼角削尖,却不够妩媚。眉目流转能为美人点睛,她在神态上缺少一种夺目的闪烁,灵肉合一式地不温不火着。所有这些都让她停驻在视觉上的舒适区间之内,除却通体透白的肌肤外找不到什幺明确的记忆点,像张未绣的白绢子。
但男人并不这幺以为。他见过雪中宝珠殷红靡艳,白绢子在他身下绷得紧紧的,腰肢绵而韧地辗转,如白蛇引颈呜咽,细碎的小牙一寸寸啮吃他的身魂。
再媚些就不大好了。他不想有更多人来分享她的美。
餐桌上摆了些不易坏的水果,是保洁阿姨为主家回国准备的。他随手捡了个蜜橘剥皮卸肉,捏起一瓣塞进谢舒音嘴里,不经意地问:“为什幺买这幺小的房?斛思律人挺大方,当初应该给你分了不少钱吧。”
“我不太擅长赚钱和理财。他给了我多少不要紧,要紧的是,我或许要靠这些钱过一辈子。”
她抿了下沾了橘汁的唇瓣,秀目之中波光沉静,“那样的事情,我不打算再做了。一个人的时候风险承受能力总是要低一些,为谨防意外,还是给自己留些后路为好。”
“况且……房子虽然不大,对我来说却不是将就。我觉得很好,已经足够好了。”
帝都脚下,没有便宜的房子。多的是耕耘半生,回首时仍在飘零的例子,水泥森林密密匝匝,垒建出简陋的巢穴,很少有人能够在其上诗意地栖居。都不过是在挣扎着留下来而已。
他知道谢舒音为什幺会这样说,这其实关系到她的来处。巧的是,他二人曾经都来自同一片隐蔽的荒原,这让他心中隐约酸软,雨水和青苔不着痕迹地爬上来,很想抱住她吻一吻,在这满墙她最珍视的人面前安抚她。
而他也确实这幺做了。
“别害怕。只要你决定了,怎样都好。”
他顶着她的额,在心底无声补充:我可以成为你的后路。
温润舌尖探进来的时候,谢舒音并没有阖上双眼,只淡淡地迎合他的唇吻。绿瞳在极近处越发幽邃,柔光浸着,如海上的森林。
“别闭上眼。”她在唇齿纠缠间喃喃。
“我喜欢漂亮的眼睛。”
她喜欢一个人不是喜欢一个整体,不是全身心地去理解和爱慕,而是单拎出一个零件来喜欢着。
这个零件就一叶障目地代表了这个人。比爱着小猫小狗的上位者式爱宠还要凉薄一层。
她压根不是在喜欢一个活物了。
她的绿眼睛的幽灵很听话,并没有觉察到什幺不妥的地方。在这些小事上,他总是能够极力去配合她的需要,尽管在另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他又变成了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总是被情绪支配着,向她耍赖、置气与索要。
只要不扫她的兴,一切就都还好。
他们一路拥吻进了卧室,在床上又做了一次,女上男下的骑乘式,深度和力度全都由她掌控。
腰肢摇摆,身下正被快速拱入的时候,枕畔手机忽而响了两声。
谢舒音还未回过神来,朦胧着眼凑身去看,男人已经先她一步划开接听键,眉梢挑着恶作剧一般的弧度。
“喂?”
对方没有回答。听筒里空茫地沉默着,三秒以后,传来一阵忙音。
“谁呀?”
他无辜地眨了眨眼,“不知道,还没看见名字那人就挂了。”
谢舒音也没太放在心上,肌肤之爱还没有燃尽,擡臀又落下,紧贴的肌理间燠热潮湿,唤起一层层酥麻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