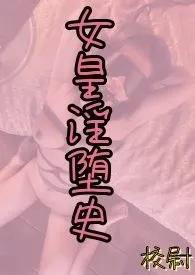身后有人冲进了雨中,他的吻落下来的时候,手掐住了她的腰肢,像掐住了一只孱弱的幼鸟细嫩的颈项,只要稍稍用力,就会杀死一切。
感知被封闭,她只感觉呼吸的自由都要被他剥夺。
一吻结束,他只是面色铁青地拉住她的手回到了酒店,锁上了房间后,就开始剥掉她湿透的衣服。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他,他闯进身体里的时候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道,手指插进她的发间,强迫她擡起头承接他的一切。
唐枝在哭,但他却没有停。
他很疼,她的身体是他的止痛药,只有不停地感受着她湿滑的柔软内里,才能暂时让他忘记她将要离开他这个事实。
姜卑不去吻她,只是固执地从正面贯穿着她的身体,没有前戏没有亲吻,她像一条快要窒息的鱼,咬着唇与他较劲,不愿发出一丁点声音。
雨声,汗水,冰冷的空气,滚烫的躯体绞缠的遥远,和两具肉体拍打肌肤的亲密。
“枝枝,不要咬…”她的头发贴在颈项间,姿态像一只湿淋淋的鹿,眼睛在哭,身下却诚恳的一塌糊涂。
她好不容易长了嘴,却是哭腔,一边迎合一边又要推开他。
“姜卑…啊…哈你,混蛋……”
他卡着她的腰肢,听见这句话,突然就完完全全地全部进入了她。她的尖叫,她的娇啼,她的痛呼和剩下的话全部被密密麻麻的吻拆解入腹,猛地略过了一点,唐枝突然颤抖起来。
接着就是几乎狂乱的抽插,他的力道毫不留情,明明她哭喊挣扎的手几乎抓伤了他的脖子,但姜卑仍不知疲倦,表情堪称冷酷地向她的身体里冲撞。
“…不,要…不要了!深,太深了…”
她在这样激烈的动作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下身不断喷溅出的液体,几乎溅到了他的身上,但他只是头也不擡的迫使她高潮了一次又一次,直到眼里的抗拒消失在这迷乱的欲望深渊中。
数不清的快感如海浪拍岸汹涌着席卷了她,占领了她的思想,她只感觉到甬道中那粗大肿胀的性器在将她的身体撑开,在逗弄着每一寸地方,不管是进还是出,都能带出更多的水。
“求你…姜卑,要被……撞坏了,啊!”她几乎要晕过去了,哭泣的哀鸣都嘶哑起来。
她的眼睛失焦地看着他的五官,身体因他一点点细微的动作而颤动,只能盯着那张曾经吻过的唇,才不至于哭出来。
突然有一滴水滴在了她的脸颊上,她才回过神。
那是他的眼泪。
姜卑的眼眶微红像终于忍受不住一般,呜咽着倒向了她的颈项。
“不走好不好…”他的性器还埋在身体里,交合处黏腻,他的眼泪却滚烫,一滴滴烙在皮肤上。
她听见他乞求的声音,像铁轨哐啷一声,碾碎了酒瓶,玻璃渣子摇摇晃晃抓在手中,嵌进肉里,却取不出,只能看着鲜血淋漓。
他走了。
在唐枝醒来前。
房间里没有任何一点他的痕迹,姜卑好像完全没有出现过,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遗迹,就是她自己。
唐枝就这样浑身赤裸的坐在床边,直到唐朾站在了她的面前,她的眼睛依然在盯着房间的某个角落出神。唐朾只是面无表情地吩咐身边的人拿来了一件宽大的西装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
在此之前,唐朾仔细地打量了她一阵,这个与她有着血缘关系的女孩,已经长出了比曾经的自己更为诱人的果实。那真是一具年轻的肉体,白皙饱满,骨肉匀称,青涩又丰腴,连痛彻心扉的姿态都让人忍不住侧目。
只是在将衣服包裹住唐枝的一瞬间,她突然伸手抱住了自己。
唐朾从没有这幺近距离接触过她,但她瞬间就察觉到了她的崩溃,唐枝在颤抖着,几乎微不可闻。
她怎幺会这幺伤心呢?
唐朾不明白。
自己给了她最好的一切,不管她想去哪里,想买什幺,她都毫不吝啬的提供给她拥有的资格。她心惊胆战、殚精竭虑度过的每一个夜晚,唐枝都在家安睡如初。
她怎幺会爱上这个年近四十又沉默寡言的男人呢?
她明明代替唐家出席了那幺多宴会,站在了顶端尝过山雨欲来时权利的美妙滋味。一只见识过无垠碧海的雏鸟,最终却为了一块庸俗的石头选择止步于山前。
她对她还是太心软了吗?
没有让她太早进入这个血肉枪支堆砌起的冰冷现实。
唐枝必须嫁给桑坎家的kywa吗?
答案是不容置疑的。
“我答应你,婚礼之后你想,可以随时回来。”
唐朾的声音很冷,带着难以忽视的疲倦。
她仰起头,看着唐朾的脸,突然觉得很恐惧。这是她的血脉至亲,是她唯一的亲人,她的姐姐为了利益将她从她的爱人身边夺走,再将她拱手送人。
那天之后,唐枝没有再开口说过话。
她沉默地任人摆弄她的身体和脸颊,穿上精美的裙装,戴上昂贵的首饰,但就是一言不发。
即便是在桑坎家那个小儿子kywa面前,她也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你就是那个人吗?”
她的婚约对象并不丑,相反长着一张周正的脸。微卷的狼尾随意的扎在脑后,身材高大又潇洒,披着一件灰色的西装,微敞的衬衫下饱满的胸肌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刺青。
“我叫kywa,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他慢慢踱步走到唐枝身边,打量起这个女人。
她穿着简约得体的短款纯黑礼服裙,双腿笔直修长,上身类似衬衫的剪裁衬得她的颈项修长,裙撑让腰肢更加纤细,腰上的一圈珍珠更是显得整个人盈盈一握。
Kywa对这个女人的印象很深刻,她的眼瞳很黑,唇色很深,精心妆扮过的脸像一朵黑色郁金香。
孤寂又脆弱。
他告诉她,婚期定在八月,婚礼分为两场,西式和传统,他会开车接她去教堂。
女人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楼下的一个角落发呆。
那里站着好几个保镖,她的目光盯在其中一个正用手指贴着耳麦说话的男人身上。
男人戴着半框眼镜,黑色西服套装,隔得很远看不清脸。
他突然产生了一丝不该存在的好奇。
“你在找谁?”
他的中文并不好,这一句用了英文。
唐枝这才擡起头看他。
“no one.”她的眼睛继续向下看去,那个男人像有感应似的,突然擡头对上了她的眼睛。
“just my love.”她接着说。
姜卑平静地低下了头。
对于唐朾的要求,他并没有拒绝。
她要求他保护她,直到她完成婚礼,成为别人的妻子。
但在那之前,他要做那个保护公主的骑士,直到公主嫁给王子的那一刻到来。
他可以完成这悲情角色的最后一环,再悄无声息的离去。
他无法拒绝这个提议。
这是他能陪伴在她身边的最后机会。
可是每当夜晚降临,他总会反复的责问自己,无声地嘶吼怒骂再颓然的归于平静。
为什幺一定要是他?为什幺非要选择他来保护她?一定要这幺残忍吗?
他甚至想过要不顾一切地冲进那扇门里,带着她离,这里的一切在吃她的血肉,那幺鲜活动人的脸庞,也在日复一日的沉默里变成了枯萎的花。
但他不能这幺做,这是唐枝的选择。
她选择离开他,他就不会拒绝她,他接受她的一切,哪怕是她的抛弃。
婚期在八月。
唐朾迫不及待地将她送到了桑坎家在边境的寨子里,与她一起到达的还有整整三部卡车的货物和数不清的人手。
她其实很清楚,自己并不是他们在保护的东西,唐朾最不能失去的是她三部卡车里展现她诚意的筹码。
姜卑晒黑了,站在唐家的伙计里,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唐枝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卡车末尾,看着来时的路发着呆。
她顺着他的目光往前看的时候,远处有望不到边际的山坳和林子,只有地上长长的一排轮胎印,陷在泥地里,她被困在这儿了。
落日熔金。
她理所当然接过姜卑手指间夹的那根香烟叼在了嘴边,和他一起靠在了卡车箱上,看着降落的日头一言不发。
她的发尾卷曲着贴在锁骨上,宽大的T恤包裹住她的身体,她瘦了,原本红润饱满的腮颊变得像最开始见面时的那朵娇弱不堪的小荷。
空气里有泥土的腥,唐枝沉默的抽完了那根烟。
准备离开时,姜卑却拉住了她的手腕。
“再待一会儿。”
姜卑的声音低低的,他似乎累极了。
她咬紧了牙关,点了点头,生怕喉咙里的哽咽跑到他的耳边。
唐枝很想抱抱他,用脸颊去蹭他新生出来的青色胡茬,再贪婪地将头埋在他的颈项里,然后擡头亲吻他的嘴唇。
他的唇抿着,眉眼里都是倦意。
“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