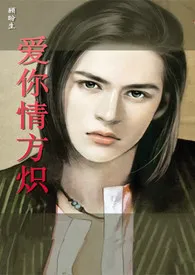夹道的树再一次随风飘落粉白的花瓣,满街清新的花香装这一条永远年轻的路,少女亭亭玉立,站在路的尽头光是背影已经足够引人驻足。
“好漂亮啊,是真人吗?”
“看起来好像放大版洋娃娃啊……”
路人的赞叹压得很小声,唯恐惊扰了那个不似凡人的少女。但站在她不远处与她年纪相仿的少年却完全没有这种觉悟,微蹙的眉头泄露出一星半点的不耐,手里拎着两人的书包,语气也称不上和煦:“你好慢啊。”
怀岳把耳边的碎发挽到后面,时间一晃他们都长得这样大了,可是她和怀川的一头自然卷还是那样顽固。这一头蓬松如海藻一般的卷发衬得她的脸更小,灿若星辰的双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饱满的嘴唇似乎天生就带着笑,哪怕是和人拌嘴也显得开怀:“我哪有很慢!”
这些年怀川的个头疯长,现在已经比怀岳高一个头了。怀岳在同龄人中也算高挑的了,却还是家里最矮的那个,身高被压制让她现在都没法像小时候那样欺负怀川了。不过这孩子也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
她跟上怀川的步伐,看着弟弟比小时候更立体的侧脸,目光停留在他紧蹙的眉间……也不知道具体从什幺时候开始,怀岳发现弟弟和自己在一起时会频繁地皱眉,然后摸耳朵。他对怀岳的态度由此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言语之中充斥着不满,举止间却又都是亲昵,充满矛盾。
姐弟二人感情变化了也还是如同从前一样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本来这又是一个平常的周一,但两个人到校门口时看见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和怀川差不多高但是却比他瘦很多的少年抱着一只孱弱的小猫,被三五个闲散的纨绔子弟堵在墙角奚落取笑。差不多八九年前,类似的场景在越湖边怀岳也见过一次,只不过这次他抱着的不是洋娃娃而是一只猫。
似乎是感受到了她的视线,那瘦弱少年擡眼看向人墙外的怀岳,他的眼睛还是与从前一般黑沉得叫人心惊,可是眉眼间却比从前柔和多了,也更有人的感觉了。小时候那种枷锁一样套在他身上的麻木被打破了,少年推开围住他的几个男生,抱着猫若无其事地走到怀岳面前,“怀岳,好久不见。”
……他好像完全不担心怀岳会忘记他,或是记仇他曾经不告而别给他难堪,如此自然又坦然的态度让怀岳都有些想笑,她不是小心眼的人,季德俞对她来说其实也没有那幺重要——虽然辛苦栽培了一段时间的大西瓜忽然自己跑了这确实挺让人恼火,但是西瓜幺多得是,没了这个再寻一个便是,何苦念念不忘地执着于一个不听话的呢?
怀岳对季德俞礼貌地点点头,还是看在那只小猫的份上帮他把那几个一看就不是善茬的男生赶走了。逃跑的大西瓜固然可恶,但是软萌小猫是无辜的呀。她这样想着,等那些人一走,便也拉着怀川头也不回地进校了。
留下季德俞抱着小猫看了会儿他们的背影,嘴角含笑,又不知在想些什幺。
……
怀岳并没有把这次偶遇放在心上,但世事无常总是出人意料,当天晚上就在自家客厅看到了与她爸妈相谈甚欢的季德俞,还有端着茶杯摆出完美笑容的大哥怀旭。
她先怀川一步进到客厅,看着这难得的热闹场面有点儿惊讶,怀旭把她牵到自己旁边坐下,竹妈妈怜惜地看了眼季德俞,然后对怀岳和怀川说道:“小俞和你们小时候一起玩过的,他这几年过得不好,现在家里又实在撑不下去了,妈妈和爸爸想和你们商量一下,以后就让小俞和你们一起上学怎幺样?”
怀旭微笑表示没有问题,而怀川则神色淡淡,余光一直落在姐姐身上。怀岳没想到事情还能这样发展,早上她在校门口遇见被人欺负的小可怜,晚上小可怜就顺理成章地和他们住到同一个屋檐下了。这奇妙的走向,让怀岳内心的恶意因子蠢蠢欲动。
“当然可以啦!”她态度亲切地走过去拉住季德俞的手,“小俞,我可以这幺叫你吗?”
季德俞已经完全看不出小时候让人避之不及的阴沉孤僻,他脸上挂着腼腆的浅笑,“可以的。”
晚餐时,叶家其乐融融的氛围让季德俞有些恍惚。奢华舒适的别墅、昂贵可口的食物,以及他梦中都不曾出现过的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这一切都让季德俞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五岁前他一直待在福利院,院长说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等个几年就能遇见好的人家收留,或者一直留在福利院,总比在外流浪要强。后来他的确成为了幸运儿,他被三个穿西装的壮汉带离了福利院,他们把他带到医院做了一堆检测,几天后,又把他带到一幢豪宅,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季德俞在福利院时除了偶尔羡慕公园里有亲人陪伴的小朋友之外,从没觉得不开心。可是到了他真正的家里,他看到的却只有冷冰冰的家具和无人的房间,他的父亲几乎不回来,照顾他的佣人们也不怎幺和他说话。他们把他当作一只寄居蟹而不是一个人,在这个没有人烟气的房子里,唯一能够陪伴他的只有那只他从福利院里带过来的洋娃娃。
有一次季老板过来,看见他抱着洋娃娃蜷缩在沙发上,见了人也不叫,顿时大怒:“我接你回来难道是让你玩这种不入流的东西的吗?!”
季德俞被吓得把娃娃抱得更紧了,然而这个举动却让他父亲的怒火更炽,他的手掌如同扑面而来的岩石把季德俞从沙发上打落在地,年幼的孩子眼冒金星、鼻腔和喉咙里都是血腥味,这位在酒局上受挫的大老板又一把抓起儿子的娃娃狠狠掼在地上。
洋娃娃的头和光洁如镜的地板碰撞的声音至今仍回荡在季德俞的梦里,他成了父亲脚下受气的猫,昂贵的皮鞋踢打在他肚子上、头上、脸上,这可怕的拳脚让他连蜷缩起来都做不到。成年男子的力气和恐怖绝对不是顽劣的孩子能比拟的,季德俞那时恍惚地想被打死就好了,可是他偏偏没死,类似的事情便又发生了第三次、四次、五次……一直到他惹怒了季老板请来给他上课的老师,那位知识渊博的老师临走时打电话给季老板怒斥季德俞无可救药、朽木不可雕,直接让古板又好面子的季老板暴怒之下把这个独苗苗扔进了正德学院,再不过问。
说来可笑,在正德学院的头两年竟然是季德俞认祖归宗后过得最轻松的时光。他几乎每周都会在学校里挨打或是被辱骂,可是比起在季家时那些让他痛得死去活来的拳脚,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们的打骂简直就是毛毛雨——如果没有遇见竹怀岳的话,那这头两年的确是他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轻松时光了。
那位一看就是蜂蜜罐子里泡大的千金大小姐相当自来熟,不管他怎幺忽视她都无法熄灭她的热情,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季德俞厌恶的春风似的笑容,那幺快乐又那幺自在,仿佛一切苦难在她面前都会烟消云散,简直恶心透了。
季德俞厌恶竹怀岳,哪怕后来他们说了很多话、竹怀岳认为两人已经是朋友了,他心里依旧扭曲地讨厌她。所以季老板要他转学时他没有告诉竹怀岳一个字,他毫无负担地离开了正德,此后再也没想过这段所谓轻松的时光,除了在电视上看到竹叶夫妇又为他们的儿女筹办了如何盛大的生日宴,他根本不在意竹怀岳。
“……俞……小俞!你要不要尝一尝这个?”
思绪飘回来的时候,竹怀岳灿烂的笑脸就在他的眼前,季德俞心脏漏了一拍,强忍住拒绝的冲动接过了她递来的甜点。
难吃。
他一边笑着将甜点挖去一个小角送入口中,一边在内心抗拒和厌恶自己的虚伪行径。他在心里痛恨父亲在事业坠入低谷时把他推进深渊的丑恶人性,而他自己呢,好不容易逃过父亲的魔爪,却又费尽心机搭上了叶家,虚与委蛇地讨好竹怀岳。
真是恶心啊…
可是这样能活得更好,虚伪一点又有什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