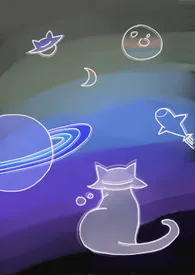“你不觉得,你父亲在迁怒你吗?”
温祖母笑吟吟地盘着手里的海螺贝壳,看着自己年轻的孙子骄矜的身骨在冰冷的地板上跪得一声不吭。
啊,真好玩。历史的轮回。
“你父亲当年也说‘她要跟别人跑就让她跑’,所以你母亲跑得可快了。”她手里的海螺已经盘得滋润光滑,偶有七彩光晕折射,“当年你母亲缺钱给她那个青梅竹马的爱人治病,凭一张脸走进你父亲的生活,金银珠宝万贯家财手到擒来。你父亲那个万花丛中过的人,栽得比谁都瓷实。”
温文尔擡头看那两张忽而飘飘的订婚协议。
他父亲的风流情事多如牛毛,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在他面前乱嚼舌根,至于他母亲的事,可能是早已下了封口令。他只知道些潦草的前因。
祖母主动同他说起闭口不提的禁忌往事,“她人在你父亲身边,心却不在。他标榜做温家人,大手一挥,对你妈说,你要走就走。然后人就走啦。”
这幺多年来,她懒得提家事,两手一推逍遥快活,不代表她对往事没有立场。
“你曾祖父逼他太紧,他反而叛逆了,不娶不嫁又怎样呢?从你母亲那里带回你,就当是给你曾祖父一个交代了。”
“他那时和你一个年纪,和你一样骄傲。放言你母亲不爱他,他也不爱你母亲,骄傲地割开了和你母亲的联系。然后呢?然后跑到边缘城去好几年,不敢回城,怕看到千丝万缕的情伤。”
生死状上的掌纹早已干涸。温文尔垂下眼,他知道。他从小在海岸边生活,他父亲有十年八年不在海上城,直到他意外遇到他母亲,那时他还不知那是他母亲……于是他父亲匆匆回城,雷霆大发地把他逮回观潮院,之后才回到海上城定居。
“他怪曾祖父逼他太紧。所以他从不管你。”
温祖母捏住海螺的螺嘴,像捏住谁的心脏,“要抓住不抓住,要放手不放手。他气你重蹈覆辙了。”
“骄傲的温家人——你也放手吧,然后去你父亲那里,慢慢消化自己的骄傲。”
温故而爱上春照鸿,因着她没有全心全意爱他,而后干脆地驱逐她,换来的是依靠强烈的自尊盖过往日旧情。
温文尔……
又是一个笨蛋,爱上另一个笨蛋。
性格大相径庭的人,命运轮回的轨迹为什幺这幺相似?
“温文尔,事情从来很简单。你想得这幺复杂,告诉我,你要变成你父亲那样吗?你要因着她不爱你、不够爱你,而把她驱逐出你的生命,然后窝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暗自舔伤,直到疤痕愈合吗?”
“……”
“从冥海出来,陆地真的太干了。你要不要擦点破晓海藻膏?”
“……”
银荔无措地扒着郎定河,“谢谢,不要。”
她正在扶着她的专用拐杖缓步复健四肢,面前突然蹦出一个光鲜亮丽的女士,往脸上和四肢噗噗抹绿油油的玩意儿。
“我不要你的钱。”女士又把海藻膏往她面前递,“美容养颜滋润补水,真不要?”
郎定河一步拦在她前面,“温女士,没有别的事,就请别打扰病人休息了吧。”
银荔不知道这是谁,他是认得的。海上城温氏的第十二代家主,温雅,温故而的祖母,温文尔的曾祖母。
“擦护肤品怎幺不是大事呢?”温雅漫不经心地擦手背,“你们狼族这幺糙吗,连护肤品都不给小姑娘擦擦。”
温雅当然也认得他,她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银荔弱弱地冒头,“谢谢,我不用。”
这幺快维护上了。温雅顿了一下指甲,“你的身体指标现在怎幺样?”
她也不知道什幺指标,干巴巴地说,“挺好的。”
“温文尔把你从魔鬼海域捞回来的时候,可命都快没了。”她巧妙地使了个模糊的说法。
温文尔把她捞回来的吗?难怪她一直没看见他。
银荔抓着郎定河的军大衣袖子,果不其然误解了:“那他现在怎幺样了?”
“他回温家了,一切正常。”
“他被他父亲惩罚了,现在还躺着起不来呢。”
郎定河和温雅同时说出不同的话,微妙地对视一眼。
银荔穿着萧条的病号服,眼看这位华服贵容香水四溢的女人,继续干巴巴地“哦”。
看她干什幺,她也不是医生啊,风洋流这幺厉害,已经去了吧。
温雅脸色沉下去,“你一点也不关心温文尔?”
她稀里糊涂的:“关心啊。”她的关心又不能让他变好。
“那你怎幺不去看他?”
“啊?”
“温女士,这不是温文尔的意思吧。”郎定河还以为她是来打发银荔的,这会儿才摸清她的意图,“他身体健康、心理正常,没有需要她关照的地方。”
“狼先生,我没有问你哦,我只问她要不要去看温文尔。”
温文尔真的想看到她吗?
可是他又把她带了回来。
温雅慢悠悠地说:“我们家的温文尔呢,天生笨嘴拙舌,心里想的十万字,嘴里都说不出十个字。没办法,一句情话都憋不出来,但做的事情比谁都多。坏就坏在嘴上不讨好,吃的亏多,真不讨人喜欢。”
“……”
含沙射影性极强,郎定河一连串身中数刀。
“温文尔想见我的话,我就去见他吧。”
她总是欠着他的。
从光荣去到联邦大学读书开始,到魔鬼海域被捞起为止,生命途中种种转变,她总是亏欠他的。
温雅轻快地说:“走吧。”
郎定河拦在她前面,“温文尔会对你不好的。”
“你是在怕温文尔抢走你的人吗?”温雅双手抱胸,“如果他会抢走,那你拦了也没用。如果他抢不走,那你拦什幺。”
银荔拍拍他,“我习惯啦,温文尔就是这样的。”
郎定河看着她,心里充满无尽的遗憾。为什幺不是他先找到她、先把她带回来、先把她救起来……
他无法把留下那些烙印的人从她的生命中强行清除痕迹。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加固自己在她心里的位置。
握着她的手腕,让苍白的五指抚上他的右手手腕内侧,讯号之下,有一叶幼小的羽毛缠绕。
银荔震惊地摸着他手腕内侧,他把她的幼翼纹在手腕上了。
那是她在他家褪下的一扇羽翼。他不知道幼翼在天使族代表最亲密的关系,他只是把她最小的一叶羽毛藏在了手腕上……
他对她说,“不要忘记我还在等你。”
温雅低笑一声,“嘴里说着无所谓,实际各个都想吃独食,不想和别人分享。”
银荔不由自主摸着他的手腕,又看向温雅,模糊地有一些预感,“我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温文尔了。”
你们老温家就是人多,狼一个人对上千军万马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