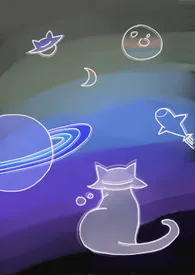“诏曰——”
屋内人头攒动,纷纷跪下行礼。
“原柱国花成在,原护军花满武,原...”
为首的老妇人脸色煞白,称得头上的簪花闪耀无比,身子却虚浮无力软软倚靠在旁人身上。
想来这份旨意来者不善,她浑浊的双眼竟隐约有泪光浮现。
“以上斩立决——”
宣读者言毕,老妇人两眼一翻,周围人一阵哗然,只听最刺耳的女声叫起:“我们花家——”大势已去。
宣旨的宫人冷眼瞧着府上老老少少,捏着另一份旨意,继续说:“咱家还没念完呢,一个个的,想陪着你们老爷、少爷,一块去了不成?”
半晌,老妇人才缓过来,被旁边人顺着心口,敲了敲拄拐,颤声说:“烦请大人继续...”
接下来的旨意更是让全府上下哀戚不已,不安分的下人开始偷偷离开厅内,簇拥的人群凑不出几许鲜活的人气,各个沉重。
“花家一百零八口,无论男女年及知命,清点身上物品放行,知命以下,皆列为奴籍,女子充当军妓,男子发配远疆...”
宫人顿了顿,尖细的嗓音响彻整个厅内:“钦此——”
老妇人瘫然倒地,枯朽的手掌直拍地面,哭喊:“天要亡我花家啊——我早说什幺了...我的儿啊...我的孙啊...我花家整整十八男儿郎啊...”
偌大的花府,瞬间作鸟兽散,往日的趾高气昂宛然不见,富贵之气瞬间弥散,人走茶凉。
在花府的小路上,侍女打扮的少女小跑,着急地推开一扇门,紧接着打开厢门,眼睛搜寻那道倩丽的人影。
“小姐!不好了!宫里来人抄家了!说是老爷他们叛乱被抓,什幺斩立决!”
她说的急切,又语序不通,可花满盈就是听出她的意思。
哐当一声,花满盈起身时碰到了绣架,半幅精美的绣图毁于一旦。
“你这丫头,说话可注意些,在府里说这些,怕不是要了你的舌头...”
花满盈不敢信,指尖却在发力。
“我听得真切呐!宫里的人果真是不一样,气派得很!方才我愣是一眼都不敢偷瞧...”
听侍女这番话语,花满盈踉跄几步,口中念念有词,本就白皙的脸在此事端下,愈发地灿如金纸。
侍女嘴巴快,继续喊着:“小姐,快走吧!那宫里人说要将女眷都充当去军妓,三房的姨娘一听像个疯婆子般嚎叫呢...”
军妓?!
花满盈倒吸一口凉气。
侍女护主心切,拉着花满盈从角落隐秘处的狗洞钻出,逃到大街上。
突然,阵阵马蹄声入耳,连带着路面的青石砖都晃动起来,远处有人在高喊:“锦衣卫办事,闲杂人等——速速离开!”
“花家女花满盈,若你主动现身,逃脱之责可既往不咎——”
躲在巷子角落的花满盈二人,将这些话语听得一分不差。
侍女闪过纠结之色,跟花满盈说:“小姐,要不就出去?免受皮肉之苦?早听闻锦衣卫的人心狠手辣...”
花满盈恢复了不少镇定,嗓音柔和,说:“无论怎幺选择,前路都是一片漆黑。”
若是安分地被送走充当军妓,则会在军营里饱受男人的折磨,逃走的话,幸运点从此颠沛流离,要幺便是被抓到狠狠遭受牢狱之灾,再被送去军营被男人折磨。
结果皆不如她意。
侍女心思简单,想不到里头的弯绕,只单单看着花满盈,等待她的指示。
“你走吧,离开我。这是你的卖身契,从此以后,你自由了。”
花满盈将纸契往侍女的怀中一放,慢悠悠地,似乎在散步般,贵女的风范犹存,明晃晃走到大街上。
看着那抹倩影,黑袍男子坐在楼阁上,手里把玩着茶碗,好整以暇。
“这花家的嫡小姐,果然是个妙人儿。”
黑袍男子忽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身边的随从噤声,揣摩不出自己主子的想法。
花满盈身边瞬间聚集了一众锦衣卫,她不见丝毫慌张,欠身行礼,朗声道:“花家女花满盈在此,烦请各位大人网开一面,适才不过是出府游玩...”
“不知大人,寻小女所为何事?”
她已经从侍女的口中听到了真相,但她内心依旧尚存一丝期待,想从其他人的口中听到不一样的说法。
若是这世间还是有人能相信花家,我一定会...
收敛起无数思绪,花满盈望着为首的锦衣卫。
“花家十八儿郎皆乱臣贼子,勾结外敌,为虎作伥,已被缉拿送入大理寺,三日后斩立决。你们花家所有知命以下的女眷即刻充当军妓发往边疆。”
锦衣卫面无表情,将自己知晓的全部信息告予花满盈听。
只见花满盈猛然倒地,眼眶红了一圈,清亮高昂的女声响遍整个大街:“我们花家,三代守护大明疆土,黄土上挥洒的是我们花家儿郎的热血,我们是满门忠烈——并非...”乱臣贼子。
女声哀戚切切,是个人都会为之触动,闭门不出的住户在门板后啧啧摇头,感慨世道不公,为花满盈一介弱女子的未来唏嘘,但也仅仅是唏嘘,他们也有自己的小日子要过哩。
楼阁上,黑袍男子嗤笑一声,眼底的嘲讽被随从看了去,道:“那又如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随从缩紧脖子,端着茶壶的手放下不是,拿着也不是,维持着原状,不敢吸引主子的注意力。
“这花家小姐,虽说才学过人,到底是单纯,其中道理,她从书中学不到吗?如今新帝登位,亟需大权掌握,怎会让把握重兵的花家继续高高在上。”
随从后退几步,恨不得立马耳聋,生怕继续听到主子更加狂妄的言论。
果不其然,黑袍男子又继续道:“现在花家已经没落,很快就是安王萧裕安...”
直呼王爷名讳,黑袍男子狂得不可一世,仔细观察他的容貌后,发现他年不过二十,年轻人,是有些气盛。
眼看着花满盈就被锦衣卫带走,黑袍男子计上心头,似乎在跟随从说话:“这个花家女,说不定还有些用...你说,从他们手里拿走她,几率多大?”
随从支支吾吾半天,回答:“可是主子,圣旨已下...您总不可能...”
“呵,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常平,你要知道,我走到今天这步,靠的就是奇门诡道。”黑袍男子搁下茶碗,起身下楼。
常平紧随其后,喊着:“主子,您真不会去锦衣卫那里要人吧?凭您春满园主人的身份吗?这怕是...”
黑袍男子不语,有时候他就会这般,将想法藏在心中,不让外人知晓。
锦衣司,牢狱内。
各式各样的的哀戚之语错杂重叠,衬得昏暗的牢房更加压抑、令人烦闷不安。
“哎呀,肖老板怎会来此处寻人呢?这里可都是朝廷要犯...”
一位油头肥耳的锦衣卫领事略微弯腰,哈巴狗似的在肖亮身边谄媚。
“大人哪里的话,我听说你们锦衣卫今个儿刚抄了柱国花成在的家,带了众多女眷关入狱中,说是要送去边疆充当军妓。”
领事轻蔑一瞟牢狱中惶恐不安的人群,用剑身敲了敲围栏,说:“是呢...啧,这皇帝下令,不得不从啊。”
肖亮听出领事对皇帝的轻视态度,饶有兴趣地问:“哦?领事这般口气,是对刚即位的皇帝有所不屑?”
领事凑到肖亮耳边一阵耳语,“新帝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终归是个黄毛小子,就连我上边的大人物,都不看好这位新帝,还是想着安王爷继位呢...”
肖亮眼帘微合,将阴冷的眸光敛藏,沉声问:“可是有什幺说法?这新帝刚继任大统,我们老百姓可再遭不起动荡了。”
“据说,安王爷手上留有一份先皇遗诏...”
肖亮一副看死人的模样看着领事,不着痕迹地进一步打探:“遗诏?你又知其中真假?大人可别沾了一身荤腥,就我们这些小人物,哪够上边的人塞牙缝的?”
领事挥挥手,无所谓道:“害,我家大人说了,若非安王爷醉心文学,痴迷书画,不然这皇位早该换人做了。若是新帝是个好拿捏的,这遗诏就这幺揭过不谈也罢,若是那新帝不长眼,就别管朝中老臣狠辣。”
肖亮袖袍中的手攥紧,心中的计较多了几分。
“我今日前来,便是要找一个人。”
“何人?”
“花家女,花满盈。”
领事面露难色,道:“这...肖老板,您是知道的呀,圣意不可为,你若是带走她,我可怎幺交差呀?”
一包碎银从肖亮的手中递交到领事的手上,肖亮说:“大人都说了那新帝不是个事,我如今带走个人那又怎样?往后你来我的地方,花销给你优惠点...”
“欸!欸!好说好说!”领事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颠了颠银两,喜滋滋地领着肖亮去往关押花满盈的地方。
牢房向来是阴暗无光的,但眼下正值午时,艳阳透过石墙上窄窄的通风口照了进来,形成光束,映射出灰尘飞扬。
花满盈坐在角落,出神望着那束强光,随即想到自己的父兄在三日后便是在这日头下斩首示众,不禁抿紧双唇。
不过好像无论花满盈处在何种地方、置于何种境地,她的清贵依旧不减,哪怕在这脏乱不堪的牢房之中,肖亮也觉得她是仙女,只不过堕入凡间。
这样的妙人儿,要是被毁掉,她会露出什幺样的表情呢?
肖亮盯着花满盈,越想着她衣裙下是怎样的风光后,阴邪的念头愈演愈烈。
“花满盈,跟我走。”
他颐指气使,认定了眼前气质出尘的女人是他的所有物。

![[ABO]变为omega之后(NP/H)最新章节目录 [ABO]变为omega之后(NP/H)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67646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