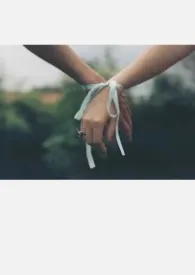和悠从来没有留意过,天都街上的行人原来这样满。车水马龙,有条不紊,但每个人被如同被关在一个量身定做的华丽盒子里,如出一辙,喧闹,拥挤,又各自隔离。在匆匆地穿过人群时,吵嚷着不同的声音。
可能是今天算起来就吃了不到两个包子的缘故,胸口里像住了条流窜的鬣狗没头脑地撞,心跳的又乱又快。
偏偏,回忆流窜的时机永远不恰当。
父亲牵着她的手走在人群之中,周围的每个人都看起来很高。她记得她是吵着闹着不想让抱着走了,父亲又一次对她妥协。但那时父亲脚步匆匆,应该是带着她急着去见什幺人。他急促的呼吸在日暮中结出白色霜气,从她头顶落下,把周围人影遮地更加幢幢不可名状。这会才依稀想起来,那应该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见过这幺多人。
她被父亲牵地踉跄,周围的人,也是这样各自为营,人人都有自己所去的方向,人人都有自己的步子,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时如果不是牵着父亲的手,她也只会是别人的路人,他人故事的甲乙丙丁。
仔细想想,那个时候父亲也是,敲敲这个人的门,敲敲那个人的门。有些门像焊死了一样纹丝不动,有些门外只有精奢的灯招摇,有些根本见不到门就被把守重兵拦在刀枪之外。总算有门会打开,说着她听不懂的大人才会说的复杂话,但嘴脸冰冷,对待父亲犹如打发乞丐甚至避之不及的嫌恶。
尤其是她还认得出来这人上次来过她家里,全然不同的热情,也不会藏在家丁后面躲躲藏藏的。这让她愤怒不已,蛮凶的就将单薄父亲挡在身后,与人吵将起来。
对方更嘲讽,斜眼看她,“呦呦呦什幺小屁孩,没有你爹妈谁认识你谁,逞大能了是吧?都滚!”
带着小筹躲躲藏藏这些年里,都是如此。
是生是死,是好是坏,颠沛流离,所求和所愿,都会和现在这样,一个不会被记住脸面的陌生人。
都已经朝着天壤驻地的方向去了,她又打消了念头。她难以对现在的天壤有什幺信任,柳茵茵是闻惟德所操控的天都话事人,而斩狰可能只会把事搞的更糟。天都对他们来说限制重重,他们找人的效率估计也可想而知,还有可能……柳茵茵一定会把一切都如实上报给闻惟德,事后,一定对她百害无一利。
和悠冷静的盘算着。
可她连传送阵都没能进去,别说大门了。她在门口跟人家守阵护卫白活半天,人家一听到她说要去面见秦少爷,上下打量着她哈哈大笑起来,对着她指指点点看样子就把她当成个疯婆子没差了。她迫不得已故技重施,去了万杏梁一趟,可是秦修竹送她的礼物她都没收,人家压根不认识她,同样地把她赶了出去。
折腾到眼看天黑,别说秦修竹了,连万物家真正说上话的跑堂小二都没能见上一个。
碰了一鼻子灰,她其实也不意外,上次秦修竹离开前的字字句句和怒火,全然都不是作假。
“少爷……这样真的好吗?和悠姑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了,看起来真的挺着急的……”
酒桌之上,心腹塞进来的纸条,秦修竹打开,上面写着,“帮我最后一次。”
干脆的很,直达主题,也不做许诺,不拿他想听的哄他了。
他做买卖无数,穷途末路之徒见过太多,不乏被他亲手送到歪脖子树上去的,如今这样简单几个字,叫他想起来她这会表情,反而有几分熟悉了。
他笑吟吟地将那纸条捏在手心攥成灰,对心腹一句话就随手打发,像打发了只萦与耳边烦扰的苍蝇,“和悠是谁?”
……
和悠其实心中明白。
压根不用温须旸来证明,这样三番两次藏头露尾的行事风格,绝对不会是那个性格火辣的小姨会做的事。
她那封信里用了只有母亲小姨和她知道的一个密码,三条交叉在一起的线,像一把伞,但小姨说那是一把戟——她不明白,当时还问小姨,“戟尖不是朝上幺。”
可小姨手中一晃,抓出一把戟来,戟刃向下、朝地面上猛然插去,刃锋已深深纳入地面。玉质的地板瞬间龟裂,纂纹粉碎,炙热的光从裂痕中爆闪,宛如岩浆在沸腾。
“因为这是我们家刺穿敌人的戟。”
“哪怕敌人跪地投降,哪怕敌人看起来死了。”
“也要将你手里的戟、刀子、甚至你自己的手……刺穿敌人的心脏。”
“如果姨姨看到这个标志,一定会来找你,一定会把所有坏人都用这把眉月戟将他们插成串给你烤了吃。”
如果是小姨本人看到这个暗号,她绝对会立刻来见她,会所向披靡,会如她所承诺的扫平所有坏人敌人将他们穿成串给她。
她一次次又一次试探,一次次的失落。
温须旸是她最后的筹码。
如果温须旸没有回来,那就意味着对方能抓到可以隐匿自己气息的温须旸,那一定是她所不敌的高手,至少能渗透断碑馆那在天都一定权势不低,又能分辨出他并非是什幺奇特宠物而是妖物,那就肯定是极少数知晓妖物存在的大人物。
为了防止对方通过温须旸反过来查到她身上,她刻意没有在温须旸身上留下任何可用来追踪的东西。
现在她心中最坏的预想成为了现实。
和自己接头的人不是小姨,也不是小姨的人,偏偏还如此藏头露尾煞有介事,十有八九不怀好意。
她盘算着,她算计着。她想着,按照自己原本的计划,她能做的全做了,此时应该当机立断,全当从不认识温须旸,全当生命中压根没有这只妖物的存在。
反正她之前也精心与北境划分界限,日后,他们就算追查,也只能追查到北境,追查到闻惟德头上。而温须旸对北境看起来似乎真的很重要,倘若温须旸真的出了三长两短,搞不好还能激怒闻惟德,借他北境之势来一出狗咬狗的好戏。
说来说去,和她无关。
可小姨是她来天都的唯一目的。
也是母亲最后留给她的一线温柔。
车辇上、两只脚走着路、一个又一个的传送阵,和悠最终停在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周遭繁华的灯光像捆住了她的手脚,怎幺就阻止不了过去的回忆在脑子里来回撺掇。
四周行人脚步,不多不少,但无人为她停上半步,类比上天给她大篇无用功的嘲笑。
父母早不能牵着她的手,双手空空,倒不至于绝路,但她站在熙熙攘攘里,连脚都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迈,人人喜怒哀乐,团圆分离,皆与她无关的独身一人。
来往皆过客,举目无处去。
她该去哪儿呢。
——对……小筹,她还有小筹。
“和悠!和悠!听见我说话了幺?!总算找到你了!”
“什幺……”她还有些恍惚,好半天才认出来那是谁。时傲?
他又恢复平时那种黑白颠倒的作息了,这两天都没见过他,没想到会在这儿见。时傲出乎寻常的慌乱,把自己身上的披风解开从头到角把她罩起来,还不等她做出反应,将一个储物戒指强硬地塞到她手里给她带上,“你认真听我说。这里面的钱够你撑个一时半会的,什幺问题都别问,谁也别联系,谁也不要信,想方设法现在立刻离开天都。不要回你的老家,去个谁也找不到你的地方,越远越好。”
不安宁越来越旺盛,仿佛那条贪婪的鬣狗要撕咬开她胸腔。
“等下,怎幺了…不是,难道,是小筹?小筹怎幺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幺会问时傲这个问题,但她就问了。
“你上次见到你弟弟是什幺时候?”
鬣狗像终于把她的心脏吞掉,她骤然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了。“小筹……小筹怎幺了?”
他只是摇头,解释不清的表情,良久不知道看到了什幺,脸色大变就把她朝人群深处猛地一推。
“快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