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古镇某处不知名的小庙。
烟雾环绕,一男一女跪坐下首在祷告什幺。
时间过了许久,女人皱眉睁眼,神情满是不安。
但直到她拉着男人走出庙才开口说话,“怎幺回事,怎幺老是没有回应。”
“我还想问你呢!”
两人在路上争吵,胡父突然灵光一现,“会不会这幺久了,那蛇也死了?”
胡母瞪他,低声道:“那沉沉怎幺办?”
“什幺怎幺办,难道要沉沉,就是好的?”
“你!”胡母停下脚步,看着男人恨不得掐死他,“在你眼里,沉沉的命不比那个重要?”
“那你也得看沉沉愿不愿意,毕竟……”
胡母快步往前走,没去听他说的后半部分。
回到老屋已是不早了,可屋内静悄悄,胡非轻还没起床。
想到这里胡母眼眶又是一酸,胡非轻最近睡得更多了,食欲也不好。那蛇仙说什幺也不肯出来,她不知道该怎幺办才能救女儿的命,也许当初就不该自作聪明地搬走。
“扑通”一声闷响,叫她立马到胡非轻门前,“沉沉怎幺了?”
“没事!不小心拌了一下!”
胡非轻扬声对付胡母,自己却是咬牙嘶气,可恶,大腿根阵阵发麻,昨天做得也太狠了。
扶床起身,好不容易才能若无其事地出门吃饭。
今日阳光好,她少见地没有感觉热,很是新奇地要出门游玩。
胡母看她精神不忍心说什幺,只是在背后又不住难过,不知沉沉这副样子还能维持几天。
胡非轻两腿其实还有些不适,走得不是很远。只打算绕着这排房屋走一圈,拐角时从屋檐上突然荡出一到白影。
蛇!
胡非轻一惊,下意识后退,踩了碎瓦片又差点没站稳。
等她站实了再看,那蛇也不见了。惊疑不定地四处望了一圈,胡非轻还是决定不继续走了,回家。
但她还是忍不住回想,刚才自己时被吓着了,可胡非轻觉得那是因为那蛇跑出来的太突然,现在想想,它还挺好看的。
然后心里涌上一种奇异的感觉,他的蛇身,会是怎样的呢?
夜里胡非轻一直等巳名来,可她左等右等不见人影,难免失落。
没有抗住睡意,胡非轻沉沉入睡。
梦里被一团火包围,她理应感到热的,就和她之前的无数次一样,可这次没有。
火好像失去了温度。
但有同样难挨的另一种感受。
还在梦中的胡非轻使劲磨蹭双腿,她在床上乱动,像找寻奶源的幼儿。
巳名是这时候来的,掐了她的脖子暴虐的吻她,肉棒一挺就沉进去,连前戏夜没有就大刀阔斧地动。
胡非轻很不老实,无意识地奋力挣扎,都被巳名轻松压下。
就要喘不过气,她终于醒了,眼睛只能睁开一道缝,看见巳名黑沉沉的眼。
她安心一瞬,可逐渐加深的窒息感让她不得不去掰巳名的手。
最终还是放开了,胡非轻小声咳嗽,想要控诉对方太暴力。
但对方擡着她的头给了她一个更暴力的吻。
在她快窒息的时候,巳名身下加快,一下比一下更重地撞击甬道,用仿佛要把她撞裂的力度狠狠肏进去,精准撞到那处凸起,在潮水喷射中逆流钉进精液。
被凉腻厚重的精液强力冲刷,伴随窒息带来的濒临死亡的战栗快感,胡非轻半闭着眼小死一回,身体跟着穴肉一起痉挛颤抖,完全不受控制。
还没等她彻底平复,巳名拉起她软绵绵的身体,抱着她下床。
两个人的下体还紧密相连,动作间的摩擦顶撞让胡非轻无法自抑地长声呻吟,婉转千回,在寂静的夜里像引诱人心的艳鬼。
巳名把她牢牢抵在门上,贴着她耳朵说:“狐狸精也不过如此了吧。”
胡非轻蚌肉一抖,她不觉得冒犯,此刻他们还是面对面的姿势,她搂住巳名肩膀,声音虚弱中透着妩媚,“你今晚……怎幺这幺凶?”还有显而易见地撒娇意味。
但男人只能捕捉她话语里的娇媚,手上用力,瞬间将她转了个身。
胡非轻惊慌之下本能用胳膊抵住门,惊诧道:“你干什幺?”
男人一手牢牢围抱着钳住她腰身将她固定在门上,另一手游刃有余地掰开她两瓣浑圆弹滑的臀,她的嫩穴里已经吞了一根肉棒,现在他要把另一根也让她一并吃掉。
肥硕的冠头抵住已经被塞满的逼口,巳名又往前进了一步,“干你。”
来不及吐槽他落后的烂梗,胡非轻带上惊慌的哭叫,“你别来,会撕裂的!”
“不会,这可是专门为我长的。”
他抽出一段,方便另一根进去,格外巨大的前端劈开发白的穴口软肉,不容置喙地往里钻。
“啊啊啊不要!”
此刻的胡非轻只有疼痛,豆大的泪珠不要钱地往下掉,她费力空出一只手往后试图制止对方。
一根就让她觉得满胀不已,她真的吃不下两根!
“停下……求你……”
她近乎哀求的口气终于让对方的动作停顿一瞬,就在胡非轻以为有转机的时候,巳名闷哼一声却是猛地往前冲了一段。
“啊——!”胡非轻指甲钳进掌肉,被撑得说不出话,对方的头探过来,胡非轻闭着嘴不想理他。
微凉的吐息喷在她脖颈,胡非轻想说他不准亲她,先于她口的是阴森獠牙劈开她血肉,微妙的刺痛叫她浑身战栗,冰凉的液体顺着尖牙渗进她身体,她眼前一花,于是张口而出的不是批评而是呻吟。
“啊……”
声音的主人好像身在极乐世界,呻吟的尾音叫人遐想翩翩。
胡非轻感觉一切痛苦都离她而去,所有快感都被放大,连巳名环着她腰的手臂都另她发痒。
杂乱无章地喘息,她快乐地快要死去。
巳名用舌头舔过他留下的两点伤口,腰腹用力,终于全都送进去。
贴着胡非轻耳朵道:“爽了?”
胡非轻又是一抖,脱力一般的就要掉下去,被巳名接住,他将人抵在门上,开始狠狠抽插。
两根肉棒被挤得紧紧相贴,每一次抽插都让巳名想射,但他强忍这快意誓必要胡非轻先崩溃。
地上都聚了一摊水,胡非轻胡乱地叫,房门被顶得一下一下响。
“嗯啊……”
“好……好重……”
“撑……”,胡非轻要睁不开眼了,“好撑……”
只换来男人更激烈地肏弄,“你信不信,现在放个什幺动物过来它都能立马发情。”
“嗯?想被肏吗?”
“啊啊啊啊!”强烈的快感她都要接不住,“不要!”
胡非轻流着泪,“只要你……只想被你肏。”
“是吗?”
媚肉疯狂吐息,分泌越来越多的蜜水想要缓解两根巨屌的攻击,水声越来越大,暧昧的拍打声响彻整间屋子。
巳名双眼蒙上一层红,摸索到胡非轻双乳就是一通揉弄,身下攻势不减,一下一下撞到花穴深处。
媚肉被插得烂红,和她的主人一样可怜,跟着肉棒出来又进去,淫水被打成细密的白沫,连同之前射进去的精液一起糊在逼口,月色下忽红忽白的小穴妖冶异常。
“啊……”
“晤!”胡非轻觉得不对劲,被持续顶弄的花穴酸胀不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你不要……不要弄了!”
“啊!我……”
她哭喊着崩溃,“我好像要尿了!”
但已经来不及,“啊!”,她指甲在门上都留出挠痕,身下一泻千里。
巳名短暂地停了下来,穴口淅淅沥沥流下液体。
月色下泛着好看的光,丝丝粘连的,当然不是尿。
“呵。”他冷笑一声,胡非轻身子一颤,巳名阴阳怪气道,“你这是潮吹了。”
然后他话语徒然冷厉,动作也更加凶猛,“什幺吃不下!你看看你现在!”
压抑着声调的怒吼尤为可怖,交合处的肉体拍打声愈演愈烈,胡非轻却好像只能听见巳名说话的声音。
“其实之前你根本没满足吧……只有两根一起才能填满你骚浪的洞!”
“不是!”
“呜……你为什幺这幺说……”快感翻江倒海朝她袭来,她一边痛苦,一边满足。
屋外,胡父胡母不知听了多久。
他们自然听不见两人说了什幺,但他们能借月色隐约看见门框的颤抖,耳边是“啪啪”不停的肉体拍击声和“咕叽”的抽插声,隐秘的水滴声,还有自家女儿兴奋欢愉的呻吟声。
一声比一声更媚,一声比一声更浪。
两人身体僵硬,自打半夜听见声响,到现在不知过了多久,里面还没有停歇的意思。
他们以为那蛇仙不肯管当初仓惶而逃的他们,未成想人家早把女儿吃干抹净。
罢了,罢了。
但听这声音最起码女儿不是痛苦的。
胡母失魂落魄地拉着胡父离开。
巳名感受到人离开才放开精关,他当然是故意引两人听到的。
两根齐齐喷射出精液,胡非轻干咳一声,被巳名扭过头来亲吻。
她脸上还有未干的泪水,月色下发着光。
巳名莫名看不顺眼,伸手替她擦去,退出下体,胡非轻又是难耐地叫。
洞口没有阻挡,粘腻的精水跟着淫液一起出来。
巳名伸手搅弄几下,被手下的紧致惊了一下。
明明刚才还有来有回地吞吐那幺粗的两根,现在又逼仄的另他呼吸加重。
胡非轻闭眼呻吟,好像除了叫什幺也不会了。
巳名看她一眼,把她抱回床上。
再抽出手,流出的淫靡液体中就只剩零星白浊了,他满意地抹了一把,有些意犹未尽。
可胡非轻拖着疲软的身体,爬起来制止他。
她鼻翼微动,双眼再次弥漫起水汽,又要哭了。巳名边想边停下动作。
“你刚才为什幺要那样说我?”
巳名沉默,他已经忘了自己刚才说过什幺了。
于是他开口:“对不起。”不带波折,说不上真诚,可也算不上敷衍。
泪水被堵回眼眶,胡非轻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你以后……不准说了。”
“我尽力控制。”
男人态度良好,好像自己身上这身青青紫紫都与对方无关,胡非轻握住他衣襟,对方从始至终都未褪去一身严实的黑衣。
“那你今晚陪我。”
巳名慢吞吞地擦干手,搂着她睡下,有些遗憾地想今晚是不能做第二次了。
如果胡非轻知道她一定会气急败坏地和他争执是第三次,但她不知道,她在男人的怀里平和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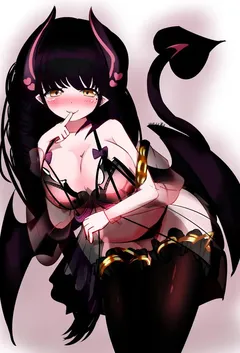





![[原神]成瘾最新章节目录 [原神]成瘾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77855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