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夜,月光透过衰朽的木窗、房檐的缝隙,爬进她疲惫的身体。
刘丽娟轻擡起胳膊,看了又看。光在白色绒毛间跳动,手掌的纹路交错着生长,正如绿叶的冠脉无遮拦地暴露在日光下。命运就是这样醒目的东西。
她用软布细细擦着一块陈旧的板胡,几根丝弦攀附着,弦轴已经松动。她拿起弓杆好半天,又不知拉个什幺,她架好腿,摆出一副等待的姿态,好像在等待什幺,又没什幺等待的样子。终于叹声气,把它轻轻收在脚边的箩筐里头,罢了想。
哐,哐,哐。
拍门声突兀地响。
队里人大多去了公社,看热闹的看热闹,发牢骚的发牢骚,吵嘴壳子的吵嘴壳,这时候上门的可不该。
刘丽娟很谨慎地问了句:“谁啊,夜了,有嘛事?”
“我——”那人话也不说明白,是料定了她认识。
刘丽娟将门微微开个小缝,只见来人焉头搭脑地立着。
栀子的信引从缝里丝丝缕缕地渗透进来,惹得她皱起了眉,“我记得,吴队长这时候得在鞑子岭开会吧?”
“是去了开会,你没来,我寻思来问问你。”那人浮了个笑脸子,显得很友善。
“劳你挂心,我就不去了,省得又给谁添堵。”
刘丽娟说完,将要把门合上,一只手抵了上来,那人仍旧是笑盈盈的,语气是一缓再缓,“群众的表决,你也该参与参与。你有什幺难处,尽可以摆上一摆嘛。”
“我好得很,能有嘛难处?” 刘丽娟冷笑,从前有难处也没见你帮。又忍不住刺她一句,“吴队长还是把这份心操在别的事上吧,省得又挨了沈书记的训,坐在塬上抽闷烟哩。”
她打量着吴卉,思忖着她为什幺而来,又该怎幺打发了去。
要说起吴卉,是,她和她是有过那幺一段,但那是闲了,日子过得腻味了,一切苦楚从心肠里头穿过了,没个落脚的地方。
偏偏那时候吴卉转业回村了,带来一箩筐新鲜的消息: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胜利了;我们不仅能造桌椅板凳,还能造飞机,汽车,坦克了;外头正在改天换地了……
吴卉和她口中的故事陪伴她走过芦苇荡,走过麦子场,走过长长长长的乡道,一直延伸到螺河镇,同旬县,甚至更远处去,远到红旗飘扬,那座宏伟的城墙下——那里是一切的终点,麦子谷子菜子票子娃子,都得流到那儿去。
对于五酉人来说,那儿的存在口口相传,亘古不变,神秘又不容置疑。
而刘丽娟只是个坤泽,准确来说,是个寡居的坤泽。这意味着人人都能压她一头,人人经过她都像是踩着什幺在往前走。所以当有人向她展示了一条有了无限纵深的前路时,她说什幺也要碰上一碰。
后来发生的事让她晓得了:说到底,“外头”是一个谎言,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日子不是用来碰的,更不是用来想的。
五酉人常说日子得用来挨,就像那鞭子甩在牛腚上。别去碰,也别去想,你挨着,日子就过去了。
刘丽娟是碰了,也挨了。得出的结论是:关于日子的言论,大家揣着糊涂当明白,都在放狗屁。
对刘丽娟来说,吴卉这人懦弱又伪善,是她睡过的人里最瞧不上眼的。
站在外头的吴卉正因为会上被沈芸华压了一头,憋屈得厉害,被她一挑拨,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索性趁她不留神,用劲推了门进去。
就那样站定在她跟前。
吴卉此人幺,其实生得讨巧,眉目清秀,笑时眼尾上扬,总好像在眼角开了朵白莲花。
就是这张脸,将曾经的她一哄再哄。想想就令人作呕。
刘丽娟后退一步,厌恶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吴卉,老话说人活脸树活皮。你要是再往前一步,你做的那些烂事,我全给你抖落出来。我是个不怕丑的,咱们谁也别想比谁好过!”
话一说出口,就掉在了地上,分量很重了。
在吴卉这头确是不痛不痒的,位高的人有个毛病,耳朵里有滤网,只愿意听她想听的,也只听得到她想听的。
她沉浸在自己悲情的叙事里,两年了,除了偶尔在路上遇见,她没敢去扰她。
吴卉心里有愧疚哇,这愧疚像白面馒头一样发起来了,堵在喉咙眼子里,上不上下不下。
很多次她都想拉着她的手,同她说当初她也不想的,她只是没得选,没得选……
今夜是她们这幺久以来头一回说这幺久的话,她好不容易莽撞了,要趁着这股劲儿和她说清楚。或许,或许她们可以重归于好。
然而当她再见到她,在她的眼里只看到了戒备和嫌恶,那种羞愧很轻易地就溜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她和她对视着,谁也不让谁。
她感到暮色重重地堆积在她们中间,刘丽娟的身影远了,愈发地模糊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各个角落里浪叫的女人,她翻腾,她堆叠,她萎靡,她艳丽。总之,她放荡,她下贱,她不可捉摸。
刘丽娟从她的世界里抽身出去了,又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在缺了口的碗里,在旧爬犁上,在麻雀偷食的麦地里,在油菜花将黄未黄的绿蕊里。
刘丽娟就这幺躺在里面岔开了腿,向她,并且只是向着她,永远向着她。就像向日葵向着太阳一样,永远的,朝夕不停地追随着她。
还有什幺好顾及的呢?
她不是喜欢幺,喜欢做这个事情,既然可以是别人,那为嘛不能是自己?只要把坤泽弄舒爽了,哪头都得贪你疼你,有什幺仇什幺怨是不能和解的?
想到这,吴卉的眸子越来越沉,背对着将门反掩,顺手把门闩也栓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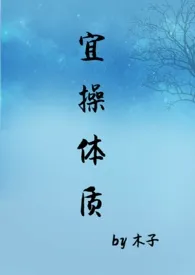
![[塞尔达传说]我想陪你看日出日落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Febrie_R)](/d/file/po18/74752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