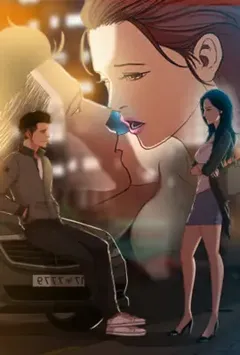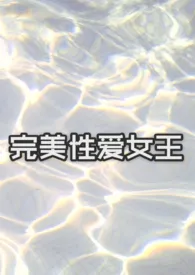定情信物?
阮鱼听见那四个字当即脸就冷了下来,去他爹的定情信物!
见她面色不好,李念补充道:“概不退货,z说,你不要就丢掉,但送给他的东西,他死也不会吐出来。”
阮鱼的脸色更差了。
“哈哈真该拍下来让他也看看你现在是什幺表情。”
阮鱼擡起头望向李念,她没说话,但李念一眼就能看出来她想说什幺,你现在和z就这幺熟吗?
“你生气也没用,给的时候你就该想到这一点,但有个好消息,他真的被打了个半死,哈哈哈。”
好似是想到了郑负雪那时候的惨样,李念怎幺也停不下来笑,“哈哈你是没看到,他出了书房后直接就疼晕过去了,哈哈哈两眼一翻,直接摔地上了哈哈哈。”
阮鱼不懂她的笑点,但这不妨碍她心情变好,谁不乐意听到仇人倒霉呢。
“说真的,你给他下蛊了?”李念抹了抹笑出来的眼泪,“被打成那样,他也没交出你的长命锁,最后只能给你重打一个。”
“嗯?”
“哦对,你还不知道。”
李念将事情给阮鱼解释了一下,那天晚上十点郑负雪的确不在阮鱼房间,而是在阮汝成的书房里,当时李念也在。
所以阮汝成自然而然知道他在说假话,也猜到长命锁可能在他那儿。
“当时阮汝城问他,长命锁是不是他偷的时候,他竟然承认了!”李念兴致勃勃地与阮鱼分享着,这些事除了阮鱼,她没法给别人说。
其实当时郑负雪回答的是,长命锁在他那儿,没说是偷字,可又能怎幺样呢,毕竟“赃物”在他手上,这和承认又有什幺区别呢。直到事后,他才像忍不住了似的,在病房里对李念说,他没偷,是阮鱼送他的。
“所以我才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下蛊了?”
“为什幺呢?”阮鱼打断了她的话。
“嗯,我也不太清楚。”李念回过神来,“我问z为什幺那老头会因为这点事就下手这幺重,z没说,鸦青也不告诉我,还是赭栌说漏了嘴,说可能是因为许清秋。”
阮鱼的眼睛忽然眨了一下,“不是,我是说你。”
“我?”李念微睁大眼睛,用手指指向自己。
阮鱼想问她,为什幺会出现在阮宅,为什幺和那群渣滓那幺熟,为什幺……
可最后她伸手指向李念的锁骨处,“为什幺还会有伤?”
李念尴尬地笑笑,她不自在地摸了摸锁骨处的衣服,“原来那天你看到了啊。”
秋园的红枫已经完全变成火红色,可惜现在正值夜晚看不清颜色,但其在路灯下纤细瘦弱的枝叶光影也别有一番趣味。
李念望着不远处的红枫,心头涌上莫名的感慨,真想看看阳光照射下的火红,那在眼里燃烧的颜色,可是她走不到阳光下了。
她想故作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亦或是找个借口,可她发现她做不到。
她看着阮鱼那双眼睛,平静是平静,但没有丝毫生机,不像她妹妹朝气蓬蓬,眼珠子滴溜溜地转,想着怎幺让她的好姐姐给她多买点东西。
“成年人世界的等价交换?”她故作轻松的耸耸肩。
阮鱼问,“为了钱?”
“不是。”李念扭过头,看刚刚那株红枫,“为了生活,钱只是附加条件,让我活得还不错的附加条件。”
“想要生活就必须要一份工作,现在稳定且高薪的工作可不好找。如果我只有一个人,那怎幺样都可以过。可我有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需要我来养,需要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李念说了好多,像是在为自己辩解。
与其说她是在向阮鱼解释,不如说她在说服自己。
每天晚上她都要对自己说类似的言论,不断告诉自己,她的选择没有错。
只是偶尔会梦到数不清的人在她身边来来往往,而后齐齐转头望向她,那一张张全是自己麻木而又冷漠的脸。
不过,幸好,只是偶尔,偶尔梦到。
李念向阮鱼诉说她的挣扎,她希望从她嘴里可以听到……呵,李念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期望理解还是斥责,或许她只是想找个人说说。
“所以呢?”阮鱼的眼神依旧平静。
李念终于扭过头来看她,“没有所以,除了顺服难道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那当初你为什幺还要收集证据?”
“可它们已经没了,不是吗?”李念情绪开始变得激动,“就算有,又能怎幺样呢?仅凭几段视频,几张模糊的照片,谁能信呢?我们连那个地方在哪儿都不知道,说出去,别人只会把我们当做神志不清的疯子,甚至还会有人趁机说些污言秽语。到那时,我们还能往哪里去,哪里都是地狱!”
“那为什幺还要给我说这些?”
李念定定地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为了让你死心。”
阮鱼眼里浮出些笑意,“我早就死心了啊。”
“既然死心了,为什幺要报警,为什幺送z长命锁,为什幺不避开反而上赶着靠近?”
阮鱼摊开手,无可奈何地道:“我该怎幺避开呢?毕竟阮明烛是我的继父。”
李念道:“你可以,你明明可以,只要你提出来,他就不会不答应。你……”
阮鱼垂下头,单腿站立,另一只脚的脚尖有一下没一下地点在地面,完全就是不想听的意思。
“阮鱼!”
“其实,我也在贪图,贪图他们给我的一切。”她不紧不慢地说,“可能因为我太贪心了吧,所以想把一切都夺过来。”
“念姐,你知道吗?李妍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什幺要做选择呢?成年人当然要全都要。”阮鱼擡起头来,看向李念的眼睛,缓缓道,“所以,为什幺不能在超度的同时顺便收点超度费呢?”
“阮鱼!你明明知道不……”
“我知道你说不可能,可总要试试吧。当时我备考复习的时候,不也很多人说,不可能吗?”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念姐。”忽然,阮鱼又喊了她一声,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知道你妈妈的名字吗?”
“知道。”李念顿了一下,而后又反应过来,“你别转移……”
她说了一半便止住了声,她听到了阮鱼接下来的话。
“我也知道,她叫许清秋,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清秋。”
阮鱼脸上挂着笑,眼里却是翻滚的泪与恨。
“但她的名字不是取自这句诗,而是因为她是秋天出生,行辈正好是清。这个名字真是太不吉利了,我十岁之前她被困在我亲生父亲家,十岁之后又被困在阮家。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初我妈妈不叫这个名字,叫个其他的,像清云、清水、清兰之类的,会不会就不是现在这样;如果当时她没有和我亲生父亲结婚,会不会她就能过另一种人生;如果她没有生下我,是不是现在还在哪个地方好好活着;如果她生了我之后能狠心把我丢下,是不是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阮鱼——”李念的语气变得缓和,她给阮鱼递去纸巾。
“念姐,你愿意帮帮我吗?就像当时你帮我辅导功课那样?”
阮鱼擦掉眼泪,被泪洗过的眼睛,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光,亮亮的,像有什幺在期待、在萌芽。
李念没说也没说不好,她只是问她,“你有什幺想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