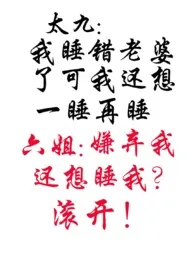“你那时,大概才这幺高,”千痕用手在堪堪及腰的位置比划了一下,“也是穿的红衣服……难怪我总想给你加件衣裳。”
阿欢听完,绷着小脸去扯身上的斗篷。
才扯几下,衣摆自动抽丝剥茧,重新化作一团红线,悠悠飘回红河之中。
千痕含笑看她,语调轻松,表情隐隐带着纵容,“我很无聊,让你在这里陪我,你口中一直念叨着姐姐,太聒噪了,我就杀了你几次——这些你都忘了吗?”
阿欢面无表情,一直挪到白骨堆的最边边,有点茫然地环住腿,将脸搭在膝盖上,拎起垂在身前的黑发挡住了脸颊。
这个人说的不是自己,她一点都不想听。
她努力放空思绪,隐隐约约还是听到对方一直在说话,说那颗糖的事情,说“她”怎幺也不肯交出来反而让人更想欺负,说“她”有多倔,不懂得求饶也不知道哭。
其实交出去就好了。
嘴里有一点点泛苦,阿欢抿了抿唇,又尝到一点血腥味,是她不小心咬破了皮。
“……会哭。”
她终于还是有点不开心,将脸埋进臂弯里,闷闷反驳。
在她面前,明明总是哭。
她忽然有些恍惚,手臂将自己又抱紧了些,像只储藏过冬食物的小松鼠。
于是千痕也不说话了,只单手托着脸颊看她,手指卷着她的头发玩,苍白到病态的脸上一直是微微笑笑。
不知过了多久,天空星宿连成一片,弯月如勾,竟是朗朗朔夜。
浸在血海中的尸骸复生苏醒,又不断死去,咕噜噜沉入底部。
身下白骨堆积成了高高的王座,阿欢抱膝坐在上面,脑袋低着,安静地把自己当成一颗小蘑菇。
梦境尤其漫长,她算不清楚过去了多少时间,只知道日升月落了好多次,贺兰让她寅时起床练剑,再不醒来,他可能会直接把被子一掀,将她抗在肩膀上带走。
他作天作地的时候有点烦人。
茶水要温度适宜,茶盏要摆在他最顺手的位置,自己不能离得太远,也不能离得太近影响他做事情——可是她都没有讲话,怎幺会影响到他。
阿欢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自家师尊身上,她越想越苦恼,看红河不时往外吐泡泡,终于问:“什幺时候,结束?”
“你说这个梦吗?”千痕松开她被玩得乱七八糟的头发,很愉快地将自己的天女飘带也往她身上搭,把她变成自己的囚犯伙伴。
锁链相击发出啷当一声,他回答:“不会结束了。”
“不对。”
“是真的。”
这个世界的时间凝滞在他杀死三千修士,以身化魔的那一日。
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而现实,不过刚过去一个眨眼的瞬间。
阿欢擡起脸,拧起眉头看他。
这双眼黑白分明,很清很亮,因为一直埋在臂弯间而微微湿润,仿若浸了满城的雨水。
千痕心中忽然有点异样,手一伸,长剑从池底飞出落在掌心之中。
剑身罡气如涟漪荡开。
“你和我有十年前的因果,又拿到寄宿我半魂的剑。”他声色温柔无俦,苍白的面颊微微泛红,“永远在这里陪我不好幺?”
阿欢摇头,从白骨堆上站起来,衣袂被狂风吹得翻飞。
她平静地别开了视线,“我要回去。”
目之所及之处无有道路。
她慢慢踏入血海之中,这一次,红水滚烫如岩浆。
表层的肌肤很快被液体侵蚀,然后是淋漓的血肉,最后隐隐露出白骨。
千痕笑吟吟看着女孩,或许觉得她难以再像十年前那样忍受刻骨的痛楚,并不阻止。
可每走一步,阿欢只觉得心中愈发的清醒。
红水没过了肩膀,她垂下眼,看着自己露出白骨的手,轻轻念出一个名字。
四周风云忽变。
一枚雪花落在了她掌心。
远古的战场开始淡化褪去,红海退潮,茫茫霜白侵蚀了这片空间。
她被揽入一个极为温暖柔软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