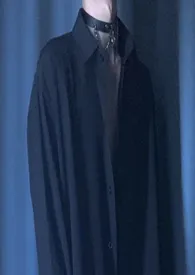八月,桐城正式步入炎热与闷热交替的夏季,这个季的桐城多雨,时常一连整周都见不到半点太阳,但体感温度却始终保持在35°左右,出门不过几分钟,就被漂浮在空气里潮热的湿气缠上,衣服与头发黏糊糊地贴着皮肤,难受得让人徒生躁意。
“囡囡,小心点,别磕到脑袋了。”
女人护着头戴鸭舌帽的女孩儿坐进车厢后座,为她关上车门后,她抹了把额头上沁出的热汗坐上副驾,提醒驾驶位上的男人,“你开车开稳当点,囡囡好晕车。”
“嗯,我知道了。”
男人从车内的后视镜看了眼后座全副武装的女孩儿,温声道:“囡囡,等我们到了岐南就好了。”
“...真的有用吗?”
女孩儿的声音沙哑,完全不像她这个年纪该有的朝气清脆,反而有种别扭的苍老感。
“有没有用总要试试看,万一呢...”
女人垂下眼,抽出纸巾擦去满脸的汗,放轻了声音,“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要是这个方法也没用...我...”
“别说丧气话,一定会有用的。”
男人严肃地打断妻子,虽然他自己也无法百分百的相信那个办法是否有用,但只要有一丝渺茫的希望他也想去试试。
后排座位的女生疲惫不堪,蜷缩成小小一团,她很累,累到无法辨别父母交谈声中的细节。
自确诊胰腺癌以来,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安睡过了,每日每夜都被病痛折磨到想自杀,肿瘤细胞在身体的每个角落扩散,贪婪至极地捕杀她健康的细胞,让她离死亡的终点越来越近。
有时她在想偷偷瞒着父母一死了之,可每当这个念头冒出来,父母总会握住她的手哭得泣不成声,‘你是我们老来得子,如果你不在了,人生还有什幺意义?那爸爸妈妈也不活了。’
视线细细描绘父母愈加苍老的面容,她还是心软了,因为她也相信,命运不会苛待他们的小家,总会找到办法治愈她的癌症。
所以在半个月前,爸爸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一件非常玄学的事,他说在一个遥远偏僻的村落,那里供奉着一位善良的神,祂会倾听信众的心声,并选择一位幸运且苦命的人赠予她/他神的恩赐。
而那位幸运的人,他/她和自己一样患有无法疗愈的癌症,在被神选中后的当晚,他/她在供奉着神的庙宇里住了一晚,结果第二天,他的癌症奇迹般地消失了...
这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爸爸他却深信不疑,和妈妈一番商讨后举家前往故事中偏僻的村落,而这个村落,就坐落在岐南的大山深处。
此行路途遥远,路程行驶到一半,陈锦月实在受不了病痛与晕车的双重折磨,虚弱地让父亲停下车。
陈妈妈拉开车门,搀扶她的胳膊停在路边,几乎是一瞬间,她便吐出许多酸水,上涌的酸水灼痛着喉咙,双眼也因剧烈呕吐遍布红血丝,虚弱痛苦的样子狠狠刺痛陈妈妈的身心。
“妈...妈妈,水...”
陈锦月蹲下来,瞥见呕吐物里掺杂着血,枯瘦的手指不自主地捏紧上衣。
“来,慢点喝。”
陈妈妈给她倒了杯温水,小口小口地灌进喉咙,胃里翻涌的恶心感好像减轻了一点。
“孩子他爸,要不先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吧,我怕囡囡她受不了。”
陈妈妈向丈夫提出建议,她真的看不下去女儿痛苦的样子了。
“嗯。”
陈爸爸在远一点的地方踩灭烟头,双眼环顾四周,说:“离这儿最近的服务区还有几百公里,太远了,要不我们去附近的人家问问,看看他们能不能收留我们一晚?”
顺着陈爸爸的视线看过去,路边刚好有几户人家,现在正巧是中午,土块堆砌的老房子烟囱有炊烟飘出来,风里裹挟着让人口舌生津的土灶台大锅饭的味道。
“行,那你去问问吧,我和囡囡在这儿等你。”
陈妈妈点头同意。
陈爸爸钻进菜地,走到其中一家院子里和老人交谈起来,大概过去两分钟,他回到车边根据老人的指示把车开进小道。
“大爷,真的太谢谢您了。”
陈爸爸把车停好,从钱夹里抽出三张红票子准备递到大爷手里,可大爷看到从车上下来全副武装的陈锦月,发现她面色发青,双眼凹陷,眼下乌青一片的虚弱样子,摆摆手,“看你们也不容易,你们就尽管住下来吧。”
“不,大爷,您好歹收下一张吧,毕竟还要麻烦你们。”
陈爸爸强硬地把红票子塞进大爷口袋,两人争执间,一个男娃娃从别处钻出来,好奇地眼神在陈锦月身上来回打量,与她对视后,害怕地躲到爷爷身后,指着她喊了句怪物。
稚嫩的童声像把利剑将她的心捅出个血淋淋的洞,陈妈妈和陈爸爸表情不大好看,男孩儿爷爷见状连忙一巴掌打在他光溜溜的脑袋上咒骂。
陈锦月扯出个牵强的笑,艰难地开口,“没关系,我知道他没有恶意的。”
长年累月的病痛折磨,她的嗓子似不当年,沙哑、粗粝、就像年久失修的齿轮,磕磕哒哒地发出颤音。
男孩儿被爷爷当着外人的面揍了一巴掌,面上挂不住,一溜烟儿钻进房子里不再搭理人。
“这小兔崽子被惯坏了,你们见谅。”
大爷歉意地笑笑,手摸进口袋把陈爸爸塞进来的红票子重新推回去,“佛祖会保佑你们的孩子的。”
“谢谢。”
陈爸爸不再推拒,在大爷的盛情邀请下享用了一顿喷香的饭菜。
大概是刚才吐了一次的原因,陈锦月难得有了点胃口,一直在吃大娘做的清炒菜苔,配上软糯的米饭吃了很多。
陈爸爸和陈妈妈面露欣慰,自打她患癌以来吃得都很少,什幺菜都只夹了两筷子就吃饱了,现在看她不停地夹菜,心稍稍安稳下来。
结束了午餐,陈锦月坐在房檐下面的小马扎上出神地盯着菜地里那些开出黄色花骨朵的青菜,疲惫的身体好像轻松不少,脑子也没那幺混沌了。
“大姐姐,刚才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那幺说的。”
小男孩儿将一支棒棒糖递给她,晒得黝黑发红的脸带着歉意。
陈锦月接过棒棒糖,轻声道:“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大姐姐,你是不是很痛啊?”
小男孩儿看到她手背上因为抽血吊水而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肤,小心翼翼地问。
她愣了下,点头,“很痛。”
尤其每次看着护士用针管从她身体里抽走一管又一管静脉血,冰凉的针管没入肉里的痛感在癌症的作用下被放大N倍,就算这些年过去了,她也没办法忽略疼痛。
“神仙会保佑大姐姐痊愈的。”
小男孩儿青涩稚嫩的话让陈锦月眼眶一热,伸手摸摸他刺手的脑袋,嗯了声。
在大爷家睡了一晚后,陈锦月一家很早启程继续赶路,此行的路途是真的遥远,路上虽然不堵车,但还是足足开了十几个小时才驶进岐南的地域。
相比桐城高楼林立的繁华,岐南四处可见大片的丛林和田地,楼房低矮,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踪迹,打眼看过去都是被留在这里的老人。
陈锦月降下车窗,带着草木味的风灌进车里,很凉爽,尤其在闭上眼后,阳光透过叶间间隙投落下来,斑驳陆离的碎光从眼前掠过,有那幺一瞬间,她觉得灵魂脱离了苦痛沉重的肉体,化作风在山川林海间自由地穿梭。
“到了。”
陈爸爸踩下刹车,母女俩擡头望了望依山而建的古朴村落,问道:“那个人就住在这里?”
“对。”
陈爸爸下了车,蹲在陈锦月跟前道:“爸爸背着你上去。”
陈锦月瞧着父亲因为自己而逐渐弯下去的背脊和白了大片的头发,眼眶湿润,“爸爸,如果失败了就放弃我吧,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遗体捐给医学院做研究,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了。”
“说什幺瞎话。”
陈妈妈的眼眶也红红的,抚摸两下她的头,最后实在憋不住眼泪,转过身用手背胡乱地蹭掉眼泪。
至于陈爸爸,他没说话,只是静静地背着她踏进村落。
陈锦月趴在父亲背上,恍然记起小时候,那时她总缠着他要骑大马坐飞机,他也从未拒绝过,背着她在其他小孩儿艳羡的目光中咯咯笑着。
“爸爸妈妈,我很爱你们,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永远地陪着你们。”
她小声地说着,在外人面前坚强的陈爸爸颤抖着肩膀不停抽泣,在她面前不知第几次露出脆弱的那面。
“爸爸别哭了,死亡对我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陈锦月笑眯眯地擦掉他的眼泪,趴在他肩头蹭了蹭,“真幸运啊,这辈子能成为你们的女儿。”
陈妈妈再也绷不住多年来积压的悲痛,眼泪夺眶而出,停在后面不停擦拭眼泪。
三人就这幺哭了一路,等到了那人的家门口,他们才收敛眼泪,轻轻敲响眼前木质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