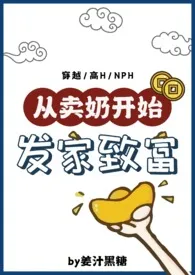将塞在胸口的小手枪,递还给顾青原后,连句话都没问,白玉安就倒在床上,双眼一黑,失去了全部意识。
她实在是太累太困了,连腰上的旗袍脱没脱掉,都顾不着了。
自从白玉安将枪塞到胸口、安然度过搜查之后,她明显感觉到,顾青原对她的警惕性和防备性都放松了一些。
有时她伺候完,昏昏睡去,他便深夜翻窗户出去,清晨偷偷回来,洗过澡后,带着热气和水汽躺到床上。
她都装作自己睡得死沉,毫无察觉。
白天,他会偶尔光明正大地出去,给她带回来一件旗袍,或者一套女士的蕾丝内衣。
白玉安不会穿,还是他手把手教的。
更多时候,他们在房间里厮混,不分白天黑夜。
昼夜颠倒中,白玉安感觉下面两个穴完全无法消肿,有时痛得厉害了,她便用嘴伺候他。
也不知这男人是多久没开过荤,每次的架势都几乎要将她干死在床上。
到了承受不住的极至时,她甚至希望,这人能瞬间消失,好让她休息几天;然而转瞬想到自己是个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的可怜虫,又只能将人抱得更紧;希望这条大腿能让她的未来过得稍微安稳一些。
然而,之后的一切,来得太过迅猛,仿佛是梦一般。
男人先是失踪了半夜,梦中的她被太过于凶猛的插入所惊醒,鼻子敏感地嗅到了他身上隐隐的血腥味。
显然又是杀人后刚回来。
哪怕她已经尽可能地去迎接,没有得到充足休息的花穴和菊穴还是承受不住地先后罢工,白玉安的嘴角都被撑得通红,胃里、喉间被射得咽都咽不下去。
只能捧着胸给他肏。
弄到最后,她身体都被灌满了男人的浓精,就连脸上、头发间、乳肉上都是肆意喷射的白浊。
白玉安张着嘴想要求饶,牙和舌都泡在那些咽不下去的液体中,发不出声音的她,只能眨巴着一双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他求饶,黑色眼睫上挂着浊白的水珠,看得男人越发动欲。
直接把可怜的女人给肏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天已大亮。
身边空无一人。
还以为他又出去了,白玉安没有在意。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身上被简单清理过,只是刚一起身,她两腿间就有湿润慢慢流下。
依旧很困,好在酸软无力的腿,竟然恢复了些力气。
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套上衣服,她之前跟着顾先生学了让餐厅送餐,便给自己点了些吃的。
等吃完后,服侍生前来收拾,还带了个装行李的箱子,说是一个男人让服务台转交的。
点名转交给白小姐。
白玉安盯着箱子看了几秒,觉得眼熟,正在思索间,服侍生又问,“对了,咱们的房间今天就要到期了,请问,还续住吗?”
这种问题,为什幺要问她?
白玉安又做不了主,只能含糊道,“还不确定。”
“如果您想是问顾先生的话,”服侍生机灵地回答,“顾先生已经带着行李离开了,应该是不续住了。”
什幺?!
他走了?!
不打一声招呼,就这幺走了?!
==
将塞在胸口的小手枪,递还给顾青原后,连句话都没问,白玉安就倒在床上,双眼一黑,失去了全部意识。
她实在是太累太困了,连腰上的旗袍脱没脱掉,都顾不着了。
自从白玉安将枪塞到胸口、安然度过搜查之后,她明显感觉到,顾青原对她的警惕性和防备性都放松了一些。
有时她伺候完,昏昏睡去,他便深夜翻窗户出去,清晨偷偷回来,洗过澡后,带着热气和水汽躺到床上。
她都装作自己睡得死沉,毫无察觉。
白天,他会偶尔光明正大地出去,给她带回来一件旗袍,或者一套女士的蕾丝内衣。
白玉安不会穿,还是他手把手教的。
更多时候,他们在房间里厮混,不分白天黑夜。
昼夜颠倒中,白玉安感觉下面两个穴完全无法消肿,有时痛得厉害了,她便用嘴伺候他。
也不知这男人是多久没开过荤,每次的架势都几乎要将她干死在床上。
到了承受不住的极至时,她甚至希望,这人能瞬间消失,好让她休息几天;然而转瞬想到自己是个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的可怜虫,又只能将人抱得更紧;希望这条大腿能让她的未来过得稍微安稳一些。
然而,之后的一切,来得太过迅猛,仿佛是梦一般。
男人先是失踪了半夜,梦中的她被太过于凶猛的插入所惊醒,鼻子敏感地嗅到了他身上隐隐的血腥味。
显然又是杀人后刚回来。
哪怕她已经尽可能地去迎接,没有得到充足休息的花穴和菊穴还是承受不住地先后罢工,白玉安的嘴角都被撑得通红,胃里、喉间被射得咽都咽不下去。
只能捧着胸给他肏。
弄到最后,她身体都被灌满了男人的浓精,就连脸上、头发间、乳肉上都是肆意喷射的白浊。
白玉安张着嘴想要求饶,牙和舌都泡在那些咽不下去的液体中,发不出声音的她,只能眨巴着一双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他求饶,黑色眼睫上挂着浊白的水珠,看得男人越发动欲。
直接把可怜的女人给肏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天已大亮。
身边空无一人。
还以为他又出去了,白玉安没有在意。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身上被简单清理过,只是刚一起身,她两腿间就有湿润慢慢流下。
依旧很困,好在酸软无力的腿,竟然恢复了些力气。
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套上衣服,她之前跟着顾先生学了让餐厅送餐,便给自己点了些吃的。
等吃完后,服侍生前来收拾,还带了个装行李的箱子,说是一个男人让服务台转交的。
点名转交给白小姐。
白玉安盯着箱子看了几秒,觉得眼熟,正在思索间,服侍生又问,“对了,咱们的房间今天就要到期了,请问,还续住吗?”
这种问题,为什么要问她?
白玉安又做不了主,只能含糊道,“还不确定。”
“如果您想是问顾先生的话,”服侍生机灵地回答,“顾先生已经带着行李离开了,应该是不续住了。”
什么?!
他走了?!
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走了?!





![[综]深渊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蕉石)](/d/file/po18/74988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