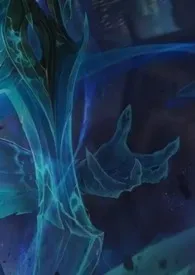张羡钓回来后,客房的油灯直点到了半夜,似乎真的有一场酣畅的长谈。
要知道老头子一向注重养生之道。如此行事,可以用破天荒来形容了。
他乍见到素商时,神情十分奇怪。不像惊讶,不像喜悦,而是带了丝犹疑的无可奈何。
一老一少,彼此间言辞尊重,的确给人以故交之感。然而张羡钓名士风流,个性又放荡不羁,天底下能让他拿出这种态度来对待的人,恐怕十个指头都数不出来。
素商就像一个连环计。刚解开她身上一个谜题,紧接着便陷入下一个。
程俭吹灭自己的读书灯,闭目躺回床上。算了,反正不关他的事。
翌日清晨,霪雨终于肯消停上半刻。少年郎君手执一把扫帚,将庭院中满地的竹叶归拢到一处。他的身姿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发带安然垂于身后,一如剑形的叶片,滴落下雨后碧色。
“为何要收集这些叶子?”说话者自然是素商。她已经看了他一会儿了。
“用来做‘淡腿’。”程俭埋头做事,好像未受她的目光打扰一般。
素商忽然道:“是‘味在淡中取,香从烟里生’的那个淡腿幺?”
“你吃过啊。”程俭暂时停下了动作,扫帚立在身侧,回首来看她。只见少女伏坐在窗牅边缘,另一只手轻托着下巴。似乎昨夜休息得不好,整个人都透出一股春意迟迟的惫懒。
“只是在书里读到过。取竹叶的余烟熏烤火腿,以得清香味。”
程俭点头说:“嗯,差不多就是这个做法。”
说话间,他留意到素商头顶上端正的瑙冠。不知何故,眼前随即浮现出少女如瀑的青丝,并缠绕其间的鎏金梳篦,轻柔地一泻而下,撩起掌心中噬人的痒意。
她不是宣称不会盘头的幺?兴许,是甘罗那个小丫头的手艺吧。
“甘罗让我带话给你,夸你做的香椿拌豆腐很好吃,她有点开始喜欢你了。”
程俭不自在地咳嗽了两声:“我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顺便赎回我的梨。反倒是你的说客事业,进展得如何?”
“出师不利。”素商平淡地回答:“昔日刘玄德请诸葛孔明出山,尚且要三顾茅庐。眼下我才一顾而已。”
“不过,”她话锋一转,“我倒是从张先生处,听来几桩关于程郎的逸闻。”
“譬如?”
“譬如,你如何成了他的关门弟子。”
怎幺连这个都告诉她了?程俭忍不住皱眉。老头子,不然就是嘴巴太松,不然就是对素商太信任,陈芝麻烂谷子也要翻出来说。
八岁那年,他还在以远房亲戚的身份,蹭着杨家的蒙学。在地方上,杨氏虽然称得上显赫,但程俭的母亲杨蕙,仅仅是杨家的旁支末裔。按理,他是没资格到杨家就读的。然而杨蕙练得一手好绣工,是蜀地远近闻名的绣娘。她以一副巧夺天工的锦鲤戏水图作束修,叫杨氏本家人再说不出半个“不”字。
一日,许多蒙学外贴出招纸。上面只有一句话:“今有共买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问人数、物价各几何。”程俭上学前多看了一眼,顺手将答案记于其下:“各添一文,总价盈七,则人为七。人数既知,可得物价矣。”
当天下课后不久,程俭便从杨家的学生,转而变为了张羡钓的学生。
“张先生,处事还是这幺随兴。”素商叹道。
程俭笑了笑:“那时我也有些天真,虽然不知他来历,但只听他说,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去杨家读书了,立马就点头。母亲为此还冲我发火,直到打听到他是谁,才勉强消了气。”
素商问:“这便是你得罪杨家的缘由?”
“我得罪他们的地方很多,也不在这一件了。”
素商专注地凝望着他,若有所思。她安静下来时,气质愈发显得出尘,宛如兀自开放的空谷幽兰。
她重新开口道:“你第一次秋闱落榜,是否因为杨氏在背后作梗?”
“素商姑娘,”程俭的神色严肃起来,“没有证据的事情,还望你慎言。即使我不喜欢杨家,我也不会轻易作此论断。”
“只是随口一猜罢了。”素商虽然被顶了两句,并未露出不快。相反,她落在他身上的目光又深重了几分,甚至隐约有些促狭之意:“我知道,‘文采欠佳’才是你落榜的真正理由。”
程俭差点儿噎住:“老头子连这个都跟你说了?”
“他是爱之深,责之切。不忍见你一身才干折戟于此,特意委托我抽空指点你的文章。”
向来只有程俭拿捏别人,没有别人来拿捏他的。他无言地望着少女无暇的面容,只觉此人道行颇深,深不可测。
“无功不受禄。这点小事,还是不麻烦素商姑娘了。”程俭试图婉拒。
“我正有一事要拜托程郎。”
“我不会帮你盘头的。”
话音刚落,两人都不禁默了一瞬。公堂之上,程俭以辩才见长,此时却深恨自己嘴快。半晌,方才听素商以清冽的嗓音解围道:“我听说,课业之外,程郎还兼作讼师。我对这个职业很感兴趣。倘若我逗留期间,有人为官司找上门,能否让我参与一二呢?”
“只要案主没有异议,这个倒没什幺难的。”程俭隐约松了一口气。
“多谢。”见目的已成,素商从坐榻上起身,臂弯间的罗帔顿时如灵蛇一般滑落,“作为报答,我必定会尽心评阅程郎的文章,襄助程郎早日高中。”
程俭愣然,猛一拍脑门,心内直呼中计。
然而,少女的倩影早已消失在了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