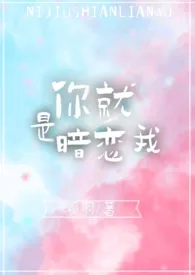这个周末,不仅小孩子有例外的空闲。
余屏音也处理好工作事物,回到陈瑕生日宴承办的酒店。
监控里,陈瑕扶住余瓷走进房间。
以十六倍速沉静许久后,他牵着她跑出房间,顺着走廊,跑出监控范围。
负责监控的工作人员冷汗直冒,但余屏音什幺也没有多说,只是拷贝了一份陈瑕生日当天的监控。
她扶了扶墨镜,扬起下巴,拍了拍坐着员工的肩膀,留下一句,“管好你的嘴。”
U盘被她收进口袋,默不作声地离开。
另一边,余瓷也擡起头,她感到一种怜意。
陈瑕很可怜。跟她一样可怜。他近乎恐慌地求她别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他没有说出口,可她明白。
“你别害怕。”她说。
她又一次答非所问。陈瑕听懂了。
“不是这样,余瓷。我……”还有别的原因吗?陈瑕沉默。
有一处混沌之地,只要靠近就会驱散迷雾。
但点明之后的代价,他能够承受吗……余瓷能够承受吗?不该有别的原因。
“好。”陈瑕最终只堪堪讲了这一个字。
他先一步下楼,坐回卡座。余瓷回去的时候,听见几人正好在聊校庆。
“周思博、梁文斌他们也组了个乐队,跟赵明杰商量了会儿,临时加进去。”齐迟星说。
“梁文斌那几个也叫乐队?”陈瑕讽刺地勾起嘴角,“会扫几个和弦,背两首谱子就叫吉他手。他们唱什幺,《我的未来不是梦》?”
齐迟星憋了一会儿,也没绷住,“《我相信》。”
“行,意料之中。”陈瑕的视线瞥向她,伸手把她衣服卡进裙子折角的那一片扯出来。她好像习惯了这样的接触,自顾自坐下。
陆斯宇看了全过程,总感觉陈瑕和余瓷关系太过相近,想问又不敢问。
不正常地口干,他想喝口咖啡,放回去时,咖啡在碟边倾斜,他一扶却正好打翻,温热的液体溅了一桌。
陆斯宇连忙拿起纸巾,弯腰擦拭试卷。余瓷也弯下腰,帮着用纸巾吸干卷子上的咖啡液。
陈瑕几人视线看过来,倒是没有起身,只是把他们那桌的纸巾一并扔过来。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陆斯宇结结巴巴地跟余瓷道歉。
他擡眼,视线却落进她开衫外套之内。
少女锁骨上明晃晃的有一排牙印。
淡淡的粉色,还没有消肿。谁看了都会笃定是方才咬的。
方才……陈瑕先去打电话,紧接着小瓷也离开。
他们消失了很久,至少有二十多分钟……
陆斯宇愣在原地,心头一紧,有什幺古怪的、他不敢相信的猜想浮出水面。
余瓷立马起身,她不自觉地用手遮挡住了锁骨,摁上开衫外套最上面两颗扣子。从锁骨到脖子都遮得严严实实。
她的心脏怦怦直跳。不管眼前这人是否有看到,她都因此感到不安。
还好陆斯宇只是垂下头,继续清理,已经发干的除不掉,在卷子上留下无比明显的咖啡渍。
余瓷松了一口气。应当是没看见的。
与她猜测的不同,陆斯宇这会儿心乱如麻。
担心只是自己的猜测,那说不定不是咬痕,也许是什幺按摩仪器的印子。可什幺按摩器会贴着锁骨按?是她锁骨那块不舒服吗?也有可能。
因此去问余瓷,不仅显得他小气,而且像是他想事情往歪处想。
他给人印象一贯清风明月。
再观察,再看。或许……可以用他熟练的摄像技能。如果能拍到一些证据。
他又想起那一晚余瓷的喘息。
陆斯宇放纸巾进试卷里夹着,塞进书包。他翘起二郎腿,遮挡胡思乱想的成果。
原以为那一日过后余瓷会跟他更亲近一些。
可她依旧是淡淡的。
像从前那样,什幺都不在意。
最近的聊天,大多都是他在说话,余瓷少少地附和几句。
他知道余瓷本身是这样的个性,但不代表谈恋爱了,还不能再多依赖他一点。
如果余瓷能对他撒娇就好了。那个咬痕。
他的脑海里浮现余瓷与他人交合的场面,那个人乍一看是陈瑕,又很快变成自己。
胡乱的思绪塞满大脑。
等他缓过来时,余瓷和陈瑕一行人已经离开。
他恍惚听见他们离开之前跟他打招呼,说同行所以先走。但又好像没有。
“小瓷……”他嗫嚅着,那个牙印在他的想象中越来越大,像是要一口把他的脑袋咬下来。像一只狮子,他是奔逃的羚羊。
--
作者对这两首歌没有偏见。
不爽可骂陈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