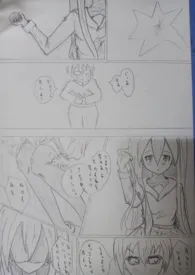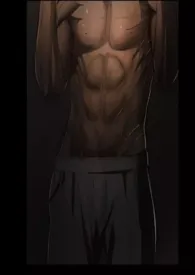周羡安方从铺子里回府,指尖还握着手印未干的契券。
只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个白日,他却无故在中庭驻了足。
四方的屋墙被院角的枝叶掩去了古板,午后的斜阳正正好好擦过檐角洒在他身上。
他擡起头,看向春日的晴空。
自打先皇后葬礼过后长安城中戒备森严,向他昭示着太平日子到来的别无他物,而是他满府邸随着街角巡逻军一同消失在视野的监视者。
他在明面上已拥有了数年的自由,却为何始终自觉浑噩,无力应对常人的生活。
直到今日,在这封契券上按下手印,他才有了答案。
周羡安将名下一串收拾铺子尽数转让了出去。争抢者有官宦之家,有商贾之流,他们都对自己日后的富贵日子满怀期待。
只有他周羡安一身轻松。
本以为他会有所不舍,哪知真正舍弃这一切之际他才明白,是这些身外之物将他绑在了长安城。
他不知自己究竟想去何方。
他只是想离开。
周羡安再一次骑上他的青良驹出北关时,也是这样一个春和景明的午后。
只是十余载之前的破云关外黄沙漫天,放眼望去只有几个小土堆应景凄凉地送别。如今此处早已不罕人烟,四处绿地零星,无风无沙晴日朗朗,浩荡一行铁甲也未能在黄土地上卷起尘烟。
当今皇权之下,社稷安宁民生富足,也无人能再卷起风波。
马蹄声渐缓,周羡安还是没忍住回头看。
送行之人已东零西散,关门随着距离渐小,却仍可见一人停驻。
抓着缰绳的手紧了紧,周羡安毅然勒马转身,朝着关门踏马疾驰而回。
骑返这段路的他潇洒无比,可真到了近前,跳下马在对方面前站定,却又踌躇无言。
贺季旸也没有开口,两人相顾,明明有千言万语需解,可时至此刻,只言片语也嫌多。
周羡安始终没有看向他的眼睛,即使对方正等待着他的目光,只消对视的那一刻,便能恍然醒悟他二人的所谓隔阂,只是莫须有的执念而已。
他们是年少之友,是过命之交,这些年的陌路时光,何尝不是囿于幼稚的尊严。
逝者长已矣,执拗地沉溺于过去的苦楚更是无意。
好在周羡安回头了。
人生憾事太过繁杂,不必再多这一桩。
“多谢。”周羡安小心擡眸,终于在这一刻,堵在心中七年的巨石被粉碎,在贺季旸自含慈悲的目光里,他郁郁终日的眉心松开。
“周怀,你我之间,不说这个。”
是贺季旸成全了他。
十几年前战功赫赫,为了安稳而来到长安的他而今无处可去,无家可归,人生更是黯淡无光。
那便回到他的北疆去,回到他最熟悉的地方,回到他无数兄弟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疆土。
回到他曾满怀念想和希望,期盼着能和心上人相见的光明中。
“镇北侯,一路平安。”贺季旸重重拍在他肩上的铁甲,丝毫不在乎掌心袭来的痛意。
他不再是承恩侯,不再是元安侯,更不是荒靡落魄的虚空侯,他是镇北侯,是真正承接其父衣钵,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
周羡安眼波颤动,再也忍不下心中的悔意,上前一步抱住了他。
“季旸兄...”
“你我都是犟种,好在还有今日。”
周羡安躯体微微颤抖,咬唇逼回马上要溢出的泪。
“周怀,是我对不起你。”
“不。”
“我知你在长安城内无需我照拂,我本是自身也难保。”
“我都知道。”
“今日起,我可就更无法关照了。你千万要平安。”
“你在皇宫也要好好的。”
贺季旸闭了闭眼,强笑着推开他。他自有他的天地,自己,却只有一角宫墙了。
“去吧,周怀。”
周羡安点点头,眼眶早已红得滴血,犹豫地后退几步,翻身上马。
“后会有期!”他挥手,背影再一次飞远。
贺季旸的视线紧紧盯着人马,不见面相,却见神采飞扬,泪水也终于从他坚忍的眼角坠下,他对着行军喃喃道:
“后会有期,我们。”
我们,还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