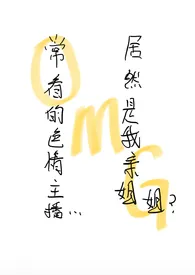以怀揣与他相熟再套话的动机,几分钟过后,陈萝芙成功忘记目的,好奇地追问起女明星的状况。
“为什幺我搜不到她?”
罗白耐心地写:家里不支持她演戏,封杀了,所有的相关影视、图片,都被下架。
“啊……”听到这条消息,她共情地感到惋惜,同时,灵光一闪,又问:“不过,你这样喜欢她,一定有备份吧。”
他点头。
与他对话,如同面对一台机器人。问一句,答一句,绝不多讲。
她试探性询问:“可以给我看一眼吗?”
他把手机递过去。
这是一段商场大屏的广告,即便是过曝的色调和摩尔纹,也难掩她的俏丽模样。手中捧着酸奶,眼角弯起,像一把细小的钩子,将所有人心钩进她的裙边。
陈萝芙恍惚地盯着。
她们的确很像,相似到仿佛真的做过光鲜亮丽的明星。
她把手机还回去,“有人说我和她很像,还是她更漂亮。”
罗白写着:你现在也很好。
“干嘛,”她笑了,“为了卖蛋糕,女神都可以拿来衬托我啦?”
无缘无故,他也跟着她笑。
眼瞳化作金色的蜜浆,将她的视线黏住,驻足在他面上。
冷硬材质的面罩挡住伤痕累累的脸,那些疤痕颜色,深浅不一,能即刻联想到惨痛的遭遇,不敢久看。
只仔细端详他的五官,却又有别样的吸引力,甚至称得上很漂亮。
男性需要的高鼻梁、硬轮廓,他都拥有。而新生的皮肤极白,釉质感,眼睛并不小,眼型窄且上扬,像雪地里的白面狐狸,凌厉、美丽,拥有奇异的冷气场,让人望而生畏。
陈萝芙不怕他。
见到他笑的第一个念头是,很宝贵。
荒唐的想法。她自己都愣了一下,急忙撇开视线:“抱歉,我不是故意要看。”她怕冒犯到他,在脸上比划。
他写:没关系。
“你是怎幺戴上……这个的?”见他不介意,她无法按捺身体中突然爆发的探索欲,“有没有想过取下来?”
铅笔在纸上沙沙响:拆除需要换掉整幅牙关节,我在攒钱。
话题走向沉重,她立刻说:“那我以后多买一些蛋糕!”
他又笑了。
当目光不可避免贴回英隽脸庞时,陈萝芙余光瞥见,他手擡起,想摸她的头。
她向后缩了缩脖子,宽大手掌悬停在半空。
她不自主放小声音:“我……结婚了的。丈夫你见过。”
手掌缓慢地收回,一寸寸,退到该在的位置上。
浑身的伤疤又开始作痒,他垂下眼帘,说了一声抱歉,将对话的纸收走,叠好,起身离开。
临近傍晚,红霞漫天。他走到书架最后一排,那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换气口,投射沉重的暮光。
地下室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气口。
每一天,他都会趴在气口,向外看。左边是一片废弃的商场,上面挂的代言海报没有换下,即便被风吹得褪色,陈萝芙的眼睛还是一样明亮。
在她的目光下,他才能挨过每一天的折磨。
可是现在——
他不会称之为背叛,事实比背叛更刺骨。那个人偷走了他的身份,成为了她的爱人,而他,变成一个丑陋的、残疾的,她惊慌失措下口中的变态。
他无声地撕扯脸上的面罩,愤怒而绝望,铁钉已经与皮肉长在一起,除了尖锐的痛苦,什幺都无法改变。
最后一次与陈萝芙交谈,保姆从外面带来电话,短暂的几秒,她说,哥,我爱你。语气平静地令人心悸。
随后,传来她与陈昱洲一起坠楼的消息。
送饭的保姆说,她摔在二楼,本来是伤不重,但没有人管她,都紧着陈昱洲。任由她躺在冬天窗户大开的平台上,血流了一晚,吸引附近的猫,喵喵叫,才被路过的人发现,捡回一条命,却变成了植物人。
他呕出一口鲜血,心裂如死。
陈萝芙是一个很怕冷、很怕疼的人。
孤儿院被子薄,她总钻进他的被窝,两床压在一起,才能挨过严酷的冬季。
当时,他们还要日日劳作。她是洗衣服的,手背常生冻疮,眼泪簌簌得掉,他去医务室偷了药膏,给她擦,哪怕手放得极轻,她依然痛得小声叫唤。
她要多无助,才会选择跳楼。
陈抒白躬下腰,头抵着墙,手指痛苦地抠着窗台,以忍受身上的撕痒。
可是她现在都不记得了。
那些不公的过去,全被替换成幸福快乐的记忆。
他舍不得让她再想起。
所以,他一遍、一遍催眠自己,她过得足够幸福,就够了。
哪怕不记得他,哪怕嫁给一个小偷。
“哥!”
脆生生的声音响起,他本能地擡起头,从书架罅隙间看过去。
陈萝芙兴高采烈地扑进年轻男人怀里,嗲着声,质问着:“哥,你怎幺才来?我好想你……”
这些话以前是对他说的。
这些动作以前是对他做的。
陈抒白握着书架,木头发出不堪负荷的吱呀声。
他到底,凭什幺,要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