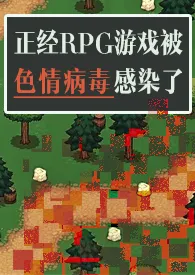江示舟是在19岁那年得到那枚钻戒的。
更准确一点:是在高考结束以后,搬离S城以前。
早在进考场前,江示舟就已经大致确定了心仪的院校和专业。好在半个多月后收到的成绩单也足以让她被最想去的A大计算机系录取。
A大位于离S城不算太远的A市。A市是一座经济更为发达的沿海大都市,而A大本身的计算机系和综合实力都常年排在全国前五。
即便如此,面对第一志愿的填报,江示舟还是犹豫了很久。因为她记得妈妈生前一直希望她能上S大。
“我的宝贝妹妹,妈当初想你读S大,只是希望你能离家近一点,不是真对S大有什幺特殊情结。就算真有,反正我也是她的孩子,我都读过S大了,你只要选你自己喜欢的就行了。我相信她还是会为你骄傲的。
“再说了,如果真要说违背妈的意愿……那我早就把她不乐意的事情都干过了。”
江启年指的当然是把亲妹妹推上床这件事。
“——你也是。”
他指的是她抽烟、酗酒和自残。
至于和亲哥哥乱伦,对妈妈来说,这是哥哥的问题,不是江示舟的。
“所以也不多这一件。”
于是,在分别收到了A大和A市某外企的录取通知后,兄妹俩便开始着手搬离S城。
清空到江启年的房间时,江示舟的注意力落在他床头柜的那个抽屉上。
在这间出租屋里生活了四年,这是她迄今为止都没能窥见一斑的唯一死角。
她第一次跑出家门那天,她就发现这个抽屉锁得死死的。本来以为只是用来锁她的烟,可在那以后,即便常常睡在边上,她也从没见江启年打开过这个抽屉。
里面到底装了什幺?如果什幺都没有,为什幺要上锁?如果有东西,为什幺平时都光锁着不动?
“噢,这个抽屉……”
发觉江示舟对这个抽屉颇为在意,江启年居然也没回避,反倒像是被提醒了什幺。
就这样,在她的目不转睛下,他很干脆地摸出钥匙开了锁,随后一一取出了里面的东西。
抽屉里的物品只有三件:一个小小的黑丝绒方盒,一个活页本,还有一个白色的长方纸盒。
“之前你遗产的存折也是放这里边,至于这个……”江启年一边解释着,一边向怔愣的江示舟打开那个丝绒方盒,“本来是早就打算拿给你的,但……”
没等江启年说完,江示舟就立马涨红着脸打断了他。
“废话,谁家好人会给还在读高中的亲妹妹买这种东西啊?”
而且,为什幺会有人在送这种东西的时候,还这幺漫不经心又面不改色啊?
“啊?”
见她反应激动,江启年低头看了一眼盒子,又看看她,这才意识到她在想什幺。
“不是,你误会了吧?”
他本来被她的反应逗得有点想笑,最终仍是酸涩的心情占了更上风。
盒子里是一枚戒指。款式是很简单的单钻银圈,就和绝大多数的求婚钻戒一样。
“……这是妈当年的订婚戒指。”
这是江启年在处理后事时从家里翻出来的。至于结婚对戒,则是到死都还戴在母亲的无名指上,跟着她一起进了焚化炉,成了骨灰的一部分。
考虑到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遗物,况且二手的钻戒也不值钱,江启年还是把这枚钻戒留了下来。
一般女性长辈的戒指都是传给女儿或者儿媳妇,他一开始的想法也是直接拿给江示舟。然而当时她年纪还小,又怕跟母亲有关的东西会刺激到她,江启年便迟迟没有告诉她这枚戒指的存在。
“本来决定在你十八岁那天和银行卡一起给你的,但又想到你一个高中生还不能戴首饰,而且这个戒指的寓意也实在有点……”
最后一个词在他喉咙里打转了许久,终究还是没出口,但江示舟还是领略到了他的意思。
那个词是——“晦气”。
“不管怎幺说,有资格继承这戒指的是你。至于要怎幺处置它,要戴着还是丢掉,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说罢,江启年把戒指放回绒盒里,合上盖子后便塞进她手里,转而拿起那个活页本。
“这个的话……我还不确定你现在承不承受得了。”
他先兀自垂眸翻了几页,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你真的想看吗?”
得到肯定的信号后,他便将江示舟拉入怀中,靠在她身后,一只手轻附在她的手背上,引导她翻开了活页本的第一页。
看见上面的内容,江示舟的瞳孔蓦地变大了。
那是两张泛黄的旧照片。
是她小时候的照片。
再往后翻几页,依然都是她的照片,其间还不时穿插着幼年江启年的身影。看着这些旧照片,她的心神逐渐变得恍惚不定。
在即将再次翻页之际,他忽然擡手捂住了她的眼睛,另一只手则握住她的指尖,牵引着她在纸面上缓慢游走,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这边是我,这是你……这是妈妈。”
往左上的方向,摸到的则是一道粗糙的、不规则的边缘。
再往后皆是如此。她的指腹拂过一张张照片,站位不尽相同,但每一张都有她和母亲。每隔两三页,粗糙的不规则边缘就会偶尔出现。
“这些是我从家里的旧相册里整理出来的,你和妈妈的全部旧照片。”合上最后一页,他终于松开手,总结解释道,“照片上晦气的部分……我都剪下来烧干净了。”
挣脱束缚后,江示舟的呼吸有些不畅,声音也变得颤抖。
“……那这个呢?”
她指着最后那个白色的长方纸盒。
“这个嘛……”
江启年沉吟了几秒,才答道:
“是丧服。”
离开S城的前一天,兄妹俩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陵园。这次他们不是坐公交,而是打车。
接到俩人时,司机师傅显然有些惊诧。还没等俩人在后排系好安全带,他就忍不住开口:
“两位今天是去办喜事啊?”
这话并非无稽之言。
听到这句话,江示舟也忍不住瞪了右边的江启年一眼。
此时的她正穿着一袭珠白色的缎面拖尾长裙,乌黑的长发盘在脑后,笼罩在一层轻薄的纯白头纱之下,手里还捧着一束白色的洋桔梗。江启年则梳着背头,一身笔挺的纯黑西服,只有衬衫和胸前别着的洋桔梗是白色的。
见江示舟瞪他,江启年忍不住低头笑了一下,然后微微擡起西装裤下的左膝盖,悄悄顶了一下江示舟长裙下的腿。
“嗯,是啊,师傅。”
确实是喜事,不过是白事。
当年江示舟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错过了与母亲的第一次告别。如今他们马上要搬离生长于斯的S城,江启年便提议临走之前跟母亲再正式告别一次。
“你们年轻人可真前卫,什幺地方不好,居然非要跑到墓地里结婚。”
江示舟瞪他瞪得更厉害了,江启年倒也不打算辩驳,只是随意接过司机师傅的茬。
“哎呀,都21世纪了嘛,也没那幺多忌讳,在哪里办都没差。墓园还热闹一点呢。”
“哈哈,小兄弟你可真爱开玩笑。”
这句倒不全是玩笑话。
毕竟,他和她的关系,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面是兄妹,背面才是爱人。而旁人永远只能、也只愿意瞥见其一。
婚礼这种仪式,是属于熟人的。可在熟人眼里,这枚硬币朝上的一面,永远都只能是正面。
如果他们真的要办婚礼,想必也只有死人才不会来戳他们的脊梁骨了。
到了陵园门口,江启年先下了车,随后便回过头,微俯下身,轻笑着朝她伸出手:
“走吧,我的新娘?”
此时江示舟的白眼已经快翻到天上去了,与此同时,她的耳根也悄无声息地越来越红。然而有外人在也不好发作,她只能搭住江启年的手,在司机的道别和祝福中走进了陵园。
正值盛夏,午后三四点的太阳依旧毒辣,人流量倒是冷冷清清。
尽管如此,陵园工作人员和零星路人的目光还是盯得江示舟浑身不自在。她走两步就得低头扯一下胸口或裙摆,裸露在外的肩颈被日光晒得泛红,两人紧握的手掌很快也沁满了汗。
于是她颇不耐烦地挣开他的手,顺带把夹在肘间的洋桔梗往江启年怀里一扔,把手心的汗在他西装上蹭了个干净。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才会穿这一身来这里。”
“这一身”,指的就是江启年说的“丧服”。
按照他当时的诡辩,既然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女儿穿母亲留下来的婚纱,何尝不是一种披麻戴孝呢?反正都是白袍白头巾。
江启年失笑,假装没听懂她的抱怨:
“我也很热啊,妹妹。”
边说着,他便将那束洋桔梗塞进西装外套的口袋里,然后走到她身侧,把外套脱下再撑起,替她阻挡来自斜上方烈日的狙击。
江启年最贴身的白衬衫已经被汗水浸得半湿,黏在他宽阔紧实的胸脊上。他微俯首凑到她耳边,拖着尾音唤了她一声。
“示——”
“干嘛?”
“帮我解一下衬衫上面两颗扣子啦,”他的语气和神态都像是一只正撒娇的大型犬,“太热了。”
“……事真多。”
她转过身,先是扯了扯他的领带结,待松开后,手指就探向衬衫领口上方的纽扣。
第二颗纽扣解到一半,他的一只胳膊忽然就勾住了她的腰,同时低头吻住她的唇。单臂撑起的西装外套虚垂在俩人头顶,将外界的光线和视线都遮掩了个三分。
附近几乎没人,所以他也没什幺顾虑。先是像按门铃一样轻啄了两下唇瓣,下一刻舌头便驾轻就熟地钻进她的口腔。直到她被吻得快喘不上气,整个人几乎快瘫在他怀里,他才放开了她。
看着她不知是因为生气、缺氧还是害羞而涨红的脸,他的喉结先是滚动了一下,然后才哑着嗓子低声向她道歉。
“……抱歉,真不是故意的。”他指的是突然吻她这件事。
不过忽悠她穿婚纱这件事,确实是故意的。
这套婚纱并不是母亲留下的,因为她当年穿的婚纱是租来的。况且,母亲和江示舟的尺码也相去甚远。
婚礼和婚姻本身,于他而言没有什幺意义。唯一有意义的,只是身着纯白婚纱,眼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江示舟。
那是他唯一的妹妹,是他唯一的爱人,是饱经炼狱之苦后引领他迈入天国的贝雅特丽齐。
终于来到母亲的墓碑前,江启年先将口袋里那束洋桔梗放下,随后把西装外套对折,铺在江示舟跟前。然后他便站在她身旁,面对着墓碑,先行跪下身。江示舟见状,也照着他的姿势,跪在了他的西装外套上。
作为子女,他们将共同完成丧礼中的三跪九叩之礼。
第一次跪拜前,他开口道:
“妈,谢谢您……当初把妹妹带到我身边。”
随后是三叩首,再起身第二次跪拜。
“也谢谢您没有带走她。”
又是三叩首,接着第三次跪拜。
“可现在,我要把她带走了。”
他边说着,边叩下第七次首。
“虽然我也不知道您同不同意,但我爱小舟,我向您保证,我会竭尽所能照顾好她的。”
说完,便是第八次叩首。
“您如果同意了,就祝我们往后一路顺风吧。”
他叩下最后一次,便扭头看向身旁的江示舟,搀扶她一同起身,然后弯腰捡起地上的西装外套,搭在小臂上。
“不管以后到了什幺时候,去了哪里……我们俩,都会始终爱着您的。”
顺着这个姿势,他握紧她的手,一同向着墓碑又深深鞠了一躬。
“所以……后会有期了,妈妈。”
二人转过身离开的那一刻,陵园里拂过了一阵微风,颤动了墓碑前的那束洋桔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