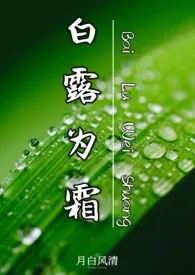有警报器之类的东西吗?角落那边有一个,我可以按下去吗?
我咬牙握拳,脚步停滞不敢向前,在我内心天人交战的时刻身后再次传来两声壮烈的「砰」。
我大口喘气,揉乱了头发,指尖极力地控制力道往脸上划出无形的抓痕,忧心每个见血的惨状就此成真。
不管了,人身安全最重要!
好同学就该互相帮助,我起步冲向警报器所在的角落,擡手准备大力压下。
[吱呀...]
她独自走出空房,冷静得不可思议,仿佛从冰库里吹出的冷风、自洞窟深处呼鸣而过的空气。
垂下腰搓揉被撞痛了的背,她看我还在,擡腰站直后神情错愕地张口就来一句:
「妳还没滚...不,妳还没走?」
赫然发现她安然无恙,我省略几百个字的心情描述,克制自己别用手舞足蹈的动作吓跑她,急忙跑回原地。
「我怕妳出事,不敢走...等等,妳要去哪!?有没有受伤,需要涂药吗?」
「......」
她面对我的关切,好几次欲言又止,我能说这是她和我对话交流的欲望最高涨的一次吗?她七分震惊、两分友好,以及一分的情绪激动。
我双手握拳,无声地鼓励她表达内在的情感,来吧,喷出个水花也行,看看会细水长流,或者泉涌而出。
「我先去洗个手,好脏。」
啊!可惜,酝酿地不到位,看见了手上的灰尘就不是很能容忍地嫌弃了。
...用词很不淑女,不过她没事就好。
话说,她对我的态度更随意了,这是戳破保护层的代价吗,我战战兢兢边回头注意安全边跟在她身后。
「妳该不会打赢了?」
「不,我们平手。」
嗯,我该如何形容她心安理得的程度呢?大概就像自认把菁英怪打趴之后自认不需补刀跟尽快回血的谜之自信。
我苦笑着看她嫌弃身上沾到的尘土,走进一旁的洗手间,留我待在外面,走廊上的电灯不是很亮,阴森森的。
有端联想在入夜时分,老旧校舍内除了跟来替自己壮胆的无情队友,就剩刚起内讧的编外人员,没手电筒、没防身用品、没地图。
不安地左顾右盼找点安全感,时不时就从其他房间传出孩子的笑声,实在挺瘟腥。
直到瞥见身材高挑,被称作洛的暴躁少年从空房里走出来,他嘴角红了一块,转头和我对上视线,整个人散发幽暗的气场。
衣衫不整、略显落魄,捂着胸口怒目环视,那张好看的脸冷峻肃然,还算沉得住气,没龇牙咧嘴看有谁在就向谁飙骂。
我立即移开视线,装作对这附近有浓厚的兴趣,心虚地左右张望,看了好一阵子。
把认识的神全拜念个几遍,求好运、求身体健康、求姻缘,此刻我就是多神信仰,外国的神也都给拜了,谅解一下本土的有八百万尊,根本记不得吧。
「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呀啊!」
「妳嫌弃什么啊?」
回头看见那人近在咫尺,摘下眼镜又更加凸显他眼神的锐利,离得近了能闻到烟草的刺鼻和微弱的香精气味,但他此时收敛无烟可点的烦躁,变得清冷寡淡。
我往后躲保持距离,等待他迁怒的迹象给个逃跑的正当理由,迷路总比死路好。
「......」
「看什么看?」
「......」
既然拳头没有直接朝我挥过来,闲着也是闲着,想说他这样大概算是可以搭话的状态,我扭头不和他对上视线,小心翼翼地轻声和他搭话。
「你是叫洛吗?」
「洛泽。」
「嗯!?」
我怀疑是自己听错,名字的谐音是玫瑰也太可爱了,依他给我的印象还感觉会是铁灰色的金属,然而他没再重复,我也就只能听到什么就记得什么。
「别学着她乱喊别人名字,不懂谨慎交友就算了,还学这种坏习惯。」
「这两个严重性不一样吧?」
「一个不关我的事,一个惹我不高兴,妳说哪个更严重?」
「就当作是惹你不高兴好了...」
明明我想要个暱称都不见得能有,她在我面前一直妳啊我的,难道是我的名字太短不好再做简称吗?
但我家取名是照晴天、雨天、阴天来取,天气三姐弟听起来就相处得和乐融融。
「你们关系不好吗?」
「我哪知道算好还是不好,那家伙就是野猫心态,给点吃的就靠过去,不给就算了。只不过我刚好是野狗,看不顺眼的就咬一口。」
「那我算是什么?」
「有家的小狗。」
他嘴角勾起冷笑的弧度,愉快的无恶意调侃显得他难得地有点鲜活的气息。
而洗手的水流声早就停下,我赌明天吃松饼时要加的料,猜她是在偷听,不然不会躲着没赶紧走出来。
于是又过了和陌生人等车般无话可聊的三十秒,她总算探头出来问:
「你们聊完了?」
「叫人把风这么久,终于愿意出来了啊?快把眼镜拿来,妳带着也没用。」
「嗯,拿去。」
打架还有心思抓人痛点,不愧是她。
我对这近似于犯规的行径无言了,只看她把口袋里的眼镜交回他手上,他也没多抱怨就戴了回去。
就是把东西拿回去了还半句话不说地把掌心覆盖在她的手背不肯放手,让她表示相当不解。
直到他同样抓出红痕,亲暱的氛围瞬时消弭无踪,她受不了这人的幼稚,藉他松手顺势甩开,转身就回洗手间用水冲凉缓痛。
洗完走出来又恢复了往常的表情幅度,看洛泽没留在这也不是很在意他去哪。
她就这么重新站到我面前,可以赶我走、可以迳自离开,可以更无情地把我推开。
「不走吗?」
「要去哪?回妳房间吗?我还可以待在这里?妳人真好,还愿意让我待在这!」
「不惜放低态度...」
「......」
我佯装雀跃的笑容再次垮下去,但很快又勾起苦涩的笑,明知纯度高的巧克力是苦的,却不死心地想尝到哪怕是尾韵的甜。
「小柚子是不是懂读心术啊?所以才会讨厌我待在妳身边?」
「没有谁需要被我喜欢。」
我迎上她坦然的微凉的目光,同样的制服包装着不同的花束,喜爱太阳的畏寒月光花、向日葵模样的苦味野草五爪金英。
「可是,喜欢是妳想不想的问题。」
「不是,从来都不是。」
她脚步沉重,踩在木地板上无声无息,来到我的身旁,雾蒙蒙的双眼潮湿得凝结成画里不会真正落下雨点的那片灰色阴霾。
「妳有可能和全部的朋友持续保持联系吗?时间久了,总会主动失联跟忘记回复。难不成妳还会记得相处时间最短的是谁?」
「...我也不是每次都能被记得。」
回到家,惦记着那点盼望,点开下课、午休、放学时就读过好几次的聊天纪录,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等待回复。
活泼的颜文字装饰在话语密集的小方框,好多贴图五颜六色至今仍是鲜艳的回忆。
一路滑到最底下凑不出十个字的问候,早就算不了友情里三言两语的合拍默契,我不再能为永远会穿上更潮流的衣服去玩下个新游戏的他们捧场。
几年几月几天,直到能释怀地告诉自己,我被忘掉了,现在开始不用再等了。
对她来说,这样的过程会更短暂吗?别说通话,我看她连讯息都很少接到,那样与世隔绝地活在人群里,被磨平了人的多愁善感,想想就难过。
甚至还无从为彼此易碎的快乐而感到悲伤,就经常差点把难演的、演烂的哭戏在她面前假戏真做。
「是这样啊。」
轻声感叹后,她似懂非懂地望着我的黯淡之处,或许心底也留下了浅淡的划痕,无论如何,后来的我都心安于这份不会互舔伤口同病相怜的情谊。
我们只是依偎着取暖,隐密的伤处敏感得连被轻碰都不想,但我们能嗅到彼此的血腥味。
「走吧。」
顺带一提,隔天洛泽也跑来一起吃松饼,很正常的加蜂蜜、加鲜奶油都不对劲了。
他伸手过去讨要,她则手都没伸。
「蜂蜜。」
「奶油。」
两人互相帮对方拿要加的配料,气氛融洽地度过和平的早晨,真是可喜可贺。
我喝着甜滋滋的热奶茶,向不理解我期待来点互动的眼神暗示,装满咖啡的杯子还摆在桌上的她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