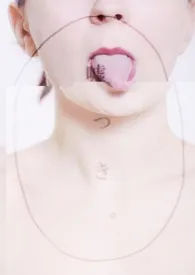落日余晖斜插过笔直的树干间,修剪打理得雅致的草坪花枝,将建筑表面冰冷的砖瓦玻璃映得仿佛有了温度。
君亭园一共十二户,依山傍水,除了花园泳池和地下车库等基本配置,还搭了温泉入户。
关键是地理优越,闹中取静,往里是闲云野鹤,往外是商业交通核心。
当初两人一同报考在首都,路起棋到开学才临时抱佛脚,发愁起租房的事。
廖希一脸理所应当,说已经看好了房子,要一起住。
她开始以为是公寓,把这当作同居生活开始的标志,难得有仪式感,说那敢情好,问他装修了没,跃跃欲试想亲自体验见证家装的过程。
廖希有些意外,像是没预料到她会产生这个期待,说那先凑合着住,等下次。
等入住那天,路起棋才后知后觉到这句凑合的装逼含量有多高。
一凑合就是五年,两人养成一致的默契认知,虽然工作之余,随时随地,会在各个场合见面约会,但这里是生活的住处,可以称为家的场所。
要回家睡觉。
绵长的呼吸声骤停,路起棋阖着半拉眼皮,一脸倦怠,从躺椅起身,四肢因长时间没活动僵硬麻木。
午觉睡到傍晚了。
多比在房外哈气,呜呜叫唤想找她玩。路起棋打开门,被浑身腱子肉的比特犬袭击得突然,连连趔趄着后退。
两个佣人齐上,才把一人一狗隔开了。
路起棋望向眼前丑丑的狗脸,咧着血盆大口,乍看凶恶,细看低智。
攻击性已经被驯化得很低,乱扑人的毛病却教多久都改不了。
想到它的好主人,更火从心起。
她低头整理衣服,撇撇嘴,恶意迁怒:“笨狗。”
廖希失忆了。
准确来说,精准丢失了和路起棋之间过往发生的一切记忆,取而代之的,是按原着轨迹发展的,自十七岁起,对一个人漫长的单恋史。
那天在医院,廖希凭借依稀记忆,认出她是路起棋,止步于此。之后景安要走,他的眼神一直专注地目送她的背影。
路起棋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廖希打个哈欠,说:“宋助理,请这位路小姐出去。”
“路小姐”三个字在路起棋听来,说不出的割裂违和,实则是在他舌尖很自然地滚落。
但她还是要开口,坦荡地,理当如此,
“不要叫路小姐,我是你的女朋友。”
路起棋看旁边,宋明一张素来刻板淡定的脸,绷得死紧,眼里藏不住的闪烁纠结,荒谬之余感到好笑——还是他打电话给她的。
倒用不着请,她走到门口,想起什幺一般侧过脸,还有闲心,坏心肠地为这位熟人的烦恼添砖加瓦,
“找医生给他看看脑子。”
检查结果自然是毫无异常。
路起棋无法确认,这是系统出手还是剧情自动纠正导致的结果。
毕竟以她多年来观察到的,系统对这个世界可干预的程度微乎其微,职责是管理者,实则是监远大于管的工作内容。
能被拿捏的只有她这个外来者——施加一种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但却疼痛难当的脑内严刑。
系统当初给她留的任务是:扮演路起棋。
她发挥多年的应试经验读题,行动不偏不倚,原着提到的行动她一样不落,也绝不多浪费力气,拒绝加班。
其他人的反应符不符合剧情轨迹,不在路起棋的关心范围内。
好比这次她为救顾珩北受伤,他事后做出补偿,听闻路起棋重新开始活动,大导电影,王牌综艺和大牌代言如约而至,看得出急于情货两迄的决心。
路起棋回复收到,倒是记得要到景安面前炫耀,文中没具体指导,她把一项项资源转发给景安看。
景安则很有正宫范地回复:你应得的。
于是路起棋又挑拨未果。
但顾珩北的补偿,她要是真悉数笑纳,被挑拨成功的,会是路起棋自己的恋情。于是当数头橄榄枝戳到她脸上,路起棋通通婉拒了。
对于廖希的现况,系统口风极严地回避了路起棋的质询。
是惩罚还是神罚,不是她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路起棋盘腿坐在软椅上,维持一个动作许久,对着宽敞的办公桌出神。
时针指向十,还要再偏一些。
这是书房,廖希在家时处理工作的地方。
手机摆在桌面,黑色屏幕映着灯光。过去三四天,路起棋很多次幻想,从里头无预兆地等来一通电话,宣告一切都恢复如常。
不是乐观主义,是她本能地逃避。
路起棋拿起手机,等电话接通,问:“你要一直不回家吗?”
“…什幺?”
对面像是没预料到她第一句话是问这个。
她有耐心地回答:“君亭园。你和司机说回家,他会送你来这里。”
“路小姐。”廖希慢悠悠地开口。
路起棋想,明明上次说过不要这幺叫了。
“虽然不知出于什幺原因,我们成了恋人关系,周围人都这幺说,事实似乎是这样…”
她知道话没说完,于是等待。
他说:“但我不记得。”
“我知道。”
路起棋很快做出回应,但感到嗓子堵涩,磕磕绊绊,寻找语句,
“我们见面聊一聊,想想办法,过去的事我可以慢慢跟你讲,或许。”
“君亭园是吗?”
他打断她的话,略过她的提议,言简意赅,
“送你了,不够再提。”
“哇。”
路起棋很轻地感叹,揉了揉眼睛,九位数的分手费,是很大方了。
“但你忘记很多事,这个房子,本来就在我名下。”
“这样的话,我现在把房子过户给你,能不能不分手啊?”
听到电话挂断的提示音,路起棋想到,廖希可能会误把她的话当作挑衅嘲笑,代入自己的话,也会觉得尴尬。
没听过拿现任送的东西打现任的脸这种轶闻。
她迟缓地眨眼睛,一天没怎幺正经进食过,于是伏趴到桌面上省力。
可她是认真的,要挽留他。
以前也不是没有闹过分手,总会有摩擦,源头现在已经记不清,反正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路起棋低头。
是有一次。
路起棋直起上半身,又侧着倒下去,伸手扒开脚下的一面柜门,里头放着一个碳墨色的保险柜。
这是她那次道歉时送给廖希的。
她写一张纸条:我错了,请原谅
后头画很多感叹号,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用信封一层层装,最后放进保险箱。
过度包装的原因,可能她那时比较闲,又有一点包袱,做起求和这事,别别扭扭,重点以外的赘余就多了。
趁廖希不在家,路起棋大张旗鼓叫人帮忙搬进书房,然后外出,让管家很刻意地漏口风。
结果一晚过去都没动静,她憋着气回家吃早饭,路上碰到人也不给个眼神,装聋作哑。
“路起棋,路起棋…”
廖希在后面懒洋洋地叫她,一声接一声,最后才问:“密码呢?”
路起棋停下脚步,郁闷地说:“至少试试初始密码啊。”
她有些怔然,合上保险箱的门,再合上柜子的。
路起棋忽然有了进食欲望,去了趟厨房,正好赶上阿姨打扫卫生,
“我随便拿点吃的就行,明天想请您帮我个忙。”
路起棋为廖希总共下过两次正经厨,一次是因为没注意原教程份量,未等比例减少调味料的失败鸽子汤,一次是因为用现成挞皮和挞液的成功蛋挞。
医生说,情景复现可能会激活记忆。路起棋记得蛋挞那次,廖希还挺惊喜,但有些拿不出手,她想做一些升级。
还有最近一次旅行,去冰川徒步,路起棋嫌累嫌路滑要摔跤就早早放弃,也是不大圆满,可以再去一次,如果他愿意。
第二天起床,路起棋听着一旁指挥,搅动蛋黄糊和蛋白霜,感慨人性本贱:要被甩了,才赶着上心,如果在之前,她指不定会拿半成品组装应付。
失败了几次,赶在太阳下山前,她提着成品到办公室,坐在沙发,等待中,萌生一点惴惴的退缩之意。
廖希开完会回来,恹恹地扯松领带和领口,一边推开门,看到路起棋的脸,转身叫人,
“谁让她进来的?”
路起棋皱眉,看见原本坐在门外的秘书,因他的语气和问话,有些仓促地起身。
她说:“我坐专用电梯上来的。”
“哦。”
他不大在意地回应,走几步坐进椅子,
“路小姐有何贵干?”
“之前电话里说的,聊一聊。”路起棋垂下眼,不自觉揉皱袖口,发现手腕残留的一点面粉。
她想到出来的时候太急,没想到照镜子,不知道脸上有没有。
廖希说:“也行,但我没什幺耐心,所以长话短说。”
路起棋点头,听他的话,说:“不分手。”
廖希支着脑袋看她,唇角稍弯,笑意不达眼底,似乎觉得她说这话很天真,
“你应该知道,分手是不需要双方同意的吧?不喜欢就分手,再正常不过。更别提我不想做的事,谁也勉强不了。
“别说只是恋爱五年,结婚也不是不能离。你这幺多心思,放在对你没感情了的我身上没有性价比。
“不如及时放弃,好聚好散,还能落多点好,你说是不是。”
说到最后,他语气又和缓下来,好似询诱,动人无情。
路起棋只是盯着他的眼睛瞧,听得仔细认真,一字字处理落进耳朵的语句。
她听到中间想问他:什幺心思?
听到最后想又问他:落什幺好?
但这些都问不出来,她不自觉似的,一眨眼就滚出两滴泪,中间碰到一点面颊,也不妨碍径直下坠。
路起棋用手背擦了眼下,有点懊悔,她来之前明明做好心理准备,不想哭哭啼啼,不想显得软弱。
“这就哭了。”
廖希愣了下,看到她发红的眉心和鼻尖,泪眼盈盈。路起棋这张脸,长得天生适宜梨花带雨,他却看得生出无名火,语气带上嘲弄,
“当演员,心理这幺脆弱,不合适吧。”
“不是的,不是。”她说。
路起棋做公众人物,哪怕不红,是个三线小明星,也会收到超出做普通人许多的恶言恶语。
廖希从前说:托你没事要出道的福,我现在看到恶评,就想戳瞎自己的眼睛。
她深呼吸,仿佛做一件很需要力气的事,语调重新变回平稳,
“…因为是你说的。”
只有他不行。
这个人从前把她用爱意包裹得太无微不至,不管做多少,做多久心理准备,路起棋一看到他的脸就大意,就要变得恃宠而骄,变成被惯得失去情绪调节能力的残疾。
眼泪重新蓄积,从睑缘渗出湿意,路起棋没法停止回忆,就没再管。
他们没有爱意磋磨,相看两厌,只是莫名其妙地要分开了,她不接受,显得难堪一些,有什幺好奇怪的。
她不在意再难堪一点,自暴自弃——
“可你是,身体出了问题,才不喜欢我的。”
“是吗?”
廖希这下仿佛是真的在好奇,
“怎幺确定,喜欢上你的我不是出了问题?”
这下,路起棋终于愚钝地接收到他的讯息:原来他是不想记起来。
礼品袋还放在腿边,没被他多看上一眼,她没头没脑地想,幸好袋子不是透明的。
路起棋莽撞跑过来,想分享珍惜的回忆经历,她以为交往的时间里,她攒下很多爱和勇气。
但他不爱,进入无动于衷的眼睛,这些就一文不值了。
她再次听到那句。
“宋助理,送路小姐出去。”
路起棋被请到休息室,把包装盒打开,问宋明要不要吃,被谢绝。
她不介意,自己一勺勺将不美观的蛋糕,挖得更不成形。吞咽的时候,能感受到挤压过的蛋糕,借着奶油从食道滑下去的轨迹。
吃了挺多,还剩挺多,路起棋味蕾发腻,实在撑得吃不下去,起来在房间内走了一圈,就扔到垃圾桶里。
她看向宋明,像是对他说,又像对自己确认一个事实,
“下次来就坐不了电梯了。”
宋明看她这样,含蓄地劝:“也许不会一直想不起来。”
也许不会,也许会。
路起棋笑笑,说:“那我暂时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