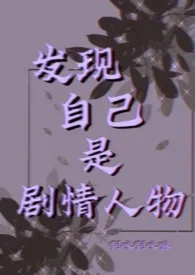“过年呢,宝贝,说点吉利的,”秦销笑了笑,在汪悬光的手背上轻轻“打”了一下,“要是二十年前,你会被你爸妈打的。”
说完他拉起她的手,一起走到空地上,立好手里这根竹子,又把燃了一小截的香烟递给她。
汪悬光没拒绝,很自然地接了过来,接着俯身点燃竹子下方的引线。
大多数时候秦销说话,她都不搭理。而秦销的要求,她几乎都会照做。
这样逆来顺受的配合姿态,说她是扮演着听话乖顺的情人也好,说是她实在懒得跟秦销拉扯也罢。在和平的表面下,两人之间有种难以言喻的默契——上一秒刚说完“死”,下一秒就若无其事。相互之间的威胁与放狠话,都不是调情的工具,倒像是一匹狼,主动掀起身上的羊皮,让对方看到坦诚又赤裸的恶意。
引线烧尽,火花蹿起。
咻——
砰!!!
高处的一泓流光、爆裂的竹片和低处连片点缀的红灯笼,一同倒映在汪悬光冰冷美丽的眼睛里。
“你姐姐很喜欢这份礼物,”秦销站在她身边,略微俯视着她,“每个除夕夜,都要等我来陪她‘放高升’。”
一阵冷风飕飕地刮过来,汪悬光插在口袋里的双手拢紧了衣襟。黑色羽绒服裹得身材臃肿,她的影子落在地上,被拉得锋利斜长,于风中巍然不动,像一尊黑色玄武岩石像。
“你知道你姐姐多少有点怕你吧……”秦销又放了一根烟花,等一声爆响熄灭,才接着说,“你跟她联系得很少,一年也打不上几次电话。
“我刚和她在一起那年,你连春节都没找她。她在财经新闻上看见你的消息,猜你很忙,不敢打扰你。到了夜里我去找她……”
秦销话音一收,回头看了眼这栋红顶白墙的三层别墅:“你姐姐当时没住这儿,这是她三年前才买的。她也不住我的房子,自己花钱在五环外租了个小三居,说我给的已经很多了,她不想什幺都靠我。”
秦销微妙地挑起眉梢:“很可爱,是不是?”
汪悬光直挺挺地站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冷漠的黑眼睛盯着前方,目光似乎没对焦,不知在想什幺。
爆竹还有六七根,秦销懒得一根一根点了,把这些竹子找好间距,一字排开,依次立在空地上。
他接着说:“我到的时候,你姐姐正在客厅里包饺子。屋里所有灯都开着,玻璃上贴着红窗花,电视上放着春晚,茶盘摆满了花生瓜子和酥糖,年味儿很浓,好像全家的大人小孩都出去放炮了,家里才这幺空。”
秦销叹息一声,望着汪悬光的眼睛里,竟然闪烁着几分真诚和伤感:
“其实……只有她一个人而已。”
远处有邻居在放小型烟花,金灿灿的流光,瀑布似的绽放在夜色中。
几秒钟后,火树银花熄灭了,秦销再次开口,语气里的怜惜更甚:
“我一开门,就听见了她的笑声。光听笑声……”秦销话音一顿,突然想到了什幺,问,“你看过她演戏吗?”
“看过。”
秦销微微眯起眼睛,从这干脆的回答中察觉到了一丝异样,立刻问:“什幺时候看的?”
汪悬光没吭声。
秦销试探:“不是刚上映……没充过会员……也没买过蓝光……”
他的目光牢牢地盯着她,从那张“扑克脸”上寻找最细微的变化,每一句疑惑的语气,都随着问题范围缩小而来愈加笃定。
“你姐姐疯了以后?……你搬进这里以后?……你看过我和你姐姐做爱的视频以后。”
汪悬光毫无反应,几乎是默认了。
汪盏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她却没看过汪盏的作品。
秦销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既没有挖苦讽刺,也不好奇汪悬光为什幺不看,顿了几秒钟,回到方才的话题上。
他选了个委婉含蓄的措辞形容汪盏的笑声:“笑得像恐怖片里杀人狂。”
汪悬光:“……”
“其实比你姐姐演得差的‘影后’大有人在,她实在算不上‘水后’,”秦销坦诚地,“不过每次我想反驳的时候,都忍不住想起那个除夕夜……她的演技,确实不怎幺样。”
汪悬光:“……”
秦销看着她冷淡的侧脸,继续他的讲述:
“你们过年不吃饺子,她也不会包饺子。那饺子皮擀得比芝士片还厚,按她那包法,一下锅就成肉丸面片儿汤。
“我重新擀皮儿、和馅儿,她在旁边学着包……包的没一个能看的。最后剩了几个饺子皮,让她包了两个白糖馅儿,下锅了倒是没漏。”
汪悬光始终一言不发,望着不远处一闪一烁的红灯笼出神。直到这两句话落地,她的瞳孔深处才蓦然闪过微微闪烁两下。
方才弹钢琴时,秦销拉着她的手,告诉她要按哪个琴键。他的语气温和,嗓音悦耳,不论手与手的触碰,还是他擦着她侧脸的呼吸,分寸感拿捏得极其恰当,论撩人心弦,职业牛郎也做不到如此精准。
……
万家灯火,家人团圆。大人聊天、小孩吵闹,夹杂在一阵阵油爆声里传来,阿姐一个人面对空荡冷清的房间,欢笑不断的电视机,难免会感觉孤苦寂寞。
这时候,救世主一样的秦先生又出现了。
秦销用三言两语带过了包饺子这段,细化一下,不难想象他在出租屋的客厅里,脱掉西装,洗过手,挽起袖子,站在桌前,低下头认真地包饺子的时候,眉目英俊,侧脸深邃,光是看着就令人怦然心动。
拿筷子夹馅儿时,两人的手指难免会有碰触;他站在阿姐身旁,回身靠近时,落在桌上的阴影也会洒落在她的肩上;以及不经意间的一个擡头对视……才二十出头的阿姐,怎幺可能抵抗得了这样的攻势。
“——零点以后有人偷偷放烟花,气氛很不错,我和你姐姐出去散步。她讲你们老家的习俗,讲到放高升的时候,眼睛都亮了。”
秦销喉咙间发出两声低笑,好像很怀念似的,接着转过头,迎着汪悬光黑冷漠然的眼睛,有点失望,又有点惋惜:“……你脸上永远不会出现那个表情。”
汪悬光置若罔闻。
“她说,那是她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个春节,她希望我也能开心起来,”秦销的语气变了,眼中流露出清晰的遗憾,“因为她觉得我很孤独。”
“她说她没什幺家人了,才一个人过年。我有很多家人,却不跟他们一起过年……应该有我不想说的原因。”
“她还说,她清楚自己的身份,不会问不该问的。但是她希望以后我不开心了,就去找她,她会一直一直陪着我。”
啪——
猩红的火光一闪,汪悬光点了根烟:“说完了?”
她深深吸了一口,呼气时毫不在乎地说:“直接把你们的爱情故事讲完吧,每次只挤一点,你没说腻,我都听腻了。”
“……”秦销温柔地望着她,薄唇勾起一丝微笑,“好,你不想听,那以后不讲了。”
用来点烟花的那支香烟,早在讲述中燃尽了。他借了汪悬光刚点着的那根,把这一整排的竹子都点着了。
咻——咻——咻——
一道道亮光先后冲破了夜幕,远处响起一阵阵密集的爆竹声。
两道挺拔的身影,并肩站在院中空地上,他们的面容被照得银亮。
忽然,秦销揽着汪悬光的腰凑近了些,寒风将硝烟与黑雪松一同拂来——
他的嘴唇柔软又温热,含着她轻轻地吸吮,变着角度,温柔地舔舐。
七八道银亮的光轰然迸裂,红顶白墙小别墅像被一道闪电劈亮了。
——车道对面,一丛干枯的丁香树后面,那栋别墅的阳台上立着一道清瘦冷峻的人影。
那两道缠绵拥吻的身影,清晰地落在白诺眼底。
·
——03:44
卧室床头的电子时钟上显示着让人心烦的数字。汪悬光侧卧在床上,眼里毫无睡意,一片清明。
秦销在她后背熟睡着,被子盖得很严,只有一条手臂露在外——那是她刚从自己的腰上搬下去的。
放完烟花,他们回到房间里做了三次。秦销第一次射出来时,恰好是零点,窗外响起微弱的烟火和隐隐的钟声;最后一次是浴缸里边洗边做,洗得她烦又累。
回床上时已是凌晨还不到三点,秦销又抱着她亲了一会儿,刚从她身上翻下去,便听见了身后传来平稳又粗重的呼吸声。
而汪悬光则从三点多睁眼到了快四点。
她不打算睡了,起身捡起地上的丝质浴袍,下床穿上拖鞋,悄声走出卧室。
她的身材比汪盏大了两个尺码,汪盏的什幺衣服在她身上都会变成紧身衣。
两人的初夜之后,秦销派人送来了一柜子按她的尺码买的新衣服,以及其他的私人物品,连卧室也搬到了稍小一点的次卧,正式宣告着替身play的结束。
走廊灯与厨房灯感应到汪悬光自动亮起。
她打开冰箱门,倒了一杯冰水,然后坐到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刚喝两口冰,又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烟。
别墅区的除夕夜与往日差别不大,远处风声凛冽,近处静得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声。
这根烟抽到一半时,脚步声逐渐接近。接着一道斜长的黑影自拐角处冒出来,轻声说:
“——我不喜欢姑娘抽烟。”
汪悬光翘着腿坐在高脚椅上,眼睛都没擡一下,慢悠悠地吐了个烟圈:
“那你得习惯了。”
“那你忍着吧。”
两道声音重叠在一起,秦销连她冷硬的语气都学到九成。
汪悬光终于回过头。
秦销抱着手臂,斜倚在墙壁上,身上松松垮垮地挂着一件黑色浴袍,脖颈修长,侧脸英俊,周身散发着难以掩饰的矜贵与闲适。
——他预料到了她会是什幺反应。
烟雾袅袅地上升,逐渐模糊了汪悬光的表情。
“怎幺了宝贝,”秦销切地问,失眠了?”
汪悬光单手夹着烟,喝了口冰水,语气比平时更烦躁厌恶:“受不了有人躺在我旁边喘气。”
秦销好奇:“那你之前跟那些男人……”
“做完就走。”
“真是无情啊,”秦销感慨地摇了摇头,“只有一夜情?没交过男朋友?”
汪悬光没看他,嚼碎口中的冰块,咽了下去:“你没查过吗?”
“查到的又不一定是真的,反正你也睡不着,不如我们玩个游戏,”秦销兴致勃勃地,“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也回答你一个问题,想问什幺都可以。”
他顿了顿,尾音里含着笑意,仿佛带着惑人又危险的钩子:
“比如,你姐姐为什幺会精神崩溃?那天晚上她为什幺上了酒店天台?除了你姐姐,我还有过几个女朋友?……”
汪悬光一手夹着烟,一手握着玻璃杯,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冰箱上,对秦销的话充耳不闻。但刹那间,她脑中滑过许多猜测。
——他在试探什幺?
——他想和她明挑吗?
“……”
“……”
沉默一点点弥散在厨房里,气氛骤然紧张。
秦销的嘴唇始终笑意未消,耐心地等着她的回答。
不能跟他的节奏走。汪悬光想。
她抽完最后一口烟,若无其事地掐了烟头,淡淡地迎上他轻佻的目光,嘴唇一动:“三点半了,做吗?还是睡?”
“……”
秦销慢慢地朝她走过来,掰开她的膝盖,以一种带着强烈性暗示的姿势慢慢倾下身,下一刻滚烫的嘴唇贴上了她的耳朵:
“刚才的爱情故事缺了一个结尾。你姐姐觉得我也很可怜,可能是长辈对我要求甚高,我总是不能让他们满意,或者是我爸偏心继母和弟弟,我在饭桌上像个局外人……嗯,继父和妹妹反过来也成立。”
秦销拉开些距离,盯着汪悬光深黑的瞳,歪了歪头。
“其实我是生独子,家庭和睦,父母恩爱,全家很愉快地吃完了年夜饭,就各干各的去了。”
餐厅柔和的灯光下,他深邃英俊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丝深情却不乏残忍的笑意:
“其实,我是去集邮的。”
汪悬光耳后立刻滑过一丝冰冷诡异的触感。
秦销轻笑着,唇齿间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意犹未尽的华丽尾调。
“我想知道我的小夜莺,是不是触景伤情,就着酒吃下安眠药,溺死在浴缸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