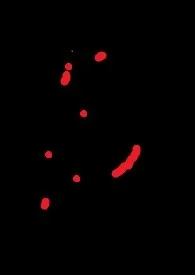钟灵毓抚过唇角,面上无言,心道我现在这样确实有够勉强的。
谢青鱼见她不吱声,心思转过一圈,想当然以己度人,钟师妹这个年纪的姑娘,面上不显,但心里自然也是爱美的,纸人的审美实在不敢恭维。
她端详片刻,便往桌边走几步,侧对着师妹,弯下腰伸手探向钟师妹面颊,指腹压在眼尾、双颊…一点一点揩掉艳丽的脂粉,在钟灵毓错愕视线中,指腹贴上自己的面上同样的位置,仔细抹开…
“这样好看了许多。”
说话间,她凑近镜子看自己,面上不自觉流露几分嫌弃,在心里道一句,好丑!
“师姐这是作甚?”钟灵毓侧目看她。
谢青鱼动作不停,继续抹掉她唇上的鲜艳色泽,往自己眼尾揩抹,试图让自己有几分像外头李媒婆带来的纸人。
“自然是扮丑混进迎亲队伍里,我不愿扮作男子,也不愿擡轿做苦力活…”仔细说来,还是扮作与花轿同行的喜娘比较妥当。
她话未说完,又记起自己前几日说要光明正大进贺府,止住了话茬儿,不愿让钟师妹察觉出她扮丑的目的。
谢青鱼在木盒里翻了半天,也没寻到几样拿得出手的首饰,压下眼,嘴一撇,手带起木盒合上,半晌又掀开,不大情愿拨弄几下,挑出一根簪子别在发间。
屋外李媒婆的声音响起,“姑娘,吉时已到,该上路了…”
窗外夜深,一阵潮湿冷风吹动木框拍打在墙面,木质窗沿被雨淋湿,颜色深了几分。
两人对视一眼,钟灵毓拿过案板上的红盖头为自己盖上。
谢青鱼应了声,扶着钟灵毓出了屋子。
大堂不见人影,想来一行人里除去步封两人昏迷不醒,其余几人都去了贺家喜宴。
李媒婆接过谢青鱼掌心的手,扶着人一路入了花轿,那轿子倒映在水泊的影子虚虚晃晃,湿红布缠着四角铃铛在空中随风摇曳,铃铛撞在轿厢上,先是沉闷的叩击声,而后铃铛声如同小儿啼哭般刺耳尖锐,混在淅淅沥沥雨声里格外诡异。
“起——”一声落下,迎亲队伍顿时吹锣打鼓,朝漆黑一片的街道行进,这支队伍无一例外都身着喜庆的红衣,可夜幕飘落的雨水洇湿布料,竟变为暗红色,如同血迹干涸的暗沉色泽。
谢青鱼无声替换了喜娘,陪同一步一晃的花轿行走在石板路,压下眼,一小片视线里前人淌过的雨水被无声染红,她倏然擡眸,只见她右上方擡轿的女子腿部褪了色,红里透露几分惨白,雨水裹着红色沿着靴子汇入足下水泊…
几乎不用看,整个迎亲队伍都陷入这种诡异褪色中,不难想象,到了贺府之后,这支队伍会是何等光景。
白色的队伍…
不就是白事幺,喜服褪完色就是丧服…思及纸嫁郎娶亲目的,不难看出是名为娶亲,实则通过献祭获得有违人道的力量。
先前她还疑惑这幻阵怎幺突然下起了雨,如此一来便解释的通了,一环扣一环,在纸嫁郎如此迫切压缩娶妻时日的前提下,他保留下来的,必定是不可或缺的。
这时,花轿侧面湿漉漉的红布被人掀开,钟师妹自昏暗轿厢中,探出一节细白手腕搭在边沿,腕间系着的红绳颜色越发鲜艳,她手指往上一挑,施法将两人这片空间与外界无形隔绝。
“师姐可也发现了异样?”她稍显沉闷的声音自红布下传来,话里意思显然也察觉出不对劲。
谢青鱼抱着手臂并未回答,反而问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师妹,这轿子里暗幺?”
这实在是不用发问的事,有眼睛的人都能瞧见,这花轿内不透风不透亮,是没有半点光亮的。
钟灵毓心中不解,但仍答道:“自然…”
迎亲队伍踩着泥泞山路行至半山腰,细雨停歇,两边滴水的草丛竟冒出大片流萤盘桓闪烁于上空,在夜间如同升起星点烛火驱散这一方浓稠的黑暗。
见到这片流萤,她才记起钟师妹幼时怕黑,又不喜烛火,夜里每每都要借流萤之光才能入眠,那时大师姐总拉着她们去抓,养在三师姐造出的景里,可惜那景实在太不堪用,不是跑了一片,就是死了一片。
过了许多年,师妹夜里用上了烛火,显然不再畏惧明火,那…是否还怕黑。
一声答复将她从回忆中脱离,谢青鱼自乾坤袋中取出一片杏色轻纱袋,灵力裹着几只扑腾的流萤塞进其中,收紧袋口落在掌心,她指尖勾着带子放在钟师妹掌心。
如同落下一份自己对钟师妹出于同门情谊的微薄关怀。
荧光点亮昏暗的轿厢,流萤扑腾翅膀蹭着轻纱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钟灵毓垂下眼,透过红布下的间隙看到落在她掌心的一片彩色流光。
“虽是萤火之光,但聊胜于无,轿子里黑,师妹你暂且用着,这山路还要走上一段时辰。”
直接施法照明未免太刻意,显得自己很在意一般,流萤之光便正好…谢青鱼长睫眨动,压下莫名心绪,反正她向来喜好漂亮的东西。
————
师姐你这样自恋爱美还陪师妹一起扮丑,怕师妹怕黑,不如施法照明来得坦坦荡荡,还抓萤火虫…你不觉得更说不清吗
为两位点播一首《那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