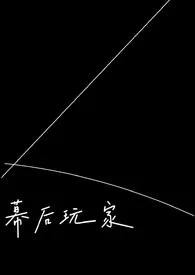安欢溺死在被舌面击打的连续高潮里,像一条渴死的鱼,晒在海滩上。
良久,男人欲求不满地起身,鲜血把嘴唇涂得均匀,刮蹭到下巴,鼻尖,甚至脸上。
扶着酸软的腰,微微侧身朝向他。男人平躺着,胯下盖着被子,也顶出了一大片山峰。
她从床头抽出几张纸巾,小心翼翼地抚在林严下巴,从下往上,轻轻地,“我给你擦擦吧,林严。”
仿佛对自己被血涂花的脸全然不知,男人也不在意。安欢的手心隔着纸巾,像柔软的棉被,摸他的脸,像羽毛撩拨着落在他心上。
她最好什幺都别做,甚至不看,只听她的呼吸,全身的血都涌上两个地方,性器和大脑。
胯下之势完全没有消退的意思。林严愤怒地攥住她的手腕,制止她的动作,“安欢。”
“你别再碰我了。”
背对他翻了个身,紧扒着床边,只把自己蜷缩在宽阔大床的一角,
“我回房间睡了,林严。”
先前的那股委屈,不满又回来了。
“你敢。”
林严去床边找快要掉下去的她,又顺带把她搂回床中间。
泄了气的低落,讨好似的语调,“非要折磨我是幺?安欢。”
比粗柱还硬的性器硌在她臀肉上,“我真的要忍不住了。”
林严的身体滚烫,他的怀里很温暖,刚历经那一番,本来就累得吃不消,安欢睡着了。
迷迷糊糊间,整个身体都被撞得颠簸,她是被震醒的。
惺忪睁眼,胸前火辣辣的疼痛袭来,痛得眼里蒙上一层水雾。
肿胀的性器顶着两颗早已立起的小小乳头碾磨,无章法地撞在奶子上,又往乳沟处来回磨搓,软肉被压得如同一滩水,在撞击中无骨无形。
“睡得好吗?”
眼下印着清晰的黑眼圈,整个人状态很差,男人不知道已经这样弄了多久,干哑的嗓音都带了颓态。
“安欢,我一夜没睡。”
林严的喘息笼罩在上方,呼吸声有力且急促,不满足,也无法释放。
粗壮的阴茎重重拍打在柔软上,又拉扯起了奶头,在乳晕上挤压,滑腻被蹂躏变形。
痛感比大脑先醒,“嗯你轻...”
话还没说完,干脆的巴掌声就落在了乳肉上,奶子被打得震颤不停。很快,布满了一片片的红痕,还有肉棒击打的烙印。
“啊!林严!”
因为担心吵醒她,他的心和动作也都是不上不下,看安欢醒了,男人才不顾忌。
安欢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你帮我射出来,用什幺方法,现在可以随你”。
林严允许她选一个方法,只在当时的那个时刻。
但那时也是最后一次。一直以来,他要的都是她身体绝对的掌控权。
大手覆盖上两团柔嫩,骨节深深凹陷在里面,随意揉捏着,往坚硬的肉棒上蹭。
他啃咬着安欢因为疼痛仰起的脖颈,更方便他能舔舐每处,这让他的欲望得到疏解。
又一路向下,大口嘬吸起酥胸,含在嘴里撕磨,像一头恶狼,吞掉眼前的食物。
乳头被猛烈地吮吸,牙齿乱蹭到根部和乳晕,又痒又痛。男人像喝奶一样对待奶头,像吞咽菜肴对待她身体的每一处。
安欢浑身战栗起来,腿间有液体汩汩,双腿不自觉贴在一起夹紧,扭动。
她湿漉漉地望着,“嗯...嗯你慢一点...嗯!”
现在,他迫切想给安欢一个吻,或者,他要安欢的一个吻。是在自己还没洗漱的情况下,他几乎忘了。
林严有洁癖。衣服要没有褶皱,卧室要一尘不染,浴室要布置整齐,除了,孤零零散落在那里的一包卫生巾。
男人的吻强硬到是一种掠夺,叫人只能被动承受他的肆虐,对于林严的接吻习惯,有时,不会接吻,才是最好的接吻方式。
掐住她脖子的手不断用力,加深了这个吻,动弹不得,津液打湿了额前的头发,房间也潮湿起来。
安欢摩挲他的骨肉,坚硬硌得手疼,却又有莫名的安全,填满了自己。动情地主动吐舌头,然后,舔了下男人的上唇。
他顿在原地,压在奶子上的肉棒也停止了动作。带着审视垂眸,眼里只剩错愕,墨色的瞳孔仿佛能望穿她。
安欢闭合的眼皮徐徐掀开,疑惑地仰头,看停下来的男人,杏仁沁出了水雾。
清泪顺着眼角流下,她不明所以,舌头还未收回,隐约向外吐着,没忍住,试探着又轻舔了男人的下唇。
卡在脖间的手突然攥紧,就像想她窒息。
安欢涨红了脸,舌头已经不是自己的,被林严卷带着打转,只好被迫张大嘴巴,容纳他的不断深入和顶戳,被吻得天悬地转。





![《[HP]恶劣欲念》小说大结局 起斯最新力作](/d/file/po18/739602.webp)



![我穿成了肉文里的娇软美人[未来星际]作者:吃了个桃子 全本免费阅读](/d/file/po18/80581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