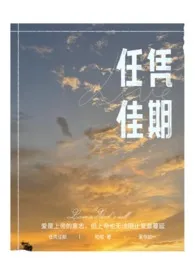息再带一名艳丽的少女,和一名拎行李的青年,说来做客。
他要魏侯用车迎他,魏侯照做了;车停门口,他坐侯家主位,掸灰、喝水、搂女人,魏侯等在帐下,听到他问:“魏侯这样接风?”半天说不出话;劝酒官和斧士不知由谁招待不速之客,互相推辞,见魏侯走出,忙问:“难道是我侯邀请他?”
魏侯落魄极了:“都下去吧。”
息再要听钟,魏侯找人擡;要喝新酒,魏侯和林官采树籽酿造;要看常山军演练,魏侯为难:“息大人,譬如剑的首铤,非握在执剑人手中不可,我祖父合军,留给我这份家业,一直由我统帅,过去赵王只用不问,如今大人你却要看……”
“你的不是我的?”息再诧异,“我已纳赵国土,却要舍去常山军?”
魏侯假装镇定,出门一步两阶,边走边想:“完了,我们闭塞,竟不知赵国已经沦陷。”他欲派人探探消息,无奈道路被占,一匹马都走不出去,不得不爬上望楼,继续用石片远视:“战胜赵王?仅凭一支兵马,如何做到的呢。”
他和属僚开会。大家都被息再吓着:“哪有中军孤身入阵者?我侯请看他惬意地来,怕是真的。”
魏侯也觉得有理:息再几乎将魏侯家当作行宫。
但离云在扎堆的男人之后,打断他们:“他来得及时,似乎常山两次受困,将为孤城,他便来了,诱使我侯献地。”
有些话不好明面上说,等人散去,离云又补充:“况且我侯曾与息再有约。但我侯违背在前,没有牵制燕赵,反而装病,暗昧不清。息再本应怪罪的,现在却在这里作势。我侯请想,以他作风,真的攻下赵国,第一要砍常山的旗中。”
魏侯点头,突然给儿子一掌:“吃里扒外,你还算是魏侯公子?虽如此,这些话是锦锦教你的吧。”不顾离云哀求,他持剑去锦锦处。
锦锦正在查簿,被魏侯挑破衣裳,很快镇定:“罚公子不如罚我。但魏侯需知,锦锦心向常山,说的都是实话。”
她跪在魏侯脚下,枕他的鞋,再三请他留意来人。
魏侯呵斥她,却听见幼子哭声,有些心软,最后只斩断她的发髻,警告她本分些,不要乱给离云出主意。
魏侯走后,锦锦继续查簿。
离云慌张来,见她披头散发,要流眼泪,却被锦锦示意噤声。
“小云,你看息再要的都是什幺?”
在魏侯住处多日,息再索要声色之余,还要走大量参、桃仁和外伤药。
“常山远,从省中跋涉,一定辛苦,他要些补药,应该的。”离云很认真,锦锦只好逗他:“你这样为息再着想,不如去讨好他,一定得他欢心。”
她不会被蒙蔽。
如果一切都在掌握,息再怎幺可能辛苦赶路?区区下国之行,他带几个从官,山水同车,夙夜游玩,也能到达——赵国不是被攻下?
锦锦哄离云:“你给我三四个未使男。”
处子出入堂室,不会受阻,又很纯洁,什幺都直说。锦锦下判断,必须要听真话、见实事。
少年带到,她嘱咐他们:“你们接待常山郡的贵客最好,白天现身照顾,夜里适当地听候。”
男孩子扒墙角去了。她又让离云邀请那位担行李的人饮食沐浴,而自己则请息再身旁的小女子:锦锦怀疑息再,连带着怀疑他的身边人。
“息再何人,这种时候,不会近女色。女子不定是由男子假扮,高个子不定是什幺重员。小云与我分头去查。”
侯夫人与侯公子邀请,二位用人逾越接受,又羞怯又荣幸。
席间,锦锦注视该女子,偶然对上她的眼:半月一样的眼,眼尾与睫毛低,多情而媚,让人心驰。
锦锦不得不承认其容表胜过省中风物,是倾国的人。
等到沐浴时,她走出屏风,看到女体。
“侯夫人?”女子扶住兽首,另一只手拦胸,状似惊异。
浑圆的乳,纤细的腿和腰,示意她是女人。
锦锦以为自己失败,便沉思,闻到药味。
“你受伤?”
“不,其实,”女子忸怩,放下拦胸的手,去拦别的。
腰上的指印,两膝隐隐的青。两手拦不住,反而让锦锦有了注意。
她假作轻松,取来丝巾,为女子淋肩头:“是我错问。”
挫败的人无心洗澡,清洁以后,追问离云:“如何,小云觉得那男子像有秩者吗?”
离云摇头:“他连话都说不好,像个僮仆。”离云受锦锦调度,本来很不自在,没想遇到比他还不自在的人,两人吃饭洗澡,只是道歉。
少年们回来,同样无所收获。锦锦期望听到息再与心腹的言语,最终一句也没有,反而有脸红的少年报告别的:“在喘气吧,几夜几夜。”
锦锦仍不死心:“息再重计,也许故意声响。我,除非我亲眼所见。”
她的心事像被读走,第二天,正堂就有滚在一起的男女:息再赤裸上身,将宠爱者按进座位,两人依偎,动作,带出水声,放纵欢爱。
旁人尽数出逃,侍者、侯奴并一位失神的侯夫人在堂外,只能看到男子挺拔的肩背,往下是深衣,被扯成一面布,挡住最缠绵处。
“是醉了。”有人说。
“醉了也不能……”侯奴目瞪口呆,“息大人竟将我侯家当成寝处。”
沉重在人心。大家这回明白,赵国或许真的完了,人家已经不把这处的王侯当作王侯,以后公然在花园里上厕所,也不是不可能。
堂上有呻吟,大家一齐去看,又一齐掩面:男子肩上架了女子一只脚。男女更贴合了。
座位湿,坐榻也湿,用来当幕的衣服下滑,被息再扶住。他搂起身下人,要换一件外衣。堂下众人接踵,立刻去找华服,只有锦锦像石像,在原地看息再俊丽的侧脸,又看他把握的女子的小腿,还是狐疑,最终离去。
被按入座位时,文鸢惊异。
息再捏她下巴,看她的舌与齿,又解了腰带,敞开衽怀。
之前,他要来酒,铺满食案,抱着文鸢说畅饮,劝酒官一走,就倾杯在菜中,只留一小盅,洒到两人衣间,散出香味。
听说他失态,许多人来看热闹,还没入室,就闻到酒味:“这是喝醉了!”
息再清醒着,心思在室外,听到某人提出侯夫人种种,思考片刻,转首向文鸢。
“息大人,不,有太多人。”文鸢似乎明白息再所想,然而被他压在身下,只好搭他衣边。
“息大人。唔。”
息再掰开文鸢手掌,捏一根指,置于她口中。
文鸢含混地提醒:“有太多人。”她眼眶泛水,嘴唇也沾湿,自己咬自己手指,不愿含。
息再近了。她变得老实。
“息大人!”
“不说话。”警告一次。
他压她腕,让她吃了手指,搅动几次,又抽出。口水成丝,最终留在嘴角。
文鸢疾喘,有些委屈,擡头却见息再褪上衣,忙去看屏风,又去看帷幕。双耳在乱发间变色。
息再俯身,这次“不说话”像商量,让文鸢有申辩的余地:“好吧,我不说话,但息大人,已经足够了,如今郡中人都相信你来游玩——”息再环她的腰,脱去衣裙,推着她的湿指,抵入两腿之间。
文鸢轻呼,手被他把握,破开自己的身体。
“息大人!”她挣扎,被息再压得不能动弹。两人咫尺,她看到他眼中兴奋,却无关情欲,吓得咬唇,进而看到门外探头的侯夫人。
“常山郡不无智者。蠢的是魏侯,因其是女子而轻视她。”息再冷冷地笑。
他伏进文鸢发间:“并不难唉。”
息再大概在说夺取常山郡,亦或是别的什幺,然而在外人眼中,他微张嘴,伏动身体,溺于姿色,同时张放姿色,深陷情爱当中;遇身下的女子擡头,艳绝的两张脸,白色的齿,鲜红的舌尖,照面以后都不见,变成两蓬黑发,一退一进,至于纠结。
有人咽口水:“当成寝处。”
息再听见,抿嘴笑了,因目的达成而愉快,推文鸢的手加重,让她一下捅到极深处。
“息大人……”文鸢发颤,不停推他,已经晚了。
靠津液进出的指,被突至的体液湿透。动情的水从指隙喷出,淋了两人满掌,甚至溅到盖衣下摆。
文鸢羞耻至极,被自己的身体绞紧,抽不出手,无意咬破嘴,便咬着伤处摇头,仍然听息再的不说话,老实又可怜。
息再低头,给门外人看,或是用心安抚,亲了文鸢嘴角;手向下,分开她双腿,摸到她沾满热液的四指,扣住向外抽。
水一股一股地涌,顺着扣合的两手,流向一人的衣袖。
文鸢起伏胸脯,用口型说着“足够”,涎水与血液在坠落。
息再只是看,于无声中听到臆动。
“啊!”突然的回送吓文鸢一跳。她尚且不知怎幺回事,身体先有反应,又喷水了。
息再松开四指,握住她腕,拽出又推进,带文鸢玩她的身体。
她手小,在肉与水间来去,不会伤到自己;但他手大,送她来去,以骨节碰柔软的入口,让她呻吟。
“息大人,息大人。”断断续续的哀求,变成低声哭泣。息再捉起文鸢一条腿,架在肩上时,她终于尖叫着哭了,身下第几次泛潮,还有失禁的水,让位子与坐榻都成深色。
湿衣滑落,文鸢于恍惚间,看到堂外人的脸:都很好奇,都很绝望。
息再扶住衣服,她又什幺都看不见了,只能依靠他,从痉挛中平复。
身下还在吐水,还有未拔的手指,她实在无力,埋进息再胸膛:“息大人,我不愿,不愿,我说好帮你,可你不能……”
她抹眼睛,低声叫“兄长”。
息再余光在看锦锦,知道这女子短时内不能有什幺说法,见她走远,这才沉下目光,以唇覆盖唇,吃下文鸢的“兄长”。
“有劳你,文鸢公主。”他抓她手臂,拔出她手指,用下人送来的华服为她擦拭。
湿了两三件以后,他抱她回榻处。
臧复正在用药,接了文鸢,有些无措。
“参煮给她,桃仁给你。快点养伤。”
如锦锦所想,实际上,息再一行是从西平道艰难入赵、直达常山,而并非对外称说的“做客游玩”,为此三人浑身赶路伤,不得不用补品。
赵国全境仍在赵王治下,如铁石牢固,想要取得,依当下的力量,还需佐之以非常手段,并一定的时间……
息再在床上休息,思考常山军规模,偶见臧复扶正文鸢的背,准备喂药,却因不灵巧,很快弄洒。两人慌乱着。
他皱眉,最后还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