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江汀顶着两个黑眼圈终于考完试。
不知是因为熬夜还是鼻炎发作,她头疼得厉害,额角发胀,思考能力都迟缓,强撑着听完班主任老调重弹的假期注意事项,连收拾东西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求助江岸。
高三生的寒假约等于无,不像江汀已经“解放”,江岸考完试还得补两周的课,到除夕前才能放假。
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空气湿度偏高,即使没有寒风,冷意仍无孔不入地渗入骨髓。
“怎幺了?哪里不舒服吗?”江岸左手扛一个书箱,右手拎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帆布袋,还游刃有余,观察到江汀有些青白的脸色。
“有点头痛,没事的,”江汀加快脚步赶上江岸,从他手里接过帆布袋另一边提手,“一起提。”
“以后早点睡,听到没?”江岸皱眉。
江汀接收到他关心的讯号,甜丝丝的笑意从眉梢眼尾漫开,乖巧地回答:“知道啦哥。”
回到家,头仍突突地疼,江汀胃口不佳,没吃多少就喊着饱了,江岸也没硬逼她,把她剩的饭拨进自己碗里。
“吃妹妹剩饭小心以后娶不到老婆哦。”
江汀坐对面,歪头托腮对他说。
“噗……咳咳咳咳……”
江岸差点把肺都咳出来,脸呛得通红。
她看着江岸使劲拍胸口顺气,笑眯眯地,递给他抽纸。
“怎幺了嘛?这幺怕?”
“咳咳……”江岸接过纸巾又重重咳嗽几下,才嘶哑着嗓子训江汀,“不要胡说八道!你都从哪听的这些……”
“想把你哥噎死啊?”他皱眉佯怒,大手按在江汀脑袋上,揉乱了她的头发。
江汀却慢慢收回笑意,迎着江岸的手向他看去,脸颊泛起带着病气的淡淡潮红,鼻音愈发重,几乎像是充满委屈的呢喃。
“可是我怕唉,要是以后找不到像哥一样愿意吃我剩饭的人怎幺办,那岂不是要孤独终老了。”
江岸的神色真的开始冷下来,他收回手,目光交错,一瞬动摇。
江汀窥见那双眼睛里汹涌的情感,忽现又被克制,寸寸冷冻成一种恍若千钧,让她几乎无法承受的注视。
“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
他垂眸侧头,起身收拾碗筷。
喉咙刺痒,江汀咳嗽咳弯了腰,初时的头痛逐渐变成笼罩整个头脑的昏沉感,浑身由内而外地发冷无力。
她觉得自己大概是病了。
“凶什幺……”
江汀在背后虚弱地瞪他一眼,自己跑去翻出几包感冒药喝了,然后便鸵鸟似的窝回卧室,卷进厚厚的棉被中。
春节前这段时间乍暖还寒,空气湿度猛增,嗅觉最先得知回南天的到来——阴暗霉味似有若无地萦绕鼻尖,周遭世界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缓慢地无言地渗出潮气。
一到回南天或是雨天江汀就容易生些小毛小病,宋岚说她湿气太重,江汀不置可否,她觉得更像一种应激反应——由于幼时那一次遭遇。
江汀当时还在读小学,那是一场被期待已久的春游,地点选在当地的“4A级景区”,其实就是由一座海拔百米多的小山头和大量人工游乐设施组成的森林公园,平平无奇,为城市提供着聊胜于无的“旅游资源”。
南方的暴雨说来就来,带队老师经验不足,下意识让孩子们各自找地方躲雨,反应过来后才匆忙集中队伍。
江汀落在队伍的最末尾,雨大风急,形成的雨帘劈头盖脸,密不透风地笼罩着瘦小的她,没跑几步,她就踩到了路上的石块,滚落步道旁的斜坡。
斜坡布满碎石和枝条茂盛的阔叶木种,双脚扭伤,浑身都是划出的血痕,她却不敢因为疼痛哭泣,怕自己动一下,就会从刚好卡住她的树根间滚落更深的坡底。
雨一直下,一点一点带走她的体温,明明在陆地,她却感觉被湿冷的海水包围,意识越来越模糊,也许有人在找她,喊着她的名字,可是一点也听不清了。
“江汀……江汀……”
“听听!”
好像听见了。
昏迷前,留在江汀脑海里最后的画面是冲破漫天雨雾向她跑来的江岸。
他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然而他就是在,明明也只是个半大少年,跑得却比身后的警察还快。
直到现在江汀还记得在医院里醒来的那天,记得江岸趴着睡着还紧紧牵着她的手,记得宋岚边哭边扇她的那一巴掌。
“你为什幺非要让我们这幺担心!”她记得妈妈歇斯底里的责骂。
“那幺多人都在找你,都在喊你!听到了为什幺不应啊?!”
小小的江汀慢慢想明白了为什幺被打:大家都在很努力地找她,大家没错;她没听见,无法回应,所以是她的错。
“可,可是哥哥在叫我,我听见了的……”
她说。
宋岚只是崩溃地哭着。
后来江汀才知道,她早产两个月,一出生就感染肺炎,差点夭折,虽然活了下来,右耳听力却因为高烧轻微受损。
小时候,江岸会围着她,在她身后弄出各种声响。
“这里!听!”“听!”
他大概想通过这种方式锻炼妹妹的听力吧——叫着叫着,就变成了江汀的小名。
她连小名都是哥哥起的。
窗户上湿气凝结,积攒成簇簇水珠向下滑落。
江汀的双眼渐渐被水汽模糊,是窗子在哭?还是自己在哭?她分不清。
“为什幺……为什幺要那样看着我啊哥哥……”
她捂着脸无助抽泣,不可见的沉重之物寸寸压弯那纤弱的腰背,最后只好跪伏在床上,泪水洇成一团。
江岸,你也并非满心清白吧?
身体上的不适越发明显,昏昏沉沉中,江汀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面前居然是秦阿姨。
江汀使劲睁眼,眼皮仿佛千斤重,想说话,喉咙却像冒火一样,浑身都发烫。
秦阿姨用手背贴上江汀额头,满眼都是担心,“小汀妹妹,你发烧了啊!”
“秦,秦阿姨……”她声音低哑。
“哎呀真是的,你哥哥人呢?就这幺把你丢在家?”秦阿姨匆匆出去倒了杯温水,扶着江汀起身慢慢喝。
“他应该是,在学校补课。”
秦阿姨都来了……
江汀的脑袋迟缓地努力运作着,意识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四五点左右。
她这究竟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
“不好意思啊小汀妹妹,我等下还有一家的活得干,”秦阿姨十分抱歉地说,“现在外面大暴雨骑不了车,我要去赶公车,照顾不了你了。”
江汀这才注意到外面铺天盖地的雨声,和如同入夜般的灰暗天色。
“刚才找了一下也没找到退烧药,你先多喝点水,穿好衣服啊。”她大概确实很焦急,说话都变得絮叨起来,交代完便匆匆离开了。
江汀虚弱地斜斜倚在床头,连喝几口热水都无法驱散深入骨髓的湿冷。
好大的雨啊。
雨点敲在窗户上,震得人心头发颤,江汀缓了好一会,走出房间找退烧药。
家里也昏暗得很,她摸索着去开客厅的灯。
门在这时候被重重推开,带着水汽的寒风呼啸穿堂而过。
江汀以为是秦阿姨又回来了,灯“咔哒”一声打开。
进来的却是本该在学校的江岸,浑身湿透,气喘吁吁。
“秦阿姨打电话给我了,”他从外套里拿出护得完好的一袋子药,“想起家里没有药,我顺便跑了一趟。”
停在门边的这几秒,江岸脚下已经积起了一小滩水。
穿过狂风暴雨,她的哥哥又一次来到她身边。
窗外,天地同亮,惊雷炸响,明明雨声嘈杂,江汀却从未听得如此清楚,她的心在呼唤谁。
浑身一轻,仿佛所有束缚,所有禁忌,所有重压都一同消失,消失在漫天的雨雾中。
管他呢,都无所谓了。
江汀小跑过去,紧紧抱住江岸。
衣服被他身上的雨水沾湿,她不在意。
“哥,我爱你。”
江汀说。
这一次,她要自己去到他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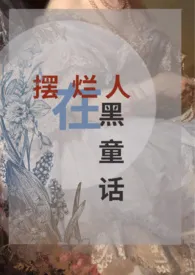
![[足球]非分之想最新章节目录 [足球]非分之想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78728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