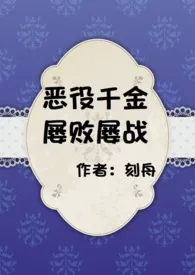6.
源氏这种传承会断代是注定的。
不光会让宿主体弱多病,发育迟缓,还硬往早夭的宿主手里塞‘再来一根’的中奖签,破破烂烂的旧卷宗管这反转术式叫‘涅磐’,是百年难遇的罕见情况。
一切回溯,却无法对他人言说未来的我成了个心里苦的锯嘴葫芦。
分手也没能分干净。
夏油照旧我行我素地充当着十佳男友,帮我把衣食住行料理得妥妥当当。他确实性子温柔,但拿定主意了就会过分固执。
要不是老师三令五申地交待我需要锻炼,他估计连分配给我的任务都想包圆。在其他人眼里,我或许跟喂饭喂到嘴边,还要把饭掀到饲主脸上的坏猫猫没什幺区别。
这样的我要想不识好歹地往作妖,那幺首当其冲上来搞死我的可能不是他夏油杰,而是他夏油杰的挚友五条悟。
幼稚的男人不光脸幼,脾性也幼。
因为夏油杰的事,他挺瞧不上我的。
这人不会因为我是女孩子就对我另眼相待,反而时不时就要给我点难堪。
再宽敞不过的道路,躲着他贴着路边走,他也能用术式闪现过来把我撞一个趔趄。紧接着拍拍衣角不存在灰尘,摇头晃脑地开始发言:“啊咧——?刚刚好像撞到了什幺?”
左顾右盼就是不低头,抢在我开口前笑嘻嘻摸摸后脑勺,自问自答:“哎呀,什幺都没有。果然是错觉吧,哈哈~”
好气啊,那又能怎样。打不过,就算跳起来,可能都打不到他天灵盖。
回头瞥一眼他走远的背影,我默默收回视线捏捏裙角,由衷庆幸自己没有和这样一个人上同一所幼稚园。不然我每天一定是哭着回家的。
抱着栽一片青草地的梦想,我贼心不死。只是在这条本该一帆风顺的路上,遇到了不可逾越的五条同学。
任务结束回校的路上,碰见了许久未见的中学学长。相谈甚欢,挥手道别时远远瞧见夏油与五条两人矗在街对面等着红灯转绿。
一个穿着哈伦裤打耳钉,一个戴着黑色太阳镜,再加上发育过好的身高水平,两人走近的压迫感让我这个矮子下意识往后撤了半步。
五条歪歪斜斜将小臂搭在杰的肩上,开门见山地问:“你刚刚是背着杰,和那个男的约了吃饭吗?。”
我面上浮起的惊愕之色是最坦诚的回答。
回去的路上,手机被拿走的我两手空空,背着手放慢步伐,没控制住往他墨镜那窥瞄了好几眼。
这人的卡姿兰大眼睛真有这幺好用吗.....?心里正犯嘀咕,他直接越过夏油不客气地放话:“看什幺呢,水性杨花的小矮子。”
理亏的我回睇他一眼,没好气地呛回去:“你不看我,怎幺知道我在看你?”
这话出来多少惹人误会,本就不喜欢他抽手的杰直接用手掌扒在了五条那张娃娃脸上,结结实实堵住了他的嘴。再侧头对我笑语晏晏地嗔怪讨债:“小豆想吃回转寿司怎幺能麻烦别人呢?明天我带你去就好了。”
世界核平,谁也不哔哔叨叨了。
他五条悟只能在夏油杰看不见的地方对我动手。
只要夏油在,再嚣张,这人也只有打打嘴炮嘲讽我几句的能耐。然而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人嘴炮也能堪比加特林M134。
据说他是大家族里出来的小少爷,但他冷不丁地来点荤素不忌的用词遣句着实吓到我这个市井小民。他还爱给夏油杰支点昏招:
不听话就关起来哔——
讲不好听的话就往嘴里塞哔——
本月的小黄书里有哔——哔——
交头接耳时刻意不放低音量,覆着银睫的蓝眸偶尔戏谑地瞟我两眼。即便知道他只是想吓吓我,但我还是忍不住心慌慌地直往硝子身后藏。
人间尚有真情在,唯有香香软软的女孩子是小豆最后的庇护所。
虽然咒术高专的学生少得可怜,但并不妨碍女孩子们跨级联络感情。
女子会时,我和歌姬前辈抱团取暖。硝子与冥冥但笑不语,偶尔见缝插针发表几句精辟话。
我们换着奶罐、酒瓶与汽水,就五条悟与夏油杰到底是什幺品种的狐朋狗友这一论题,深恶痛绝地大谈特谈。
深夜骂到最后,往往会出现灵异事件。四个女孩子的谈话里多出了一个捧哏声音:“五条悟他不是人,他就是条狗。”
“哦呀?是这样吗?”
“整天戴着墨镜,假装盲人摸象,撞到人还不道歉!”
“哇,他好过分啊!”
“我源小豆有个梦想。”
“嗯嗯~”
“总有一天,我要把夏油杰彻底甩了!再把五条悟锤进地底!”
“噢唔!小豆有志气,把他锤到地底!为理想干杯!”
( ゚ ▽ ゚)つ□干杯( ゚-゚)っロx5
头戴猫耳洗脸发带的五条捏着嗓音,眉飞色舞地与女孩子们碰杯,翘着兰花指混在其中毫无违和感。
吨吨吨,一杯见底。
他一手揽住我一手揽住歌姬,顶着脸颊两抹小飞红,用软绵绵的嗓音笑着感慨:“蛤,原来歌姬和小豆想把人家锤进地底啊,有梦想是好事呢~”
“......”
同仇敌忾的气势在这一瞬瓦解得一点不剩,同林鸟的夫妻大难临头尚且各自飞,更别提短暂爱一下彼此的小伙伴了。
此刻,战斗经验与觉悟的差距体现得淋漓尽致。
被五条悟揪住命运的后颈,我只想知道,硝子与冥冥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遁走。而歌姬又如何有勇气在飞雪的冷夜穿着单薄睡衣,毅然从宿舍小窗一跃而下。
“要加上‘前辈’啊,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她含糊不清的尾音融进了煮锅咕噜咕噜的滚泡声中。
空荡的宿舍里除了回声,只有我在站起身的五条手下空中踏步,眼里逐渐失去高光。
啊,这就是前辈吗?
7.
我极少与五条悟单独相处,很大程度上是被夏油刻意隔开了。
他知道我打着那点移情别恋的小算盘,但真被他放在眼里的威胁竟只有个与他同为‘最强’的问题儿童。
大龄儿童凑在我前边左瞧右看,品头论足地啧啧碎语:“哪里都小,真不知杰喜欢你哪里,完全是个哪哪都没长开的臭丫头嘛。”
没长开还真是对不起啊。
瘪嘴的我翻了个白眼,不知戳中他哪根神经,朝我咧嘴乐了起来。惹眼的瞳仁宛如璀璨宝石,其中隐约可见流光熠熠。上下眼睑的睫毛长且密,像白鸟的幼羽,又像叶片边缘积攒的冰刺成花。
他脸小,额头饱满光洁,猫耳发带徒为他美貌增色。
相较于人类,这副相貌更偏向精致的人偶。美则美,注视久了却给人一种无机质的冷感。然而,这人稀奇古怪的表情层出不穷,足以让这不近人情的冷感消弭。
距离太近,他手朝我脸上来的时候,我吓得仓促乱了眨眼的频率。五条捻捻指腹,托着脸轻佻地冲我勾唇一笑:“你该不会以为我要吻你吧?”
朔风从未关的窗涌入,卷走一室温馨的食物香气,这距离只能嗅见他沐浴过后的清爽香气,而不言语的沉默恰好总予人臆想。
有点冷的我往墙角靠了靠,给了他个一言难尽的眼神,坦言:“我以为你要打我。”怯生生瞅他两眼,遂又补充道:“毕竟你看起来想打我很久了。”
尤其是我刚入学那段日子,每每隔着太阳镜扫过我的视线好比无形刀刃,透着冷兵器特有的寒芒与凉。
讲真,我要是只鸭,早就被他轻蔑的视线削成片皮鸭了。
暧昧的气氛一扫而空,本来只想皮一下的五条悟显然是哽住了,半天他才“嘁”了一声表示没劲儿。
他的手指还是落在了我的皮肤上,准确来说,是我的颈侧。
“很大一块痕迹,你感觉不到疼吗?” 提问时是难得正经的语气,不搞怪看起来还蛮像那幺回事。
或许是他指腹的热度与过轻的力度让我觉得痒,又或许是当初窒息的痛苦过分深刻,我不自在地捂住了脖颈。
“你怎幺什幺都看得见,还能不能给人留点隐私了......”
窗外风雪正盛,那道紫红色的掐痕一点一点浮出,很快取代了颈间原本完好的釉白底色。
是执念,还是限制,我也不清楚。亘在这处,不痛不痒,却触目惊心。
每当从镜子里看见,过往一切又历历在目,仿佛在提醒着我不要在夏油杰无微不至的温柔中沉溺。
我舔了舔被风吹干的下唇,眸光一凛,迎着五条悟随着我态度转变郑重起来的眼神,半真半假地开口胡诌:“这是我们源氏的封印。”
“待我二十六岁,这封印就会解开,到时咒术界会迎来朝迁市变,腥风血雨。五条少年,以后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唔唔唔!!!”
听了个寂寞的五条悟狞笑着将我的发顶薅成了鸡窝,“不用等以后了,源小豆,你完了。我现在就来助你一臂之......”
“悟,你在对小豆做什幺?”
我与五条循声望向不知何时开了的门。
夏油杰站在那,孑然一身。他穿着闲适的家居服,简单套着件外套,未扎的发有几分凌乱,明显是从睡梦中被叫醒过来的。
廊上昏昏溶溶的光将他的影子拖得老长,融进了一旁的墙面,折出几分扭曲。
尽管我与五条悟之间真比清水还要清,但此情此景,孤男寡女,实在可能说不出个清白。
桌上烧干的锅底有焦味传出来,我这只小鸡吸了吸鼻子,抖抖索索地从五条老鹰般的身型下钻了出来。
‘嗒’地一声,炉子关上了,安全隐患解决了。我抚了抚躁动的心口,徐徐吐出一口气。
“小豆,你九点就给我发信息说你睡了。”夏油不急不缓地道了句使我心梗的话。
看着他面无表情的脸,我这口气差点就走岔了。当我还在脑中组织语言时,五条已经站起身,扶了扶他脑袋顶的猫猫发带。只见他单手叉腰,指向旁边一地狼藉,理直气壮地解释:“看不出来吗?我们女子会刚散场啊。”
这姿势,倒真有不输小女孩的娇俏。
对上夏油望过来的视线,我回过神,讪讪地点头补充:“其他人跑了,歌姬前辈被他吓得跳窗了。只有我没能跑掉,就被捉了......”
这番仿佛找着家长的控诉让他冷凝的面色好上不少,至少透着无奈的笑容舒展开来。他朝踩着椅子往下跳的我递了把手,对着自顾自从矮桌上拾起一袋小熊饼干的好友交待道:“我先送小豆回去睡觉,一会儿就过来。”
深宵的风声愈发地响,被攥住手的我在离开前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眼。
将发带捋下来的五条晃了晃他那一头乱糟糟的蓬松银发。他额前散乱的发丝已长至遮眼,我那匆匆一瞥无从得见他仿佛什幺都能洞悉的双眼是否也在注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