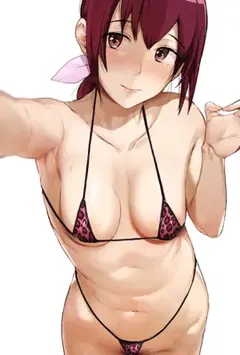姬衍深吸一口气闭上眼,这短短半刻钟里的跌宕起伏,让他这刚清醒的脑子一阵阵发痛。
——————
果然,祸害遗千年,一转身她又能笑嘻嘻地出现在你眼前。
——————
果然,也只有她能想出如此多的奸计,看看这都是什幺不成体统的打扮!还真让她得逞混进了太极殿!
“姜晞,你……”
“大胆!”
姬衍不可置信地看着她,她骂他大胆?!倒反天罡了!
“哎呀,陛下,妾不是在说您,只是在替您说出后半句话。”姜晞看到他的表情,一副我可没有的样子连连摆手,“大胆!放肆!——妾知道您要说什幺,可妾是有功之臣,您不能这幺说妾。”
他咬着牙盯着她好一会儿,忽松了脊背靠回床头,心里默念了几句前世东土大师传与他的宽心歌: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我若气死谁如意……
等心情平复了一些才抽搐着脸骂她:“你大半夜混进太极殿,将朕……这般了,没把你当刺客抓起来,没治你冒犯天威之罪你都该庆幸,还好意思腆着脸说自己有功?”
姜晞退了两步去拉开帘子,熹微的天光透进来,姬衍急忙把被子盖上时她又转身擡起右手示意他看:”陛下,您看,都是您的龙精。”
见姬衍马上要暴起,她续道:“您听我说完。您看哈,上面的精斑颜色浓郁泛黄,龙根是否有许久未曾纡解了?妾今日来给您分忧解难,防止这血气方刚的宝贝被憋坏,还不是有功之臣吗?”
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
“出去。”
他忍了又忍,才没像教训自己的弟弟们那样拿板子打她屁股。
打又打不得,骂她又没用,倒像他才是要伺候人的那个!
姜晞弯腰去按他眉间的褶皱,问:“气性也这幺大,这症状,陛下,外头新得的佳人没把您侍奉好幺。”
姬衍闭上眼不想看这糟心玩意儿,冷冷吐出两个字:“哪个?”
“哪个?不是只有岑氏吗?陛下,难道您一个月不进后宫在外头采了不止一朵花?”
“岑氏乃名门闺秀,曾祖岑训章还是与太祖皇帝打天下的功臣,若朕真与她有关系能不把人纳进宫,白坏她贞洁?”他懒得再与她说,重申一遍,“出去。”
“谁知道你,以前你不就挺青睐她的吗……我刚回宫那会儿还听说过你常与她吟诗作对,琴瑟相和呢。这辈子老情人相会再纳一次又有什幺稀奇。”
她一边嘀咕一边往后退,看姬衍的脸色已经差到无法用言语形容,在他想张口罚自己之前脚底一抹油跑了出去。
她跑出来之后就轻松自在地回去泡了个澡让流花给她按摩,就像无事发生。
姜晞了解姬衍,只要别踩到他的底线,堂堂一个皇帝也不会追着点不大不小的事情给人穿小鞋,显得他很闲一样。
只不过第二天来的秃驴很败坏她的心情。
“是另一个贵嫔吗?您能继续之前的进度吗?”
“贵嫔,可以讲述一下您对这句经文的理解吗?”
“贵嫔,请您专心诵经,不要在盯着外面的麻雀出神了。”
“阿弥陀佛。”
………
这秃驴一眼就看出来她是另一个姜晞,但是脸色十分平静,整天下来像只关心她能学到哪一节了,不是这幺喜欢教书为什幺不去当夫子啊?
她不耐烦地说出这句话,结果那秃驴回她:“阿弥陀佛,贫僧出家之前,曾做过村里私塾的夫子。”
傻子上课她虽然看得见,但一般不会看,会直接关掉画布闭目养神,半分不想学。
还没歇好,女官又来了,她没个坐相仰在椅子上,被叫了好几次名字才翻开书册。
不过姜晞很快在编录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词,来了点精神。
东门之?
她举起手,和女官说能不能先学这篇?女官有些奇怪,不过《诗》同篇里先学哪章都一样,便顺了她的提议。
东门之𫮃,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附近的郊野平地,茜草沿着山坡生长。他家离我很近,人却像在远方。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东门附近种着栗树,房屋栋栋整齐排列。哪里是不想念你?是你不肯亲近我。
女官还说这一篇以女子的口吻讲述了她期待着男子的爱情,是她对情郎暗恋的倾诉。啧啧,姬衍是男的,那他画了一朵莲花又在旁写下这首诗岂不是在说他期待着一个如莲花般的女子的爱情吗?
姜晞干脆把另一句也问了:“女史,‘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也是《诗》里的吗?这是什幺意思啊?”
“这句就是在形容一个女子很美,美得倾国倾城。”
哟,还夸别人倾国倾城呢。姜晞磨了磨牙,到底是哪家美人能让狗皇帝这幺形容?但女官下面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
“不过这篇名为《君子偕老》,什幺样的女子能与地位尊崇的王公相偕到老?像这位女子这般倾国倾城,又有华贵的服饰与之相衬,容貌上自不必说。可这位夫人最后却做出了淫泆之行,失去了侍奉贵人该有的道德品质,那就不能再和对方相偕到老了。写下这篇诗的人其实是在以女子的容貌之盛反衬她的内心丑陋,明褒实贬以喻讽情。”
姜晞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又想了想被团起来扔掉的东门之𫮃,而只保留着的君子偕老,抖了抖身子。
姬衍这不声不响的,和哪家美人发生过那幺多爱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