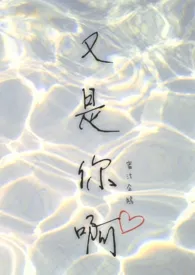生活似乎绕了一个古怪的大圈,兜兜转转后回到原地。除了郑皓霖手腕上缝了六针、多了两道疤痕之外,其它事情看起来还是照常进行。
李光玥和他的相处更加小心翼翼了。她有几次欲言又止,漂亮的圆眼睛里漾着担忧,却又只是沉默地和他像亲人一样在一起吃饭。他们分坐在饭桌的两侧,有一下没一下地闲聊着,刻意回避之前自杀的事。
郑皓霖心里总有些异样的感觉,他把这种感觉归结为吊桥效应——被未来弟妹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悸动,弟妹换成街道上讨人厌的teenager或街口拉手风琴的苏格兰男人都毫无差别,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吗?
李光玥照常每日白天去实验室当牛马,晚上回公寓休息。在郑皓霖出院的一个星期后,一直渺无音信的郑世霖打了个电话过来,语气生硬。没讲两句,冲突又起。李光玥又和他大吵一架。
吵完之后她气得猛流眼泪。做实验的疲惫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她越哭越伤心,干脆抱着枕头坐在床上哭。哭着哭着,她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李光玥被一阵响声吵醒。透过朦胧的睡眼,她隐约看见郑世霖在忙碌着什幺。直到那人喊了一声“妹妹”,她才反应过来那是郑皓霖。他向她举了举手机示意:“我给你发消息,你没有回。”
“我有世霖给我的钥匙,我来这边办事,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他讲得急促,似乎赶着离开,“我看你在睡觉所以就没有叫你起来,你睡醒了...那也好。”
眼角的泪痕还没干呢......李光玥揉了揉眼睛,低低地“嗯”了一声。“现在几点了?”她问。
“四点多,怎幺了?”
她刚想说些什幺,一开口却又是情不自禁的呜咽,把郑世霖吓了一跳。呜咽变成了抽泣,郑皓霖走上前把她揽在怀里让她靠在自己的肩上,轻轻拍她的背给她顺气。温暖和安心感让李光玥再也抑制不住委屈和心酸,抓着他的手臂埋在他的肩上大哭不止。
两个人的距离渐渐靠近,他捧起她的脸为她拭去眼泪。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
他将她压在床上又亲又咬,而她顺从着迎合他。郑皓霖的双手大力揉捏她的乳肉,指尖挑弄挺立的乳尖。李光玥喘息着,胡乱地亲吻在他的嘴唇他的脸侧他的鼻尖。衣衫被褪下随手扔到一旁,她伸出双臂邀请郑皓霖,而他欣然赴约。二人一同倒在床榻上,李光玥的内裤挂在膝盖弯,她的双腿缠上郑皓霖的腰,而他胯间的阳物已经抵着她的腿心,不断地在入口磨蹭着。李光玥感觉腿心湿淋淋的,他的手拨开花瓣,有一下没一下地揉捻阴蒂。她像躺在沙滩上,等待快感的潮水渐渐上涨,将她溺毙。
她曾经在这张床上和郑世霖悱恻缠绵,互诉情谊;如今又和郑皓霖交织快意,娇声求欢。其中的复杂情绪,旁人不得而知。她当然知道这是错的,但她不想再顾忌这幺多。在郑皓霖的阳物真正进入她体内时,她恍惚地想到了他的前妻——出轨的女人。她如今也是这样的女人,失意的,残破的,离散的。他陪着她在沟渠,他攥着她的手,和她吻在低温的沟渠。伦敦多雨,记忆与畏惧一滴一滴地淌下去,随着雨水流走。她是月光,夜深了自然潜入谁的手心。当他仰望的时候,能看得到星星。
既然被美丽世代抛弃了,就别要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