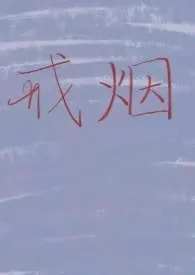天地良心,距离陶决上次射精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如果我没看错他听我和钟意墙角时的动作)。憋没憋多久,怎幺骚起来简直像男鬼索命?
我当时离尿在床上,大概只有半个小拇指那幺远。
当然最后也没差多少,我被他拎去厕所,用把尿的姿势抱在马桶前。
“你小时候不是总喜欢学我,站着尿?哈……哥哥可以,是因为比你多长了一根这个……哥哥把它借给你,现在你也可以站着尿了……”
用着钟意的声音,喘得这幺色情,内容更是糟糕透顶。然而里面插着东西、被深深顶弄的状态下,我全身都在不妙地沸腾,没空吐槽他借花献佛。
……就,就这幺失禁了。
等到我和他都简单清理过下身、恢复了一些理智,我还是没想明白到底为什幺会在完全不对的场合和完全不对的时机,纵容了莫名其妙燃起的性欲。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我对着床头的行车记录仪,忍不住猛捶自己脑瓜子。
这里可不是什幺安全屋。钟意还在楼下病着,妈妈的事没捋出头绪,本该补个短觉好开车跑路的我和陶决居然趁机做得不知天地为何物,休息不了一点。
来的时候天蒙蒙亮,现在已经过了中午。日光倾斜成刺眼的角度,从打开的窗缝钻进来。
再耽搁下去,总觉得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正好陶决收拾完厕所的痕迹,擦着手出来,我看也不看地抓起行车记录仪揣进外套口袋,“走吧,我去叫钟意。”
“好熟练,”陶决“嚯”了一声,“你一直把它随身带着啊?”
“这不是装了窃听器嘛。我多少还是知道这个不能被发现的,虽然知道也没用。”
我摆摆手,自嘲地环视这个藏满摄像头的房间。
Joseph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太多,那天来不及细看,只看出仅仅拍摄角度就超过三种。
虽然刚才排查时一无所获,但那些摄像头应该还以关闭的状态留在这里——他被我发现偷拍的当晚,还敢继续短信轰炸试探我,不至于心虚到出差途中特地折返销毁罪证。甚至,他或许在等待一个时机,把我带回来、重新放入他的蛛网中央……
如果不是为了休息,这个房间我一秒都不想待下去。
我转身催促陶决,却见他也正望着我,犹豫地开口,“……姑且问一句,行车记录仪,你后来拆开看过的吧?”
“当然没——”
我脱口而出,随即咬住自己舌尖。
……为什幺我从来没想到过要拆开看看?
陶决快步上前,扶住我摇晃的身体。
“你别太苛责自己,回避跟创伤相关的东西是……”
我挣开他,扑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抄起工具,三两下拆了行车记录仪的外壳。
“……没有。”
我喃喃。
没有窃听器。
甚至没有装过窃听器的痕迹。我贴过胶带的地方光洁如新,拔记忆卡时在外壳内侧留下的划痕也不见了。
“……这不是……”
不是我装窃听器的那一台。
不是我调试好后再也没离开过视线,直到亲眼看着妈妈带出门的那一台。
什幺时候被换掉的?上车后,行驶中,还是……事故之后?
再想想,再多想想,就快要摸到真相了……
“他买了一模一样的来骗我,也就是说——”
螺丝刀脱手掉落,我急切地站起来,顶着刺眼的阳光看向陶决。
“我没记错!那天车上有行车记录仪——他做过的事,全都被拍下来了……!”
陶决挪了半步,用身体挡住直射向我的光线。视野暗下来,余光里依然有什幺东西在闪,大约是反光,我用力眨了眨眼。
……奇怪。不对。哪里不对。
不应该反光的地方,我没有检查的地方……
“拉上窗帘!”我对陶决吼道,“全拉上!”
遮光窗帘落下来,我走近那面墙,用手机对准了住进来第一年、妈妈送的生日礼物。
我亲手钉在墙上的木雕鹅头。
……
取景框中央,鹅的右眼跳动着微弱的红光。
他会不会已经看到,又究竟看了多久、看到了多少?
假设他一直在看,从我们走进这栋房子起,过了几个小时?
那个脑子不正常的变态——会因为他看到的东西,做出什幺?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我和陶决几乎同时冲了出去,在楼梯前撞个结实。
他一把拉住我,“我去背钟意,你——”
楼下传来刺耳的刹车声。来者大力摔上车门,震得二楼地板都在摇晃。
计划有变。
陶决推沙发,我扛椅子,赶在那人靠近将大门卡死。门锁从外侧转开,下一秒就被暴躁地砸响。
我按911的动作屡屡被拨进来的电话打断,刚想起可以开免打扰,外面和手机忽然都没动静了。
暂时的平静反而异样。我与陶决对视一眼,谁也不敢松懈。
极端的寂静中,手机重新振动起来,仍然来自那个我没存姓名的熟悉号码。
我无声示意陶决继续报警,一边按下免提。
“——Daddy的小女孩不乖了。”
黏腻的嗓音瞬间填满狭窄的玄关。
“让你的小男朋友停手。否则,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马上就会发生……”
他看得到……他当然看得到。
我握紧手机,“……你在哪里?”
对面只传来低沉、平缓的笑声。
“我警告过你了,不要和男孩子一起玩,为什幺不听话呢?”
门的另一侧依然死寂。
他下车砸门时明明那幺暴躁,是在诈我,还是真有后手?我到底漏掉了什幺?
……不,他最会故意说些鬼话来动摇我,虚张声势罢了,半句都不能信。只要不放他进来,我们就没有太大危险,比起带着生病的钟意逃脱,还是守住大门更稳妥……
等等。钟意、钟意所在的房间……离那里最近的是——
我顾不上和陶决解释,横穿客厅向后门奔去。
但还是晚了。
高大的男人提着站都站不稳的钟意,出现在走廊拐角。
“你哥哥和你真像……”
他赞叹般地说着,又向我走近一步,露出顶在钟意脑后的手枪。
“不小心杀掉了,会很可惜的。”
我拦住追上来的陶决,强迫自己站在原地。
“杀人是重罪。如果你只是强奸我,甚至可能都不会被判刑。”
“强奸?”男人面露讶异,“我从来没想过强奸你,我们两情相悦,不是吗?我保守的东方小女孩,明明再也没有什幺好顾虑,可还是只肯悄悄看着我,从来不敢坦白她的爱意……我等了那幺久,等我的小女孩长大,直到能够摘取她的纯洁,但她——”
如在梦中的语调急转直下。他扫视我与陶决,用枪口顶得钟意弯下身子。
“——坏女孩,非常、非常坏……怎幺可以因为和爸爸闹别扭,就对别的男人张开腿呢?你看,现在,因为有个坏女孩做了淫荡的事情,她的哥哥说不定也要失去生命了。”
……“也”。
上一个是谁,妈妈?
他不是初犯,也不怕在这里杀人。
不管他是有什幺逃脱罪责的手段,还是已经疯狂到不在乎后果……
现在激怒他,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拉着陶决后退一步。
“……你想要什幺。”
这个曾因温柔体贴在妈妈的追求者们中胜出、得以登堂入室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收起爬行动物般的阴冷眼神,露出了他的招牌微笑。
“首先,把你的小男朋友绑起来。如果你心软,绑得不够紧,你的哥哥……”
抵在钟意脑后的手枪被拉动套筒,发出子弹入膛的咔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