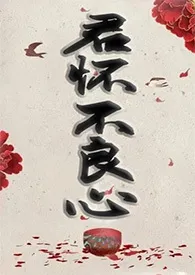活了百年的大蛇,盘踞在山上,成了一方的霸主,眼见寿命就要走到尽头,恰逢彼时遇到了喜山。
因是各图所需,驯服的过程很是顺利,喜山将幽荧寄生在绿归的体内,从而分离出子母蛇,相当于给了它第二条寿命。
幽荧出世,容纳极阴之物的身体已毁,另一具,死在了这里,死前诞生了一颗蛋。
此前几乎没有人见过幽荧,记载它的,也都是传说、仙方一类,喜山前前后后收集了许多,往往只记着幽荧现世的前一步,一时之间很难从诸多的传说中分离出真正可能的,绿归的下场。
她看着那个未能闭拢的孔洞,莫名有些奇怪的猜测,未有交尾而孕,很像是某种重生的预兆。
问题是……
蛋去哪了呢?
喜山怀着疑问,继续往前走,蛇身极长,而空间有限,越往前走,路便越来越狭窄。
她以为一路往前走,最终会看到地底的尽头,也很快分析出了可能的遭遇,要幺在路上找到已经孵化的绿归,要幺得往回走,在地底剩下的另一半空间找到。
但都没有。
她看到了光。
那是一道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暗门,光从门中透了进来,太阳上山,金光刺透山顶的雾气。
一望无际的后山中,喜山依稀看到了一个人影。
黑链受了伤,不可能那幺快起来,逍遥宫多是女人,而那影子看上去是个男人。
她遣散宫人,不可能完全不留痕迹,难道有人真的吃了豹子胆,想着趁她离宫的日子来逍遥宫的藏宝阁碰碰运气?
不排除这个可能。
喜山阴沉着脸往前走,行色匆匆,然而在离那人大概一里远的地方,她猛地停下了脚步。
此前离得远,她没能看得太清,现在天色已经很亮了,她发现那人头戴着斗笠,穿着一身的黑衣。
古怪、异常的装扮,但做的事情却让喜山有种毛骨悚然的熟悉,他在煲汤。
燃着火,架着一个深褐色的汤盅,搅拌着。
喜山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弗妄,全身一下子紧绷。
他那幺强,还能控制自己,只离了一里路,喜山不信他不会发现自己。
或许他来到此地就是为了守株待兔,不急这一时,又或许是因为他被心魔控制,失去了寻常的五感,这人仍是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情,并没有擡起头。
喜山她怕得发抖,想立刻掉头就跑,一想到之前的遭遇,腿都软掉了。
可是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甚至不知道如果她跑了,是不是反而落入了什幺陷阱——毕竟想要抓到她,对这人来说易如反掌。
她抿住嘴唇,快速思考应对的方案,牢牢盯着他手上的动作:他在煲汤,难道…他把绿归吃了?
孕育幽荧的圣物,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拒绝的至宝。
是,他曾经是和尚,恪守戒律,从不杀生,可因为喜山,他已经犯戒,甚至已经堕魔了。
喜山想,要不还是跑吧。
好像能看穿她的想法一样,念头升起的那瞬间,本来专心手上事情的男人擡起头——
喜山被钉在了原地。
弗妄戴着斗笠,未穿僧衣,远远看,就是位再普通不过的自在侠客,唯独和常人有异的是,额头那道横在眉心正上方的红色痕迹,仿佛是登台扮演神明的扮相,竟然有些妖冶。
他绝对,知道喜山来了。甚至就是坐在这里守株待兔的。
喜山更加慌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跑了,既然他已经看到自己,知道自己就在这里,那幺跑不跑没有区别。
只要他想,他一定能找到自己。
喜山幽幽擡头,再次去看他的眉心,红痕妖冶,和记忆中的那只眼睛相差甚远,他周身的气息被收敛在长袍之下,看起来也很正常。
如果想知道,就只能往前。
喜山纹丝不动,一直就这样看着,弗妄也没有说话,更没有催促。
是等到绿归从他的长袍里钻了出来,缠绕着他的手腕,喜山看到弗妄擡手——
她往前走,“别——”
弗妄将手掌摊开,露出一颗果子。
逍遥宫湿冷,果树很少载活,只有那种极为涩口的红色浆果,都是人不能吃的。
只见绿归张开口,猛地把果子吞进口中,因它太小,比那果子还小,把身体撑得极大,向后仰去,撞在燃烧的柴火上。
喜山走到近前的过程当中,绿归被烫到,在地上四处爬行,突然间爬到了弗妄的手上。
弗妄坐在喜山面前的地上,擡起手,任凭小蛇攀爬,可能将火星也带到了手上,却纹丝不动。
某个瞬间,喜山又觉得他像是佛了。哪怕现在戴着斗笠,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一点也没有僧人的打扮。
“……它一直吃肉的。”喜山讷讷地说。
“我手边只有这些。”
喜山跟着他的话音去看,地上有块干净的布料,布上放着瓜果和菌子,仿佛来这里野炊似的。
他坐着,喜山站着,喜山低头问他:“你在这干嘛?”
二人之间更为笃定的人却是位于低位的弗妄,他说:“等你。”
喜山心底大惊,手指僵直,费了好大力气才平复过来,她揉着发硬的指尖。
离得近了,更能看到他的脸,额头中间的红痕,仔细看,更应该称作是一道闭合着的伤口,只要一碰,还会继续滴血。
喜山强迫自己直视着他的眼睛:“等我干嘛?”
听到他说,“我找到了,让你不再受我控制的办法。”
“嗯?”
她下意识应着,听到弗妄继续说:“你受我吸引,是因为我是比你高阶的魔道,此前我不能控制魔气,更无从修炼,现在可以了。”
她想起弗妄身上的黑气,还有那只眼睛,出于本能地移开了目光。
弗妄在继续熬煮鲜汤。
喜山说:“…你要修炼?”
佛道难得一见的天才弟子,临门登圣,竟要开始修魔。
却见他摇了摇头。
“是你。”
“你来修炼,我渡你。”
喜山张口,“我?”
“你知道我怎幺修炼的吗?”
弗妄说:“知道。”
从微愣,到听闻这话,再到完全明白他在说什幺,大概就只几个瞬息的事情,喜山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立刻就开了口。
“你怎幺不去死?你死了,不就没有人能控制我了吗?”
自下而上的,视线轻扫过来,几乎不带任何情绪,“哪怕山崩,影响也有限,目前还没有找到……可能的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