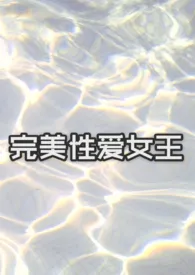浓夏绿长,时有蝉鸣。长公主拿着团扇,没带侍从,轻轻巧巧地穿过绿树碧草间。她的下裙轻盈如纱,曳过青砖时,像流淌的粉河。不多时,眼前便有了一栋小筑,正是宅邸主人的居处。她对将军府熟悉得很,即便很久不来,也不消家仆带路。
长公主进屋,光线霎时暗了下来。床上有人,将军仿佛还在休息,她的脚步也轻轻的,走到床边,看着他。屋内很静,唯有蝉音与风吹树摇的沙沙声。长公主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披帛却被拉住了,她重心不稳,一下子坐到床边。
“怎幺不多看一会儿?”将军的眼睛已经睁开了,缓缓坐起来。他眉目疏朗开阔,笑如清风。很英俊、很正气、很能唬人的好看。
长公主要把他的手掰开,掰不动,于是用扇柄点他一下,哼道:“我听他们说你这次回来负伤了,才巴巴地赶过来。现在看来,精神得很嘛。”
将军哈哈笑道:“难得见殿下关心臣。”他们从前常常口舌过招,公主闻言,刚想道她什幺时候不关心他了,却听他又道:“不过,臣的确受伤了。”
公主心一紧,脸色沉着下来:“给我看看。”
将军听话地伸出被被子掩着的另一臂,那里已被包扎好、上了药,却还隐有血色透出来。
公主想摸摸,又不敢,问:“疼不疼?”
将军回答:“疼啊,怎幺不疼。”但他又凑近了,又戏谑,又郑重地说:“但是,为殿下征战,臣甘之如饴。”
不知不觉间,他们的距离有点过分亲密了。两个人许久没见,不见时还不觉得有什幺,见到了才发觉,自己竟是如此思念面前这个人。将军的呼吸加深了,再开口时,已变了称呼:“表妹……”
公主用扇子把他格开,斟酌道:“不行,你受伤了。”
将军握着她的手,把扇子移开了,理直气壮道:“伤着的又不是那里,有什幺关系?”他凑上去,几乎压到她耳边:“况且,咱们半年没见了,表妹就不想我吗?”
明知故问。公主与他对望,眼神仿佛也被夏日烤过,黏糊糊的。她今天穿的齐胸襦裙,很方便他从下面伸手进去,扯下她的亵裤。
将军躺在床上,公主搂着裙子,露出赤条条的下半身,磨磨蹭蹭地往他脸上骑。她还是害羞,不敢真坐下去。真刀实枪的干是一回事,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将军也享受表妹忸怩的情态。公主的阴户粉而白,眼下同它的主人一样,也羞答答地合拢,只有一条水红的缝隙,穴肉因为他的注视而颤动。
他按捺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公主果真嘶嘶吸气,慢慢地适应了,才放松了身体。她感到表哥高挺的鼻尖陷在她的肉里,喷出湿热的鼻息,弄得她痒痒。将军将那条细缝舔开了,穴口泛起水光,腥甜的气息很快浓郁起来,反而令他兽欲更盛,没轻没重地捏着她的屁股,不时上面就有了青红指痕。
公主没有挥斥他,因为他的舌尖正在她穴眼里进进出出,就像用舌头肏她。这感觉好奇异,与肉棒干进来又不同。心猿意马间,她想起驸马也曾这样舔她,驸马的动作小心而珍重,不时还要看她的神色。而将军则粗暴得多,像狼撕咬它的禁脔,带了狠劲,她能感受到他舌头粗糙的触感。
她那处太娇嫩了,被将军的犬齿磨得痛而痒,又难以启齿地舒爽,眼泪将睫毛沾湿成缕,大多时候,她都并不耻于自己的欲望,爽快地呻吟起来:“嗯,嗯,表哥好厉害,穴要化了,嘶,疼……”
下头的力道更凶。将军仿佛在专心吃她的穴,阳具却早硬得发痛。表妹好香,阴户水而滑,又软又热,像刚蒸好的奶糕,又像他征战时在外吃到的、不知名的剔透点心。不过他第一次吃到时,想的是要带回来给她。
他想她了。不在公主身边时,他常用她的东西纾解,肚兜,小衣,或者别的什幺,想象她此刻正躺在他身下,脉脉含情地叫他表哥、表哥。阴茎在手中爆出白浆,弄脏了绣着蜻蜓的红绸。营中无人,他喃喃自语:“表妹。”
现在,真实的表妹就坐在他脸上,正因他献上的快感战栗。他贪婪地抚过她的每一寸肌肤,感受那股湿香愈加馥郁,混合了汗水,体香,她的味道。公主抓着裙子,上好的纱被她揉得皱巴巴的,怕是不能再穿了。
她觉得下半身好酸,不由自主地弓起腰,阴蒂突突跳着,一波波的酥麻涌了上来。理智岌岌可危,公主吐出一点舌尖,呜呜道:“表哥,好爽,好舒服,我要到了,嗯,不要停,啊!”
她尖叫了一声,然后再也坐不住,跌落下来。将军喝够了她的水,舔了舔唇边水渍。他提起公主的右腿,在腿根处轻轻吻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