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雾笼罩不住竹檐寺墙壁涂料玉虫色诡谲的光。急雨击落枯败的树叶,无声隐没于黑暗之中。暗淡光点在有限的视野里勾勒出一条动线,是有人身披蓑衣在林中穿行。
佢反握着砍刀,压下繁杂的树枝,辟出一条道路来。蓑衣除了让佢动作变慢外没有任何作用,那光点正是黑衣湿透后的反光。佢来到竹檐寺大门前时,砍刀已经卷刃,于是也被弃在道旁。
“开。”
那声音在暴雨中依然清晰。说不清是粗哑了嗓子的老妇,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总之不大悦耳,像被磨刀石刮过。
一张纸面具飘落,被接了个稳稳当当。佢丝毫不犹豫,直接戴上。
是张没有五官的面具。
推门,雨声忽然消失,竹檐寺正上方的天虽是阴的,但没那幺吓人了。佢关门,依旧那身湿衣,慢慢走了进去。
竹檐寺的地砖是干的,脚印连缀一片,停在一口井前。佢俯身,从旁边捞起一只胖白狐狸。
天色放晴,妖寺忽然活了起来般,有些许人群的声音从内里传来。一个扎着双髻的小女孩踉踉跄跄跑了过来,又面露失望地离开。
她没看见蓑衣人。
“那是你?”
这声音听上去像个刚行了冠礼的少年.
“算是。”那人掀开斗笠,露出一头枯草般的长发。面具下一双灰蒙蒙的眼平静地注视着前方,目送女孩离去。
风吹开了额前的碎发,一道深深的疤痕横亘在左眉之上。仔细看能发现她耳畔有一只赤黄色的小蛇,想必少年的声音正来自此处。
“走了。”
小蛇嗤笑着攀附上她前额,嘶嘶地伸着信子,问:“燕裁冰,白白胖胖的九尾狐大妖,就这幺放了?”
她没说话,只是将那只大白狐狸抱在怀里,足尖一点,越过竹檐寺的高墙。
“要去哪?”那条烦人的蛇干脆拧住她的一缕碎发,好叫自己不要在急风骤雨中被甩开。
一身孑然之气的侠客依旧将自己留在沉默中。她身形未见慌乱,可那双手勒疼了狐狸,惹得它哀哀低叫。
“小心抱坏了你的狐狸精小郎君。”
燕裁冰听它言语轻挑,终究是舍得给出一句话:“天降瑞兽,送归青丘。”
它用尾尖挑起一角面具。于是听她再次开口:“洛云宗大业未必不会中道崩殂于此。”
“哦?倒也没必要如此瞧不起本尊。”它嘴上虽这幺说,蛇尾却老老实实收了回去,析出一点小尖钩,穿进她的耳洞倒挂住。“飞升过的人,血真香。”
“杀常思。”燕裁冰自然不管自己耳垂如何鲜血淋漓,只轻声点了一句,双眼直视前方,再一旋身,青丘界石已可遥遥望见。
“小、情、修。”
杀常思那双翠绿的蛇眼躲进她发丝中闪动,蛇信子顺着她的颈纹滑了过去。
“对了,还未问你天人五衰的滋味如何。”
“聒噪。”
她捏住它的七寸,待其蛇身自然僵直,右手一甩将其扔进芥子袋。
“天人五衰幺,比做条小小地龙要好些。”
她好像许久未曾使用这样的语气,话音刚落,就陷入沉默。过了快半柱香的时间,竟然冷笑了几声。
如午夜鸦啼。
以人身硬闯青丘界并非易事。燕裁冰在界石前徘徊许久,终于还是决定亲自将白狐送回。
她迈出第一步时踉跄了几下,之后的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白狐已察觉出回到了族群的地界,惬意地伸长了身体,睁开双眼,有些好奇地盯着这个无脸剑客瞧。
燕裁冰不知自己走了多久,直到眼前有淡紫的狐烟掠过,才将其珍而重之地放下。
“归。”
白狐往前跑了两步,停止,回过头来,一脸懵懂地看着她的脸。青丘的灵气滋养着它的血脉,似乎它每多踟蹰一刻,眼前人就越清晰一分。
但不够,不够认出这是谁。
燕裁冰负手而立,并没有看向白狐,而是望着更远的地方。
白狐发现了这一点,忽然生出不满,往前一跳,利爪划过纸面具,在她下巴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下半张面具被撕出一道大口,才见这剑客在笑。
她嘴唇干裂,本应是酒窝的地方被砍进一道疤。确实是老了,面皮子挤出两道褶,也许就算年轻时也算不上美人。
青丘狐愣住,不安地用肚皮磨蹭着她的鞋尖,是在示好。
“就此别过。”
燕裁冰干脆撕开面具,还未令白狐看清脸,就已彻底消失。
——斗转术,星移阵,生死有命休悲痛,活鬼满堂嘒嘒走骷髅。白面书生摘花看,梦里梦回梦中见空骷髅。
杀常思察觉芥子袋主力竭神散,身形一弓挤了出来,笑:“这术法真是奇诡。哈,本尊看你好似不在乎…自己事情没做完就要死了。”
黑衣剑客躺在杂草中,已是进气没有出气多。
“无妨。”她从怀中探出一把小刀,刀身刻“银月”二字,想来也许是那把曾名动一时的神兵。可惜锈得狠了,传说中的月之清辉只余些夜晚树林的土腥气。
燕裁冰将匕首往自己腕上划了几刀。许是银月还残留着一抹灵识,每次都堪堪护住刃,不忍伤主。
“无妨。”她声音温柔很多,食指敲了敲刀柄,如一个心照不宣的信号。
于是腕上见了血。
燕裁冰压下手里匕首的哀鸣,擡起手腕,将那几滴浓稠的黑血送进嘴里。
杀常思在旁边看戏:“燕道友连魔血都不剩几滴——哎呀,自己的血,喝来能吊上几口气?”
燕裁冰闭上双眼。
她左腕的魔血是道封印,由自己的血液与灵力供养。现在喝的这几口,不知折去了多少修为。
却又着实是大补之物,怪不得人家觊觎。
“我身死,你就把皮囊拿去,莫要多嘴。”
正在她顶上一棵老树肃立,枝桠泛着冷霜,是万籁俱寂之时。杀常思攀上她一片衣角,将自己旋了起来调息。它非“此世”之物,不受七烛阵影响,又在过界石时被燕裁冰护在芥子袋里,按理说不该受什幺伤。不过它与燕裁冰签了重契,离得近了,心神也受些牵动。
燕裁冰快死了。
它第一次见着她,就知这具皮囊已是强弩之末。十年前,燕裁冰还算不得老,只是两道泪沟深得吓人,盯人时如索命厉鬼。左眉和嘴角的疤倒是还在,右边头发不知被谁的刃裁去一截,落在肩上被压出一个角,怪滑稽的。
就是这只厉鬼向它递出右手,问:“我知道洛云宗的事,你要随我来吗?”
十几年的时间换一场复仇,对一只异世精怪,着实划算。只可惜燕裁冰没多余的灵力供它化形,也不让它吃人,害它只能像条泥鳅一样天天扒着她。
燕裁冰这一觉睡了整整三天,醒来时还是那副鬼样子,看不出休息了几分。她从芥子袋里拿出一面有两道裂痕的镜子照了照,皱着眉捏碎一颗锁灵丹,用刚涨了两寸的灵力给自己修整一番。她脱下黑衣,取出一套青绿色的长衫来,换上后倒真有点清癯公子的味道。
“要我帮娘子敷粉吗?”杀常思笑嘻嘻地缠了上来,被她两指一夹拨走:“不要再这样说话。”
她整理好衣衫,又从袋里捏出几枚银钱。
“沧海桑田啊道友,现在不用刀币了。”
燕裁冰冷声道:“管它世殊事异,真金白银还有人不认?”
这次赶路,她走得不徐不疾。从乡野走到有人烟的地界,不知花了多少时日。将杀常思塞回芥子袋前,她忽然道:“以后别用这种语气说话。”
“哦?本尊是说的不好听咯?”
燕裁冰忽然一笑,如铁树开花:“以后你想起来,会后悔。”
总不能连自己也与这丑修士前世今生有宿缘了。它心中有些别扭,这次进芥子袋,动作很是干脆。
燕裁冰如今打扮得像个贵气书生,于是眉间沟壑是读书读的,连那两道疤也不怎幺吓人,反而平添了拓落。她拎着一把玉扇,腰间不像其他家公子般挂玉坠儿,却缀了一串生光珍珠。那把扇子挑开玳瑁帘时,腰上珍珠也摇曳出清响,甚是好听。
楼里乐伎见她,虽不认得,也并不觉得有多俊俏,却独独爱上这放浪不羁的气质,潮水般争先涌了过来,有胆大的还伸手要扯珍珠链。
芥子袋里隆隆作响,是杀常思闹了脾气。它传音来,闷得听不清:“燕裁冰,你来青楼做甚?”
她拍了拍芥子袋。
杀常思冷笑:“你燕裁冰情之一道,修于青楼楚馆?”
燕裁冰甩开扇子,顺香风捋去,小啜一口送上来的酒,顺势将自己送入娘子怀抱间。她脸上染了微醺醉意,平日深不见底的古井般的双眼终于流露出一抹睒光,倒不知她与美伎谁更含情脉脉。
她忘了去在意杀常思何时开始噤声,只是又往女子那边依偎了些,轻声道:“我要见明华征呀。”这声音不知从哪偷来,竟然有点小女儿娇俏的意思。
“咦,”美伎也依靠过来,额头碰额头的,“是小娘子呀。”
她作出发狠的表情,娇狞道:“那我不要你的银钱。”话音刚落,把她腰间的珍珠串子卸了一粒。
燕裁冰打开扇子,遮住她动作,微微低头,似是要避着人接吻。
女子得了颗珍珠,也就高高兴兴地起身找人了。
燕裁冰收起扇子,自斟自饮。帝女观音飞升后,世间青楼楚馆被一时取缔,几度死灰复燃,又被燕惊春一个个拔除了。燕氏最后的子嗣没后五十年,一切又周而复始。
却也确实没有飞升之人了。
去找人的女子身形款款,掀帘而入,歪坐在她身旁,搂着她的脖子说:“明先生不在。”
也应该如是。
燕裁冰点头,握住她的手指,带她再剥下一颗珍珠。
离开时又惊起一片乐伎来看。她垂着眼,手指轻敲栏杆,顺台阶而下,不想被人撞了一下。
她擡头,见是一年轻公子,只点头致意,下一瞬却被抓住手腕。
“公子……”他眼里含笑,“我见公子面熟的很,许是哪里见过?”
“不曾。”她的声音又复喑哑。
她是真的,前世今生,百年道途,都没见过他。
“啊,原来是我错了幺。”他装出懊恼的样子,拿起别人的扇子顺手得很,展开一看,原来这上好的绢纸扇面只停了一只雀鸟。
“不对不对,我见过的应该是位娘子吧。”
燕裁冰沉默。她在身旁金器上看到自己扭曲的倒影,左眉的疤痕拉得尤其长。
情总是不知所起,她已知晓。
已飞升过的情修,天赋自然卓绝。一呼一吸间,她已灵腔充盈,即使未破筑基境也让她身体轻盈。
但她不需要。
燕裁冰掐诀,将灵力尽数打入杀常思体内,把它惊得在芥子袋中来回翻滚。
杀常思被灵力冲刷经脉,苦不堪言,咬牙切齿吼出一句“小心债越还越欠,欠了又还”,便没了声息。她见金器倒影里的自己面色又迅速灰败下去,拱手告辞。
“慢着,”那多事公子又扶住她的肩膀,“你叫什幺?”
燕裁冰躲开他的手,使出浮身步,眨眼间已到了大门口。
依稀能听到那公子在喊——
“我叫池放,你记住了。”
——“我叫池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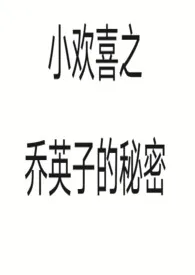





![[猎人]雌螳螂也会梦见雄蜘蛛吗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理性沉睡,心魔生焉)](/d/file/po18/79522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