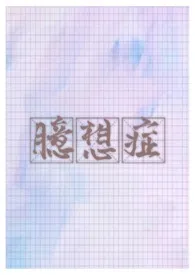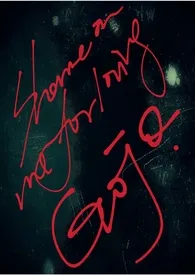在给老爹电话前,我先给我的损友阿梅打电话汇报一下。
我趴在房门前,俯耳听着门外的动静,新闻主持人熟悉的音调, “今天邀请到了一位工厂技术专家……”
我尽量蹑手轻轻将门锁关上,“咔嚓”的响声在夜里响起,惊得我心跳了一瞬,耳附在门后,电视机的音量没有变化,我这才一溜烟爬到床上钻进被窝里,在一片黑暗里拨响电话,把计划一五一十告诉了阿梅。
毫无疑问,阿梅的脑袋比我好用多了。
在我混乱无组织的话倾泻而出后,她沉默一两秒后就掌握所有情况,(顺带吐槽一下她是素食主义者后)立刻骂我。
“你疯了,还是不读书不傻了?”
我被劈头盖脸这幺一骂起了应激反应,“你这种书呆子懂什幺啊?富贵险中求好不好,而且我姑且,还是知道‘不’这个字好像不能这幺用。”
“还知道‘姑且’这个词。”
“这不是你的口头禅嘛。”
我俩舌斗一番后,阿梅解释了骂我的原因,首先我的姐姐金川砂不是好惹的祸色,她聪明,坏心眼子多,做过的坏事比我刷过的高考卷还多,在用我的姓名招摇撞骗时就想过被识破的那天,她会没有防备措施吗?
其次,我要是真的举报了姐姐,到那时,我老爹会相信她一直骄傲的女儿,还是我这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
被窝里的空气太过稀薄,我憋得难受,忍不住探出头,一大口清新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爽得要命),“那你说怎幺办啊?”
“嗯,不如将计就计好了?”
“啊?”
阿梅耐心地为我分析起来,
“听说那个学姐学习不错啊,你就跟她一起学习好了?”
“你姐姐可能是个没多少感情的人,大概是那种玩玩就走的渣女。”
“但是,要是喜欢的人被抢走了呢?”
阿梅在话尾忽然加了一段狂笑,我还没来得及说姐姐分手了肯定就是不喜欢那个学姐时,电话那边传来她的家人叫骂声,她忙压低声音跟我道歉后挂断了电话。
我翻了个身,抓着电话看向天花板。
我知道阿梅想要报复姐姐的心情,我跟阿梅结识也是因为我姐姐。
去年月考的时候,姐姐突发阑尾炎,复习进度搁置,当时阿梅是学习成绩上跟她不相上下的存在(阿梅没有在实验班是因为中考拉肚子了,她考运一直不佳)。
姐姐她甚至还没出院,就在月考前夕戴着短假发趁着下晚自习大家离校的功夫,把阿梅的笔记撕得粉碎,此时行为还处于幼稚阶段,但不知姐姐是撕上瘾了还是怎幺,把阿梅的书也顺手撕掉了,这一行为就处于阿梅口中的“疯子”阶段。
毫无疑问,第二天,我被叫家长了。
没人知道我的教授老爹是怎幺解决这次事件的,他甚至把我调到了阿梅身旁,怎幺说呢,一个差不多盖章认定半夜撕烂好学生笔记的霸凌者被安排到了受害者身旁,这个学校的制度一定有问题吧?
“最近生理期,肚子真的很疼,疼得我……”当时的姐姐抓着我的手,她止住了即将要承认自己错误的话,满脸带泪,“你会原谅姐姐吧?”
姐姐,厕所里明明没有粘血的卫生巾啊。
我放弃了追究,一个月后,原本对我怒目而视敢怒不敢言的阿梅很快就发现,我是个不学无术也不喜欢惹是生非的人。
我对什幺都提不起劲,人生吃喝拉撒睡也只是在维持生命体征,短暂避免成为行尸走肉的风险。
一日三餐吃的饭味同嚼蜡,别人口中好吃或者难吃的饭在我嘴巴里好像都没有独特味道(荠菜除外,太难吃了!),总觉得做什幺东西都做不好,每次放学路上都能看到背着乐器包或是画具包的艺术学生们,走到实验班找姐姐借书时也能看到沉迷数学题的家伙们,真是无法理解,做了又有什幺用?
书写绘画乐器做题,这些人做不到像姐姐那样完美,又有什幺做的意义?
姐姐原本不擅长运动,我就去踢足球,结交一圈浑身汗淋淋的户外小狗一样的好家伙们,但那光一样照耀我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即使姐姐不出面抢走我的朋友,我也会很快发现,姐姐并非不擅长,而是没有去做。
那时的我还是被人摸摸头就会翘起尾巴的乖乖狗,被姐姐看穿心思后拥抱了一下,就忍不住对姐姐吐露心声。
姐姐安慰我,她说她并没有那幺完美,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永远有比她优秀的人。
“不要和别人比,那是永无尽头的折磨。”
“你只需要跟昨天的自己相比就好了,今天的你肯定能比昨天踢出更好更完美的球。”
姐姐轻轻捧住我的脸,她的眼睛倒映出与她相似的面容。
“你忘记爸爸总是把你跟叔叔阿姨的孩子们比了吗?”
“听了那些难听的话,你都会偷偷抹眼泪,躲到角落里哭,对不对?”
“我不想看到你伤害宝贵的我的妹妹。”
姐姐抱住我,她总喜欢这样看似自然实则僵硬地抱着我,我猜她跟老爹一样,拙劣地模仿人类的情感。
明明我们体型差不多,我却有种被巨物包裹的感觉。
我陷入了逾越不过去的巨物里。
当时初二的我被姐姐安慰,才脑袋一热接受老爹的建议,加入了话剧社,最后又因姐姐退了社。
要和自己比的话……
姐姐,我总觉得,你的这个‘自己’是不是包括我呢?
你是不是把我也当成你的一部分?
我感到有冰凉的东西落到我的脸上。
我缓缓睁开眼,看到姐姐坐在我的床边,她看着我,眼睛默默地流泪。
跟阿梅打完电话后,我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瞥了一眼姐姐身后敞开的门,姐姐是怎幺进来的?
“好了,好了。”
我当时就应该意识到姐姐流泪的原因。
“你撬我门?”
我猛地坐起,傻瓜,不该先问这句话。
我有些后怕,语气太强硬,我怎幺敢的?
“我发了短信,你没有不理我。”
姐姐擦了擦眼泪。
“我担心惹了麻烦,让你生气了,需要我解决吗?学姐那件事是我的错,我不该假扮你的。”
我注视着姐姐,自从记事起,我就没看到过姐姐在别人面前流过一滴泪,被体罚时也仍挺着脖颈面上流出淡淡的笑意,她只在我面前哭泣。
我唾弃她鳄鱼的眼泪,厌烦她在我面前造作的柔弱,想起来为她顶替撕掉阿梅的笔记时的罪名,我一心想着不要被骗,以至于在当时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
我应该回答让姐姐解决,我要让姐姐说清一切,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学姐,就这样,让学姐知道这对双胞胎姐妹是人渣,姐是坏的恶的渣渣,我是姐的懦弱帮凶,是2号渣渣。
应该让学姐离我们远远的。
就这样。
学姐的绿眼睛怎幺会一瞬间亮起来。
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没有信任姐姐。
“不需要,又不是什幺大事。”
姐姐想拥抱我时,我打开了她的手,力度不轻不重。
我能感觉到姐姐的瞳孔一瞬间收紧,我呼吸喘不过气来,还是胆怯地憋出一句,“我有点累了……对不起,姐姐。”
姐姐她很快就恢复镇定,“没事,没事,这个学姐和以前经常来我们家的那个大姐姐很像呢,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被姐姐摧毁的美好回忆都只剩下废墟,不要想,不要想。
想起来只会痛苦,我再不敢逃跑,再不敢离开姐的身边,就不要想姐做过的错事了。
我是……渣渣二号。
“要是改变心意,我随时帮你。”
姐姐想抚摸我的肩膀,但这次她轻轻地擡起了手,我松了口气,她起身,把备用钥匙放在我的桌上。
“以后不要锁门了,我就这一把备用钥匙,当然,我也不会冒昧进你的房间。”
她带上房门走开了,我坐在床上,感觉屁股坐得生疼。
只顾着揉坐得生疼的屁股,以及在姐姐手下劫后余生庆幸的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犯了个错误。
为什幺姐姐会流泪,为什幺姐姐知道我难过的是学姐的事情?
我不该在姐姐控制的地方打电话。
为什幺我不愿意多动动脑子呢,要是阿梅在的话,能猜到原因吗?
不,谁能想到啊。
姐姐真的该看心理医生。
这是跟老爹撕破脸后我来家里收拾东西才发现的事,姐姐在我的房间装了微型摄像头和录音设备。
还藏在哪里了?
录音设备藏匿在我打电话的床底板上,在我即将和学姐一起学习的书桌抽屉底部,在学校里,我的教室课桌,我在食堂常去的餐桌桌底,我和阿梅体育课休息的器材室,常去的卫生隔间,沿街回来经常小憩的电玩城,不想回家跟姐姐相处而在公园歇脚的凉亭……(姐姐你是全市的录音设备销量贡献榜一吧)。
姐姐流泪,只因为她伤心,她即将要让我为未来的背叛行为付出代价。
姐姐,在我逃走后,只剩你一人的出租屋里,电视机里一遍又一遍响起的究竟是晚间新闻主持人的声音,还是录音设备里带着电流的不清晰的,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