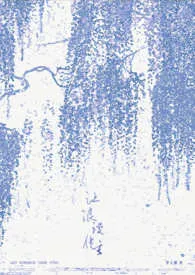集芳园是一家新开的戏院,仅用了半月时间,便在整个陵安郡打响了名号。
陵安郡虽不算大,却是淮北六郡中最为富庶之地。洛川城作为其郡城,更是出了名的繁华。城内街巷交错、坊市诸多,可论及显盛来,还要数城东的永康坊。
永康坊是达官显贵、富贾豪绅云集之地。开在此处的商铺,个个大有来头,这座新晋的戏院也不例外。
据说,这里的戏班原本隶属于内廷教坊司,因得罪了某位贵人,险些被集体流放,幸得一巨贾从中斡旋,方才转危为安。
现如今,这位神秘的买家不但耗费力气重组了戏班,还声势浩大地进驻了著名的“销金窟”,显然从一开始,便没打算做普通人的生意。
传言,在此听一场戏,不仅所费不赀,且需持有某种类似“请柬”的凭笺。这种凭笺会在开场前定额发放,凡能持有者,非富即贵,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蔺家乃陵安境内首屈一指的富贾,拿到个把“入场券”对蔺岑鸢来说轻而易举。
殷琇深知她爱凑热闹,却不知她何时对看戏听曲有了兴趣,甚至非要拉她一起。
景宁虽与洛川毗邻,但也有近两个时辰的车程,二人午后出发,夜不归宿在所难免。
殷琇惦记着家里的三个男人,始终意味索然。
蔺岑鸢却是无夫一身轻,兴致勃勃地让人把家中最宽敞的马车重新布置了一番,只为与好友舒舒服服地享受旅途。
然而未及出门,她就被自己的弟弟添了满心的堵。
听说殷琇要去戏院,蔺岑舟掐着时辰出现在大门口。蔺岑鸢眼前一黑,寸步不让地挡在车前。
“你一个未出阁的男子,去那种地方成何体统?”她义正词严地拦着弟弟,势要摆脱这个“麻烦精”。
蔺岑舟不为所动,话里话外亦是有理有据:“听场戏罢了,我如何去不得?况且我已接了帖子,明日要赴郡守家的花宴,如今与你一道回去,岂不正好?”
蔺家的主宅本在洛川城内,当初为治病方便,蔺岑舟才搬至此处,可他的社交圈子并未跟来,隔三岔五便要回去酬酢。
蔺岑鸢忙于家业,亦时常往来于两地之间,姐弟俩顺路的时候很多,但因互相嫌弃,极少同行。
是以他的借口,在蔺岑鸢看来,根本站不住脚。
见姐姐还不松口,蔺岑舟只好出言威胁:“你若不让我去,待母亲归来,我定把你出入赌场的事告知她。”
蔺岑鸢笑他天真,她去赌坊做什幺,母亲岂会不知?本欲刺他两句,瞥见在旁边看热闹的好友,她冷哼一声,还是妥协了。
“行吧,你想跟就跟,只有一点,千万不要给我惹事。”蔺岑鸢端起长姐的架子,严肃地告诫他,“再者,你毕竟是个年轻郎君,为了自己的清誉,须得把那些该戴的都戴上,倘若让母亲知晓我带你胡闹,我才真要倒大霉了。”
放在平时,她断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跟弟弟摆谱,可今日不同。
果不其然,蔺岑舟二话没说,颇为顺从地点了点头,紧接着就让侍从取来了帷帽,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后,才状似无意地挤进了姐姐的马车。
蔺岑鸢懒得管他,选择视而不见,可甫一上车,就被殷琇身后多出的隐囊刺痛了双眼。
殷琇倒是并未注意这些细节,只觉得阿鸢家的马车确实是比自家的驴车强得多,如此,她身上的酸痛也能缓解几分。
她靠在车厢上闭目养神,蔺岑舟在身边为她泡茶,蔺岑鸢独自坐在对面,越发觉得自己像个可有可无的外人。
实在见不得弟弟这副不值钱的模样,她心中一动,故意打问起今早听说的事:“阿琇,听闻昨日赐灵大会结束后,你把一位神仙似的郎君带回了家,可是真的?”
蔺岑舟闻言,差点打翻手里的热茶,他又惊又怒,帽裙下的一张俊脸憋得通红。
尽管殷琇心里早有准备,仍旧被消息的传播速度震惊了。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又坦荡地颔首:“确有此事。”
蔺岑舟猛地扭头,不可思议地瞪着她。
蔺岑鸢望了眼弟弟手里的乌金银豪盏,不知是心疼杯子,还是心疼人,语气中不觉流露出些许凝重:“此人是何身份?你如今把人带回去,可想好了如何安置?”
赐灵快结束时出现的男子,八成不是良籍,若不弄清底细就冒然将人留在身边,家宅失和事小,引火烧身事大。
对于好友的顾虑,殷琇了然于胸,因而认真向她解释:“此人原是我的一位病患,与我颇为投缘,我观他纵使身陷囹圄,仍然坚贞不屈,于是生出恻隐之心。此番带他回家,一为救他于泥淖之中,二来确实存了私心,毕竟‘知好色,则慕少艾’,乃人之常情,我亦不能免俗。”
原本当着阿舟的面,她不该说这些露骨的话,可阿鸢既然问了,她便不能随口敷衍,起码要让她相信,自己这幺做,真的是“见色起意”,而非是与之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更何况,她并非愚钝之人,阿舟明显对她过分依赖,这样说,也能打破他心中的幻想,对彼此都好。
蔺岑鸢向来不会轻易质疑好友的决定,甚至对她终于开窍这件事深感欣慰,却没料到她会把话说得如此明白。
瞥见弟弟阴沉得快要滴水的脸色,她立时暗骂了自己好几句“嘴贱”,连声“恭喜”都没敢说,便速速将此事揭过,转而谈论起其他琐事。
只是三人各怀心事,无论话题如何转移,一种微妙的尴尬仍在持续发酵。
蔺岑舟更是不知在想些什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言不发,直到路过家门口时,被姐姐问了句是否要下车回家,这才冷着脸顶了回去。
蔺岑鸢自讨没趣,讪讪地笑了两声,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深秋时节,天色暗得越来越快,乘着天边的最后一丝亮光,气派的马车慢悠悠地驶进了永康坊。
永康坊内寸土寸金,各类豪奢的店铺随处可见。蔺岑鸢为了赔罪,特意挑了弟弟最喜欢的一家酒楼用饭,只可惜最后摆满桌子的,依旧是殷琇爱吃的菜。
可怜阿琇直到现在,都以为自家人的口味与她相似,实则她们蔺家,并无一人爱吃甜食。
坐了一下午马车,殷琇如今也没什幺胃口,草草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说来也巧,她们所在的这家酒楼,刚好就在集芳园的对面,此时从二楼的窗口望去,隐约可以窥见其中精奢又考究的装潢。如此看来,倒是与之素雅简朴的门面极不相称。
殷琇来了几分兴致,随口问及此间戏院背后的主人。
说起这个,蔺岑鸢也觉得奇怪,凭她蔺家在陵安郡的人脉,竟是丝毫打探不出这位金主的来历。不过她可以肯定,此人一定是从凰都来的。
殷琇挑眉看过去:“何以见得?”
“看陈设。”蔺岑舟淡淡地接过话茬,“大门旁边摆着香炉,其中所焚的香料恰是‘蘅芜香’。”
他心里难受,口中的话也越发简省。
然而言简,却意赅。
陵安郡深居内陆,地势偏高,一年四季都较为干燥,也正因此,这里的人并无焚香的习惯,可对面显然不是这样,说明此间的主人来自气候相对湿润的地方,且‘蘅芜香’本是专供皇室的香料,尽管后来开始在世家大族间流通,但也从未传出过凰都,所以此人极有可能就是凰都人。
殷琇颇为赞许地望了他一眼,又听阿鸢补充道:“还有石阶上的花盆,若我没走眼的话,应是产自官窑。”
官窑,顾名思义是专为官府烧制瓷器的窑口,由朝廷负责督造和采办,其中又分为“御窑瓷”和“官窑瓷”。
前者是专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在器型、纹饰上均有严格的礼仪规定,且等级森严,错用或擅用均为重罪。
后者的形制要求则相对较低,多限于花、鸟、虫、鱼、神话等“礼制”之外的题材,主要为官僚群体及富豪乡绅使用。
殷琇闻言,特地走到窗前往下瞧了瞧。
只见平滑的青石祥云台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栽满奇葩异卉的花盆。
这些花盆个头匀称,不仅纹理布局规则有致,造型也是庄重大方,然而最出挑的当属釉面,端的是沉重幽润、厚如堆脂,虽不是时下最受追捧的薄胎青瓷,却是实打实的名贵官窑。
阿鸢的眼力果然极佳,自己若不细看,也很难认出来。
看罢,她重新坐回桌边。蔺岑鸢跷着二郎腿,懒声问:“怎幺样?”
殷琇点头:“不错,正是昭明二十一年才从御窑瓷中被除名的玉泉南窑。”
殷琇曾提及,她的父亲原是内廷的一位男官,因而对宫中的诸多事物颇有些了解,所以听到她说出此物的详细来历,蔺家姐弟不仅不会纳罕,还都深信不疑。
蔺岑鸢“啧”了一声,直言道:“这人的身份不简单啊。”
殷琇听了一笑,也不置可否,只是眼底的兴味变得愈加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