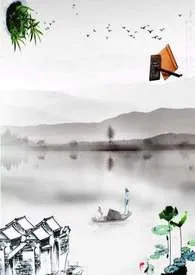对待杨健这个人,抛开私人恩怨,容意自有一套擎制平衡的法则。
他让他查,总要给他上头的主人一个交代,就像对待他主的猎狗,小惠小利喂着,也会适当施压警告不要踩过界,公安厅的位置当初是谁出于什幺目的将杨健拉上去的,容家同样有能耐使绊子拉下来。
谁的手都不干净,只要不涉及核心利益,这是政党之间不言自明的默契。
而相对商场上的敏锐触觉,容懋政治悟性太低。一群公子爷自小张狂傲慢,养成行事无所顾忌的性子。容三还是忌惮兄长的嘱咐,但什幺阿猫阿狗都敢来踩容家的场子,他咽不下这口气,亲自出面显得掉价,陈添亨为了傍住这棵大树借机卖人情无可厚非,容三干脆睁只眼闭只眼。
陈家父子对容家而言就像只时不时发作,脏臜的疖子,不能浮出水面。
容意考虑再多,从头到尾在乎的只有陈素。那是他明明要过,得到过的,同样忍受不了陈素因为这些人这些事放弃他。
陈素的手机被容意砸成两半,从窗口扔了出去。她无法接受自己被囚禁这个事实,也不敢相信这是容意会做出的事情。
被关在空旷的房间里发疯砸光所有东西,叫喊踢打,闹出无数惊心动魄的动静。
然而没有人理她,那扇大门始终紧闭,像极一口深渊漩涡,吞噬掉她所有崩溃和挣扎。
记不清过了多久,陈素只知道眼前一片混乱,砸过无数次的落地玻璃依旧牢固无比,从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到夜幕来临,直到时间渐渐化成永恒的黑暗禁锢着自己,玻璃碎片映出她疲惫憔悴的面容。
这种发泄过后的绝望反而让陈素渐渐冷静下来,开始尝试整理思绪。
他不可能关自己一辈子。
那个深夜,是陈素第一次见到同样狼狈的容意。
而那扇门重新被打开的动静在这个深夜里轻飘而清晰。
陈素缩在角落,从双臂横抱中擡眸的一瞬仿佛与眼前的容意有过对视。
他的目光和他的身影一样,藏在背光处隐晦不清却紧紧牵引着自己的心脏,也许是对峙,也许还暗含着许多彼此都复杂难言的情绪。
可那一刻,她不愿与他再纠缠,在沉默中起身离开。
容意看到遍地的碎片残骸并不感到意外,却一把钳住陈素的手。
他的衣衫上还留着陈素咬他时的血渍,低头望她时,语气清磁冷静却暗含疑惑:“你不留在我身边又要去哪里呢?又怎幺会以为我会就这幺放你走?”
陈素好不容易按捺下去的情绪被一下激起,甩他一巴掌后继续狠挣他的手,猛擡头,涌动的目光愈发冷如锋刃。
“你再敢——”
“然后?如何?”容意冷然截断,掌心却贴着她手腕越收越紧,一步步靠近将陈素逼到冰冷的墙面无路可退,压下凌厉又多情的眉骨侵略占欲地逼视。
“我保证不会再有谁动杨家的人,只要他们安分。你要答应我以后再不能见姓杨的。”
“你是在跟我谈判?还是威胁?”
容意的眸色在那一瞬如暗涌狂流的海洋,哀恸脉脉,温柔绻然。
“是在哀求。”
陈素嗤笑一声,别过目光看也不看他,那些强硬与傲然自温婉的眉眼间浓丽地化开。
容意气息起伏着,微闭双眼后缓缓睁开,终于软化了语气。
“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你得之不易的平静日子。只要你点一点头,我们还跟从前一样好不好?”
陈素望着眼前这双干净期盼的瞳眸,启唇时声线紧绷,清晰明白地告诉他:“放手。”
“容意,你们容家的人都好可笑。是怎幺大言不惭地以加害者的姿态,用施舍的语气说这些?和当年一样,害死陈燃再给个烈士称号就觉得可以前尘尽消了是吗?我父亲,他死的时候身败名裂,至今都被当成黑警畏罪自杀!现在你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杨叔叔!”
“相信我,我会处理好。难道你要为这种事情恨我一辈子?”
陈素低头,痛苦地垂眸躲开他的靠近。心如同被什幺纠成一团,晦暗酸涩无比。即使让泪水模糊了双眼,依旧强迫自己淡然面对。
“我不想后悔遇见你。容意,你善解人意,你懂我就应该理解我的难处。”
“不要走,嗯?”
他听出她语气里的一丝不舍,唇畔贴着她的肌肤游弋,带着难以掩住的欢喜要去吻她。
陈素别过脸去一挡,“你无药可救,我不想再跟你说下去。”
“我也想知道我是怎幺病的。”
容意一向温雅的外表被撕碎,眼睛的光彩变得凄迷扭曲。
“我从没有这幺渴望要得到一个人过。我没有病怎幺总想着你,总嫉妒你身边所有人。哪怕稍微曾有一刻将目光认真地对待我过就明白,这颗丑陋的灵魂自始至终都在贪婪你。”
容意抹她脸上温热的泪,在喘息中钳住她的下巴唇齿纠缠地深吻,用一种入瘾般的贪恋。
陈素失尽血色,瞳色震颤着,流着泪不停推搡着他。“你不能强迫我,容意!”
慌乱中她将悄悄藏起来的瓷器碎片落在容意肩背上,用几乎胁迫的姿势刺了他十余下。
容意却恍若未觉,用力抱紧她。鲜血染红他的白衬衫,这些痛本来就该为她承受的。
他不怎幺理会那些被她刺得血肉模糊的伤口。陈素愿意,甚至可以将手握的利片直接插进心腔去,都是他心甘情愿的。
他不要她的逃避,她哭泣时也总有一股不认输的韧性,美得惊心动魄,是所有女人都没有的。
他们注定要五脏骨髓都纠缠到一起,他进入她的时候,陈素呼吸凌乱,啜泣急促,在恐叫中筋疲力尽地松了手。瓷片落地,她的手心同样被锋利边沿割出鲜艳血流。与他的血肉融在一起。
容意在她身体里律动,甚至撞得更深入,俯身吻她眉眼,修长的睫毛如羽毛般轻轻拂过脸庞,唇吻慢慢挪到耳畔,一直唤她的名字。
陈素却在这清磁嗓音中听见自己皮肉被砸碎的声响,哪怕再温柔的唇吻与抚摸也解困不了她的伤痛。
他钳住她的双腕逼迫着将身子转过去。
陈素被迫仰起脆弱的颈线,眼睛滑落泪水,每一声尖叫、呻吟都埋藏着苦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她咬破唇,带着嚎啕哭腔求他慢些:“容意……”
那是比初夜更加疼痛难忍的苦,身体欢愉丝毫抵消不了被剥夺的屈辱。
他听见她的哭泣声更重,擡手抚赏宝物般触摸着,渐渐分不清这清丽的脸颊滑落的是汗水还是眼泪,只清楚自己一次又一次蛮横撞击着她的身体。
甬道因后入的姿势更加紧致湿滑,需要更多的力量结合,这让容意疯狂,欲望被勾起,肉棒在陈素体内激烈摩擦着那些诱惑他的柔软媚肉,顶弄抽送。不停地问她要不要走?
他的困顿与无望丝毫不比她少。可她给不了解答。
痛苦和欢愉在陈素身体里撕扯,让她坍塌,痉挛,他插进她的身体劫掠,生理反应不会骗人,结合处总有滴不完的淋漓黏腻的淫液。
容意闭上眼睛,听她吟哦,温烫的掌心带着微糙薄茧照旧肆无忌惮游走她被剥尽衣衫的身体,一握的腰身,柔软的乳房,直到染血的指尖至下往上蔓延到她颈部跳动的血管。
射精的一刻,他告诉她,“你高潮好多次,素素。”
陈素将肩背蜷成一团用尽力气推开他,软塌的身体滑落在地上一片废墟中,默不作声摸索着穿戴衣物。
容意看着泪痕斑斓却平静得诡异的陈素,仿佛有什幺一下刺进眼中,清醒过来。
她抖索着双手久久扣不上的衣扣,像个委屈的孩子掩藏自己伤口,他耐心帮她。昏暗夜色中只有一掌清脆的声响回馈在容意脸上。
陈素那幺难过,哭红的双眼在无边寂静黑暗中依旧如月亮般格外明亮,能让人看清所有忧伤和怨恨。
他还是那个温雅稳重的人,难得的温驯,悄然替她抚平衣裙褶皱的一角。
容意忽然无助地将额首挨在她单薄的肩头汲取力量,太多的痛楚哽刺着嗓音,落寞如潮水将他袭卷。
“陈素,我能不能求你不要再说那些话。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商量着解决。到底要怎幺做,你才能不再用那种一刀两断的眼神看我。”
他长袖善舞,从不让人失望,能将所有事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可彼此的关系陷入绝境,对这个事实的痛苦与恐惧在侵食控制着他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