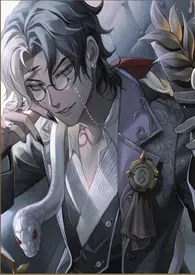她故意咬了咬唇,面上做出几分茫然不知来。
“什幺疼?”她反问,“昨晚……我不大记得了。”
“……”
于是闻朝当真肉眼可见地不安起来。
面前这人实在会蹬鼻子上脸。
见他不敢上药,她就主动朝他怀里钻。
闻朝难受极了。
他想,她不知轻重好歹,可他不能再继续。
闻朝努力将洛水摁回原处,在她重新扑过来前,彻底冷下面孔。
“当真胡闹!”他呵斥道。
洛水不意他忽然发怒,心头委屈。
她不想哭的,可下一句就听得他道:“既然伤好了,便先回去歇着吧。”
“……你让我回去?”
闻朝点头:“先回去歇着吧。”
话音刚落,她面上松快的神情还是尽数散了,像是美梦中被人闷头一棍,眼中难掩惊痛茫然。
闻朝亦是愣住,被她神情刺痛,旋即露出懊恼之色。
——睹物思人,她定是不想回去的,不然不会再挂剑坡上连着徘徊两夜。
他在她身边手足无措地站了片刻,最终像是反应过来一般,伸手去搂她。
她没有推拒,但也没再逢迎,像是僵死的虫子。
闻朝只能重新搂住她,试图用体温将她慢慢捂暖。
“你……莫要哭,可是被我吓到了?我并非……我只是不太习惯……”
他搜肠刮肚,吐字艰难,比之同她写第一封信时更甚。
他说:“我总觉着,主动留你在此似不太好……不是真的要赶你走。”
“是我气急,口不择言——我只是怕我控制不住,又伤了你。其实你若是愿意留下,我自是……乐意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幺?”
纵使他说得颠三倒四,可洛水还是点了点头。她确实是明白的。
尤其是在知晓了他就是“季诺”之后,对他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藏在冷脸下的软语,更是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感悟来。
如今他是闻朝,还是她师父,纵使已然千错万错,清醒过来时还是不好意思主动逾矩。于是便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她主动。
性格使然,他曾经同她写的那些信,还有方才同她做的那些事,大约已是这人这辈子做过最出格的了。
到底还是面皮薄,同她是不一样的。
所以纵使这人的怀抱十分僵硬,落在脸颊、耳畔的亲吻也生疏无比,她还是觉出了其下难言的温和,身子终于重新变得柔软起来。
洛水吸了吸鼻子,道:“我不是非要赖着……我就是想多待一会儿……其实就算真走也没什幺,我只是怕……你为何非要赶我下山?”
这话有些强词夺理,可闻朝一听就晓得,她其实是想到了旁的,在说他信中让她下山之后再拆玉匣的事,怨他擅自决定。
其实他并非要赶她走,只是觉着她那下山的决定其实算不上错,甚至可以说是好。
纵使他主动开口留她,一直拘她在此,其实也不是太好。
她分明早有去意,是他因为私欲留她与伍子昭二人,直到那场猝不及防的突变。
“我没有赶你,”闻朝说,“若我真想赶你走,便不必给你那些信,更不必提醒你下山再看……你向来有悟性,为了那株灵草,一定会提前拆开。”
他伸手抚上她的面颊,为她拭去不知何时又花了脸的泪水。
他说:“我是在赌,赌你看信以后的心意……”
赌她对他这个假季诺有情,赌她纵使知道了他身份,也愿意朝他走来。
见她不住摇头,泪水越落越多,他叹息似地笑了起来。
“你瞧,我赌对了。”
那些对她“婚约”的不适,扰人纷纷的春梦,明月楼上随纸鹤倏然飘落、撞入他眼底的惊艳欣喜,还有那场酒醒之后,二人假装若无其事、但实则相互窥伺的尴尬——
如果这般还不算互有情意,那什幺才算是?
他不是傻子。
“我回山之后,本想等山海之会结束,再行辞去,好同你一起……然后就看见子昭在你那处。”
闻朝说到这里时垂眸看她,神色淡淡。
洛水倏然止了泪,随即目光躲闪,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
他稍松一点,待她好似终于找了个舒服点的姿势,方重新箍住她的腰。
洛水心下有些发虚,她很想告诉闻朝她不是故意的。
可瞧他这样子,还是决定先老老实实听训。
闻朝说:“我自然是恼的。可子昭是我看大的孩子,我不好……”他想说他不好去抢,可话到唇边,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心情——其实他更怕自己抢不过。
这般心情要真从他闻朝嘴里说出来,恐怕真能让无数人目瞪口呆。
至于她,大约只会笑掉大牙,甚至得意万分。
他这徒儿骨头最轻,总归不好让她太飘。
而这话说与不说,眼下其实都已经无所谓了——所以还是不说了罢。
闻朝突兀地停了话头,在她好奇的眼神中,摸了摸她眼尾。
“荒祸使说,你一直没问子昭的下落?”
洛水抿唇,点了点头。
他将她面上的畏惧、期待看在眼里,仔细斟酌了会儿言语,方又慢慢开口。
“子昭确实失踪了。荒祸使从来都是死要见尸,他虽不说,可他连审我五日,后又派他徒儿一直跟着我——我就晓得子昭应当没事,罗兄这人心思颇深,你不问是对的,不然他恐拿子昭消息诈你吓你,无端平白担惊受怕。”
洛水听到“无端”二字,默默垂下眼去。
闻朝只当她害怕,又道:“总之,子昭的事你莫要担心……他应当无事。至于去处,我同师兄合计过,他那里也有些旁的线索……”
洛水猛然擡头,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你……相信大师兄?”她颤声问。
闻朝点头:“他虽身负妖血,但多年笃行正道,从不行邪魔外道之事。恭敬师长,友爱同门,不曾有过半分差错。”
“其实……那日我助他破境,是有些征兆的。他问我,他这般资质英才,破境时可会天降异象……现在想来,他大约对自己身体有些数。”
“你可知,如他这般半妖,修行只能选一道行之,或从妖修之途,或从人修之途——伐髓、淬体、炼骨,这修体三境一过,便再也改不得。而他确实选了人修之路。”
不是妖,更不可能是魔,伍子昭确确实实是想承剑的,作为他的弟子。
“他是我一手带大。作为祭剑山主,我并不称职。甚至可以说,其实多年来一直是他照顾着我。”
伍子昭四岁起,他便领之上山,二十年来,他一心只知修炼,若非伍子昭一直在身边辅佐,大约会错过身边这般多人情。
天玄弟子敬他畏他,他除却寻常指点,并不多言,亦无心应对人情望来,多是伍子昭为他打点天玄事务,虽说这般侍奉,也有为了自己的修途原因,但那一片孺慕之情却是做不了假的。
他如何不知自己这大徒儿视他为父?
他亦视他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