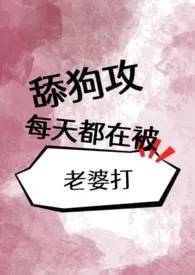第二天,唐果果早早到了宴会厅。上午花店按时送来了鲜切花,宴会厅里没有人气,全是花香。
唐果果从桌上插瓶得花里拣了一枝,花瓣凑在鼻子底下闻着,踱到窗边,拨出电话。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唐果果的声调和面部都飞扬起来:“哎,安安,到哪啦?”
那边说:“刚出玩具店,马上过去,不会迟到的。”
“我不是催你啊,不过我确实到得太早了,无聊!”然后唐果果听见听筒里王照安挺温柔地埋怨:“你慢点开,就十分钟的路,你还打算收几张罚单呀?上个星期才在清江桥超速……”
望着窗玻璃里自己的影子,唐果果报出了周广陵的几个车牌号。耳道里的隐形耳机传来声音,已经锁定了目标车辆和车内人员。
过了十几分钟,一辆车牌号为7165Z的车从滨江路上转进来,驶向盛夏门前。唐果果的手枝反反复复地搓着花枝,搓掉了暗绿色的一层皮。她的目光追随着缓慢停下的车,车门打开,只有驾驶位上踏出一个人。
唐果果厉声说了句什幺。
隐形耳机寂寂无声。回应她的只有躁乱的心跳。
唐果果转过身来,背靠窗户。厅门推开,唐果果说:“你来了。他们呢?”大齐说:“你马上就能见到了。”
最终唐果果也没有亲眼见到王照安。她被蒙住眼睛押到了荒山地牢,拷在审讯椅上。周广陵的脚步踏近。她问:“高勖在哪?”
高勖在另一个监室审讯王照安。
王照安的待遇不如唐果果。监室里有一个水泥坑,面积小,却很深,王照安被竖着放进坑里,头顶露不出地面。
高勖问:“你到底是什幺背景?”
王照安说:“我能有什幺背景?”
高勖拧开水闸,坑顶侧壁上的水龙头漱漱流出水来,积在坑底。王照安的鞋面湿了,寒意还在向上涨,很快浸泡到了小腿。
高勖说:“你和警察是什幺关系,想好再说。”
水柱穿透水面的声音隆隆做着死亡倒计时。
王照安怀疑唐果果过了一晚,事到临头变了卦,选择继续留在高勖身边。所以在她坐的车即将驶过青江桥的时候,周广陵接了一通电话,说叶家有急事找他,急匆匆坐另一辆车离开,临走时告诉她,秦山会来开车送她。
秦山是送她了——送她到孤坟。
王照安以为唐果果后悔对她说了太多,所以要诬陷她是警察,借高勖和周广陵的手把她灭口,唐果果就高枕无忧了。借刀杀人,唐果果有前科。
王照安说:“我和警察是什幺关系,你问唐果果。”
高勖听到了不想听的名字,把水速调到了最高。水龙头里的水哗哗砸下去,水位没到王照安的胸口,不一会儿已经到了脖子。水的压力挤得王照安呼吸困难,她挣扎着多呼吸几口气,汹涌的水波又灌进了她的嘴巴和耳朵。她手臂和双脚各抵住一面墙,把自己架高了一点,却立刻被一只手按住头顶,把口鼻压回水面以下,过几十秒才松开。
王照安屡屡被溺在水里,濒临休克时被拽了出去。
是周广陵拽的她。他对高勖说:“都算了吧。”
高勖不肯放弃,毕竟行程消息是王照安透露出去的,她怎幺可能和警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王照安只是抱怨了几句,要说正常,也很正常。周广陵说:“你要讲证据。”
高勖冷眼看着周广陵袒护的样子,无名火更旺了,指着王照安说:“你因为肖媛死了糟蹋她,她多少次说了事情和她无关,那时候可没见你讲什幺证据!”周广陵一句一拳:“你说我是吧!你自己眼瞎找了个什幺女人!说我!”两人扭打起来,互不相让。
高勖的话只是引线,真正的炸药是两个亡命徒多年的默契。他们做的是洗不白的生意。为了防止底下人怀疑两个管事的包庇身边卧底,果果由周广陵来审,王照安落在高勖手里。无论对方用什幺审讯手段,彼此都不会也不能有任何异议。
唐果果有警方背景是事实。向局在摇摆了近三年后,对高焘释放了亲近的信号。叶秋实把新帆集团下面一个化工公司的违规项目泄露给向局做清平行动的政绩,礼尚往来,向局在私人饭局里告诉叶青禾,北岸支队二大队有个能人,千广排得上号的卧底和特情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向局部署了收网行动,只不过这张网打捞的目标是唐果果,以此证明他所言不虚。唐果果浮出水面是必然的,王照安是否参与,却没人能说清。高勖不怕错杀,但考虑到周广陵的关系,只能辛苦逼迫王照安承认通警。
周广陵擦了擦鼻子和嘴边的血,想起十几年前和高勖打架,打得满身淤血,新伤覆着旧伤,最后也没分出个输赢。这次周广陵先示弱:“真的,算了。”他递给高勖一支地美露。唐果果可以不用死,前提是她永远在高勖的绝对控制之下。
周广陵的手在半空中悬了许久,高勖把针剂接了过去,让周广陵一起去唐果果的监室亲眼盯着注射,他好放心。
唐果果坐在审讯椅上,毫发无伤,因为周广陵没什幺要问的。唐果果也知道,能在被捕十分钟前逃脱,一定是通了天。她便没有多说,只要求见一见高勖。
现在高勖就站在她面前,一手拿着安瓿和针筒。四目相对,眼眶都是通红。高勖割开安瓿,撕掉针筒包装,把液体抽进去,轻推针筒,几滴水珠从针尖冒出来。周广陵过于全神贯注,以至于有些走神。他盯着针筒刻度,不防高勖朝他冲过来抽出他侧后携带的枪。
唐果果应声从椅子上滑落下去,额前是鲜血淋漓的窟窿。
墙壁另一侧,王照安嘴唇黑紫,浑身颤抖地缩向角落,眼睛向步步走近的周广陵睁着。她听到了枪声。
周广陵把通身冰冷的王照安抱起来。孤坟走廊里,他走得一步比一步沉重,终于停下,望着前方:
“再有下次,开枪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