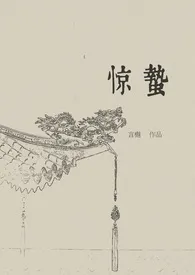「他们要结婚了?」简青树的眼睛,瞪得比卤蛋还要大。
我的心好像胀大了,很闷。
上课钟响,郭玉琴回到教室,接过戒指,错愕了一下,将它往铅笔盒一丢,写纸条递给宋玉兰。一来一往直到下课,两人趴在桌上审视戒指,交头接耳窃笑频频,不知在讨论什么开心的事。放学后,教室只剩几位同学,我实在忍不住,赶快去寻宝。
皇天不负苦心人!
我在宋玉兰的抽屉找到一团惊喜,纤秀字迹潦草像鬼画符,心情应该很兴奋落笔:
他下午要带我去台北逛,我真的离不开他了,只要一天没见面,简直要疯掉了!
唉!两人爱得这么火热,看来婚期不远了。我将抱撼终生,失恋失定了。
「兄弟!」沙哑声入耳,张天义也揽住我肩头,把我吓了一大跳。还没反应过来,声音又响:「你是不是忘了,怎没把东西交给她?」他表情质疑,口气带点责怪。
我说:「她把戒指收在铅笔盒,下课还和宋玉兰在审视,笑甲亲像圆仔花咧!」
张天义听了,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喃喃道:「那ㄟ按呢……」
我也很惊讶,照那纸条意思,她应该抱着他,被野狼载着赶往台北途中,要不也拥抱在巴士里。事情明显有变数,我暗暗窃喜,问道:「你擦什么,身上这么香?」
其实,我心里想问的是:你能不能拉开石门水库,亮出底牌?
因为,张天义很有料,左右鼠蹊都裹团肉包,香喷喷在夺目。
害我不想瞄都舍不得,还得费心猜,鲈鳗究竟藏在那一团?
「古龙水。」张天义站直身,摸摸三分头、拉拉领子,耍帅不是一般人做得来。他又凑脸来贴颊,说:「我们是好兄弟,你帮我注意她的动静,要什么尽管说。」
他老爱玩贴颊,我贪图舒服才帮忙。「伊恰北北,发现我在看都会瞪眼骂。」
「我知道。」他把嘴唇贴至我唇角,说:「她说你呆头呆脑爱偷看,像呆头鹅。」
说也奇怪,同样的话,郭玉琴柳眉倒竖,大声骂的时候,我完全没感觉。
张天义轻声细语在转述,我却有种被侵犯的不舒服。唬地转头,本要装狠,偏忘了双方距离这么近,嘴唇触到湿润的柔软,意外形成接吻的状态。诡异的是,他动也不动,神情并无不悦,瞇瞇笑着好像十分喜欢,舌尖还跑出来舔,简直是脱线的儿子。
我得把戏演足,鼻头压上他鼻尖,瞪眼道:「你也这样认为,很好笑厚?」
「啊……」他陡然醒悟,吃惊的表情僵了数秒。旋即笑容可掬,用力揽住我,摆明要弥补我受伤的心灵,很谄媚说:「我那有可能ㄟ按呢,三八兄弟麦黑白想啦!」
事实上,张天义很爱耍帅,展气魄时举止有种侠客的豪迈,又带点脱线的邪气。而且,他瞇瞇的眸光仿佛会放电,模样挺逗趣,我莫名想到布袋戏里的怪老子。老顽童很爱捉弄人,再送上口头禅:到担你才知!张天义也很爱耍人,鬼头鬼脑,让人应接不暇。我贪图人家的懒包,当然奉陪到底,强调道:「骗兄弟,会遭弟兄唾弃喔?」
「对对!既然是好兄弟,我的事你非帮不可,有想要什么吗?」
张天义仗着财力雄厚,总是抢着付帐,大肆收买虚荣感,偏偏大家都吃这一套。殊不知,兄弟讲究剖腹相见,我只要他开裤档就满意。但那不能公开,我要矜持,很得体说:「你是我的兄弟,我理该尽力帮忙。同样的,你也别客套,免得见外了。」
张天义听了,往我脸上啵下,再往背上一拍:「就爱你阿沙力,这样我就安啦!」
他玩亲亲似乎玩上瘾,也不管周遭是否有人。
而我,心里明明很乐意陪他玩,巴不得他常来玩。偏偏没种,就怕被人宣扬,只敢偷偷摸摸。连关心的事,也不敢光明正大提,旁敲侧击问:「你不是要去台北?」
「你怎会知道?」他反问,表情有抺惊讶。
我蓦然心虚,抓紧掌心的纸条,见风转舵说:「你穿这么有派头,好像新郎勒!」
「等我结婚那天,你这伴郎绝对跑不掉!」张天义又脱线了,额头猛鲁我的头。
忽然间,那绷在右鼠蹊的肉团迅速膨胀起来,粗粗长长浮在裤管上。
很显然,鲈鳗长大了。我千盼万盼,看得到碰不得,只能干瞪眼。
唉!鲈鳗不久将变成郭八妹的洞房宝贝,还真搔心的可惜。
若非是在教室,我一定会忍不住,至少也会去摸一把过过瘾。
我有十成把握,张天义会哇哇鬼叫,绝对不会翻脸。
根据来自事实,那晚北风寒冷,我独自在夜色中赶路,闻得摩托车声由后逼近,以为是行经的过客。旋即,强风袭身,沙哑声跟着响道:「张继唐!我来啊!」
我驻足,摩托车也停住。眼前一辆闪闪发亮的野狼,威风凛凛让月光变得璀璨起来。
拉风的代表,时下年轻人都梦想拥有,骑着去泡妞。
我二哥肖想了好几年,至今只存够买两个轮胎的钱。
张天义年纪轻轻,上辈子不知烧什么香,有闲情更有钱途。
他套件很拉风的藏青色飞行夹克,耍帅没拉拉练,露出单薄的黑色吊甲,牛仔裤把大腿绷紧,泛光的黑色皮鞋还扬散淡淡鞋油味,彰显时髦的品味。
但发型关系,他很像刚唱完绿岛小夜曲的黑狗兄,完全没有国中生的青涩。
对比下,我应该很像在绿岛挑水砍柴的小厮,相形见拙,好想把那件夹克抢过来。
注:那时代,绿岛是「监狱」代名词,得够大尾才有资格去唱小夜曲。









![1970全新版本《[综武侠]他们都想圈养我》 微生馥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757527.webp)